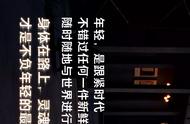内容简介
亡国帝姬宝锦,为姐复仇,隐瞒身份入宫随侍新帝。收复旧部、步步为营,却发现真相扑朔迷离。 一盏珍珠面具、一纸泛黄的情笺揭开了血染的过去。情途与权路,局中之人终难割舍。 千重宫门次第而开,景阳钟响回荡天宇,一切回到开始,他们又该怎样抉择……
本故事来源于QQ阅读
精彩片段
周遭喧杂人声渐渐止息,冠盖亭亭拥簇下,有人悠闲而入。
那人服色内外皆是玄黑,宽袖与前裾上以细密紧线织绣金龙,到得近前,才看清他眉目生得冷峻清扬。
正是清晨时分,他却带了淡淡倦意,扫视了满室中人,正对上一双震颤惊骇的黑眸。
是他!
宝锦跌坐在地,指甲深深陷入肉中,刺得鲜血淋漓,也浑然不觉。
竟是那林中吹笛的神秘男子!
她咬住唇,任由乱发蜿蜒垂落,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在这一刻冻结。
耳边的人声喧哗,她也听不见,满心满眼里,只有那“万岁”二字,仿佛狞笑的梦魇,铺天盖地的袭来。
就是这个人……将元家三百多年的天下颠覆,让锦渊姐姐……死无葬身之地!!
微凉有力的手掌将她的下颌抬起,强硬,不容置疑。
“是你。”
仍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意味,九五至尊的声音,醇清优美,少了往日的涩意和不耐,多了一股玩赏的兴味。
“居然是重眸……”
低笑声中,皇帝直对上她的眼。
温热的血从袖中逸出,手中一片湿腥气,明明只是一瞬间,却有亿万念头汹涌决堤而出。
宝锦的眼,异常清明,那幽幽重眸,穿越这红尘俗世,如宝钻辉璀一般映入他的眼中。
“你的琵琶……弹得很好。”
皇帝的声音,清晰地传入她耳中。
握住下颌的手,终于放开,下一瞬,她被那臂膀从地上挽起。
“宫中的御乐,尽是些蠢物,不料教司坊却有如此人才……朕却要收为己有了!”
他吩咐道:“将她调入太常寺的礼乐局,暂时安置在北五所。“
“万岁……”
禁军头领硬着头皮出列,低声道:“此女是*人的凶嫌,徐大人父子的命案,还须着落在她身上。”
皇帝听了,微微冷笑,“此次寿宴,朕一直在这,没看到什么刺客,却枉送了徐绩一条性命,京师治安如此,可真是让人放心!”
话中的讥讽刻薄,让一旁的京兆尹汗如雨下,皇帝却不看他,继续道:“徐绩的死与她有什么相干?!至于他的儿子……”
他沉吟道:“是什么状况?”
“徐公子住在西院,为父亲的身亡夜不能寐,小厮守在门外,只听房中一声重响,他已经倒地毙命了……是毒*。”
他偷瞄了一眼皇帝的脸色,道:“我们紧急搜索,却见这位玉染姑娘已经脱逃,那时正是四更天。”
“四更天……”
皇帝冷笑更甚,轻声道:“那时候,她跟朕都在竹林之中。”
那队长顿时一惊——竹林与西院相隔甚远,皇帝又是金口玉言,这样一来,这少女确实是清白无疑。
再无人敢违逆皇帝的意思,他又深深看了一眼垂首不语的宝锦,转身离去。
……
怎么一路回到教司坊的,宝锦已全然不知,浑浑噩噩间,已到了寝居门前。
季馨急急开门,金色的日光射入屋内。这晴暖的色泽,让宝锦终于从僵冷决绝中清醒过来。
胸中被压抑的气血终于涌上,她只觉得喉头一甜,哇的一声,一口鲜血便喷了出来。
在季馨的惊呼声中,她面若金纸,瘫倒在地,再也不省人事。
*了他……
一定要*了他,为所有人复仇……
这是她最后浮上心头的憎念。

****
徐绩府中,只剩下啼哭之声,仆役下人们一边布置灵堂,一边也在对这两起凶案议论纷纷。
沈氏逢此大难,已经哭晕了过去,所有家务,全由云氏一人操持。
她双目红肿,却仍沉静自若,指挥着家人奔忙,一日之间,丧仪便象模似样了。
“大姐,你下手真是狠辣……”
云时沉声道。
云氏面上波澜不惊,居然还微笑出声,“你居然有此妇人之仁。”
她端起凉透的茶盏,啜饮一口,姿态娴雅从容,“他是我的庶子,却也是沈氏最大的筹码。”
“她怂恿徐绩把婴华用来联姻,任意践踏她的幸福,那么,我便将她最珍爱的儿子毁去。”
她微笑越发森冷,“徐绩死了,他的宝贝儿子也被我除去,从此以后,这个家,终于可以安身立命了!”
她仿佛松了一口气,将念珠放在桌上,神情安恬无邪,仿佛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婴孩。
“你是用的丹顶红吧?”
云时问道,他望了一眼长姐,思索片刻,继续道:“茶中无毒……那么,是绢帕。”
云氏眸光一闪,叹道:“父亲说你缜密聪颖,世上难见,真是不假!”
“毒下在酒茶之中,极易发觉,于是你暗中让下人给他送去劣茶,他素来锦衣玉食,一口饮下便会觉得粗涩,吐掉后,定会以绢帕擦嘴,于是上面的毒素,就到了口唇之上。”
云时面无表情地复述着,看着姐姐悠然的微笑,他轻叹道:“你处境险恶,我也无法苛责……且自己好自为知吧!”
他起身就要回返,却听长姐轻喝道:“阿时!”
“你荐来的那个玉染姑娘,已经被皇上带回宫中了……”
她有些歉疚地说道。
“什么?!”
云时乍听这话,惊得停住了脚步。
他清俊沉毅的面容上,因这噩耗而染上了一层阴霾……和愤怒。
宝锦从车上下来,一眼便瞥见眼前巍峨典雅的重重宫阙。
如此的熟悉,然而又陌生……
她轻轻咬唇,眸光微闪之下,随即恢复了平静。
她温驯地低下了头,莲步轻移,跟着引导的女官前行。
今上攻入京中,也不过是一两年的光景,一应宫人仍是沿用前朝旧人,这位女官举止娴雅,脚步不疾不徐。
“皇上洪恩海量,才赦你入了禁中,天朝乃是礼仪之邦,不比你们那些塞上蛮夷,可别在御前出丑露乖。”
她声音虽然细柔,言语却并不客气,轻瞥了宝锦一眼,回转过身喃喃道:“奇怪,我总觉得你的脸有些熟悉……”
宝锦的唇边露出一道轻笑——
她辞阙下嫁之时,不过十五,经过四年的颠沛波折,身段已大为清减,加上长期郁结于心,面容气质都大为改观,整个京城,怕是再没有人能识出她的身份。
也许,那个面容圆润俏丽的宝锦,早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消散了吧……
不到一刻,一行人便来到云贤妃的锦粹宫前。
那女官停在光华璀璨的龙凤云纹照壁前,扬着脸吩咐了一句:“且在这等着,我去禀报娘娘。”
远处有接应的宫婢迎了她前去,两人一边行去,一边隐隐传来低语——
“这是从教司坊调来的,也不知道使了什么狐媚手段……早晚是个祸害……”
“我家贤妃娘娘掌管后宫事务,哪有闲心管这些小事,只见她一面就罢了……”
宝锦低着头默默等候,秋水寒月般的清眸牢牢盯着脚尖,仿佛那丝履上的嫩黄缎花有无穷玄机。
云贤妃吗……
垂下的乌发遮住了她的冷笑——这伪帝才篡了朝纲,就给自己的妻妾一一加了封号,这些宫中老人,居然就恬不知耻的满口喊上了!
她想起属下呈上的宗卷,上面特别提到了这位云贤妃。
她是江州云家的二小姐,也是云时的二姐,徐绩夫人的妹妹。
伪帝崛起时,云家便能“慧眼识人”,老家主认为此子非池中之物,力排众议,将女儿嫁他为妾。
以名门大阀的千金之尊,女儿居然为人妾室,这在当时被全江州的百姓嘲笑,现在看来,却是一项很有远见的投资。
****
“父亲大人当年这一着,如今看来,实在很有远见……”
云贤妃端起茶盏抿了一口,随即轻轻放下,举手透足间端方温雅,声音却是寡淡的,毫无称赞之意。
“那时候,他对我说:‘宁为英雄妾,不为庸人妻’,果然,没过几年,我便随了万岁,搬入了宫中,他也成了国丈。”
她微微一笑,仿佛含着无穷讥诮似的,眉心也隐隐见了细纹。
婴华斜签侍坐在下首,恭谨地听着,心中却因小姨的讥讽语调而暗自心惊。
“婴华,我不知大姐是怎么想的,竟把你也送到这见不得人的所在——一个两个地送进宫来,显摆我们家女儿多吗?!”
云贤妃在六宫和皇帝旧部之中,素来以低调谦恭著称,人前绝不多一字一语,因此才得了帝后二人的信赖,以后宫大权相托,可如今对着长姐的爱女,言语之间却是异常尖锐。
虽然尖锐,徐婴华却听出了她话中的关爱和担忧,她起身替小姨斟茶,轻轻道:“小姨,你别生气,仔细心绞痛又犯……”
云贤妃望着她,平日淡漠的眼中满是痛心,“徐绩被刺客所*,你庶出的兄长也死了,徐家眼看着没落……即使如此,也不需你牺牲了终生幸福,到这幽幽深宫中来活耗!”
“小姨,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徐婴华咬着唇,低低道:“我从小看惯了父亲的作为,天下男子都没什么两样,嫁给谁都不过是个色衰爱弛的下场,倒不如到宫中一搏,也许能振兴门楣。”
她看了眼云贤妃,有些腼腆地笑道:“更何况,小姨你执掌后宫大权,再不济也不会让我吃亏。”
“傻孩子哪!”
云贤妃恨铁不成钢地叹道:“你真以为万岁对我信任宠爱,这才委以重任吗?!”
她眉心深蹙着,咬牙冷笑道:“皇后娘娘忙于国政,无暇来管这些后宫琐碎,瞧着我老实本分,这才让我替她照看——什么大权,不过是人家不想要的弃物!”
“怎么会?!”
徐婴华惊诧地睁大了眼。
云贤妃笑得悲凉,指着鬓上的素钗通草,以及一只简单的银制虫草头道:“我一直以来隐忍低调,连金玉都不敢佩带,这才得了她的欢心……哼,皇上的宠爱!除了皇后,他眼里哪曾有过其他女子!”
她低低的,近乎****道:“这后宫之中,其实是女子的坟墓,婴华,你真的来错了!”
徐婴华瞧着小姨落泪,正在手足无措,却听廊下有人轻轻扣门。
“是谁?”
云贤妃迅速擦干了眼泪,平静如常地断坐着问道。
外间是心腹侍女的声气,“娘娘,教司坊那边调了个人来,正要等娘娘看过。”
“这种小事……”
云贤妃正要拒绝,却听徐婴华接口道:“这便是那个卷进我家凶案的玉染公主了!”
“是她?!”
贤妃不禁吃了一惊,想起大姐曾经说过的,皇上对她青眼有加,心中斟酌着,连声音也微微放缓了——
“请她进来吧!”
外间侍女何等精乖,听这一个请字,便应了一声自去。不过半刻,便有青绫裙幔在朱漆门槛前翩然而过。
那女子素衣布履,入殿觐见时,却也不似平常人的瑟缩,浓密的眼睫低垂着,恭谨的姿态将所有情绪遮掩。
云贤妃听婴华说得稀奇,留意去看她的相貌,却也不见什么国色天香,只那一双重眸,顾盼间清扬幽
“毕竟是一国的公主,这气韵品格就是和那些狐媚子不一样……”
贤妃低声表示赞许,和颜悦色的让她起来,还赐以座位。
“北五所住得还惯吗,那里素来荒凉,也未得修缮,也真委屈你了!”
婴华见小姨态度和缓,甚至带上了几分客气,也想通了其中奥秘,只听贤妃又道:“你初来乍到,宫中的礼仪律条也不熟悉,宫中刚选过秀女,她们每日在梨尚院跟掌事学习仪规,你也每日随班好了!”
婴华不禁一惊,那些秀女虽然暂无品级,却也是预定的未来嫔妃,玉染不过是乐师伎人,又怎能和她们同处一室?
“多谢娘娘恩典,只是贵贱有别,怕是玷污了各位……”
宝锦微微欠身,举动之间,肌肤雪白晶莹,脱俗耀目。
“无须过虑,你也曾是王家贵女,只是造化弄人……”
贤妃唏嘘道,又挽了婴华的手,对着阶下笑道:“这是我长姐的掌上明珠,也在中选秀女之列,你们今后可以多多亲近!”
又闲谈了片刻,贤妃赐了些缎帛,这才吩咐人送她回去。
“小姨,你是顾虑万岁,才对她如此优容的吗?”
“傻孩子,不看僧面也要看佛啊,她若今后得了圣宠,也好留个见面回旋之地。”
贤妃眉心掠过一道不易察觉的微笑,又道:“若万岁真的瞧中了她,那才有好戏看呢——哼哼,皇后一贯从容淡定,本宫倒想看看她花容失色的模样!”
她咬牙冷笑了一阵,眼中又重归黯然,“可惜……即使一时得宠,也撼动不了皇后一丝一毫。”
她回眼正视婴华,竟是前所未有的冷肃,“你记住,千万要在御前藏拙,万不得已承宠时,也不要拔了头筹!”
“您是担心皇后她……?”
婴华悚然大惊,背上生出冷汗来,“不至于吧,她从未有恶名传出……”
贤妃苦笑着,眼中的光芒幽闪,声音里竟也带上了惊惶——
“她不必行恶,就可以让人跌落万丈深渊!”
****
婴华再见宝锦时,是在梨尚院的正堂上。
正是休息时分,七八位中选秀女在厅中莺声笑语,却在见到缓缓而入的青裙纤影时,蓦然停止。
宝锦一路走近,步履翩然,所有人却都在她走近时,将椅子拉远了寸许。
“听说了吗,她是教司坊来的……”
有人低声说道,不过几日,她们便得悉了只言片语。
“不过是罪家奴婢,也配跟我们同处一室!”
清脆如黄鹂的嗓音,却带上了几分尖酸刻薄。
说话之人捋着雪腕上的金钏,上面七颗猫眼红紫饱满,眩得人眼迷离,配着那一身明红宫装,越发显得娇媚如玉。
她是皇后的堂妹方宛晴,在这一众秀女中,隐然领袖人物。
其余人也是勋贵之后,好几个人的父兄更是今上的得力良臣,她们一听这话,惊讶不屑之后,纷纷表示赞同。
“陈掌事,这是怎么弄的?!”
方宛晴娇斥道,一旁的管事额头见汗,却是有苦说不出。
“这等倡优乐妓,学什么礼仪也是白费!”
又有人在旁凑趣道,话还没完,却听一旁有人轻轻嗤笑。
方宛晴回头一看,不禁笑道:“哟,我却是忘记了——月妹妹跟她同是塞上蛮夷,只是你运气好,才没被没入教司坊。”
嗤笑的那少女肌肤苍白,眼角眉梢却是掩不住的英姿勃勃,她也并非凡俗,乃是若羌国公主。
若羌与姑墨同属于北郡十六国,向来是天朝臣属,姑墨王与先朝皇室交好,誓死不降今上,这才遭到灭国的下场,而若羌一向依附中原,任谁做皇帝,却都是恭谨服侍,如今新朝乍立,其国便将公主献入了今上的后宫。
这位公主名讳极长,翻成汉话就是明月之意,她闻听这恶毒言语,也不动怒,只是笑声更甚——
“世代王侯之家,确不需学什么礼仪,有些人祖辈手上仍有泥迹,倒是要好好学过,以免丢丑。”
她的汉话音调奇异,却是清晰流利,在众人的低笑声中,方宛晴气得面色铁青,银牙几乎咬断。
皇后出身陇西世族方氏,方宛晴身为她的族妹,却是入赘男子与方家女子所生,她父亲虽然豪富,祖辈却是泥瓦匠,可说是卑贱已极。
众人正在斗口,却听宝锦站在中央,轻声道:“各位都是天子亲点,自然不能与我这卑贱之人共处一室。“
她轻声对管事笑道:“教习姑姑马上就要来了吧,那就麻烦您替我拿扇屏风来,也好遮挡区分。”
管事踌躇半刻,便遣人拿了扇素屏风过来,刚刚将她的座位遮没。
“这便与诸位隔离开了……”
她轻声曼言道,众人却是面面相觑,神色古怪——
她这一遮,不显卑贱,却仿佛成不露面的千金贵躯,众人反似明面的陪衬了
方宛晴顿时气得酥胸起伏,怒道:“你以为自己是什么千金之尊吗,入了教司坊,就是千人睡万人压的——”
“住口。”
门廊下传来淡淡一喝,宛然却是女子声气,却让几位管事都面色大变。
此时正是秋凉时分,只见一袭雪色姑绒斗篷绰立门前,在众人的目光下,一双绣有金凤的云丝珠履轻轻迈过门槛。
“皇后娘娘……”
于是以几个管事为首,在场各人都一齐行礼如仪,厅中顿时鸦雀无声。
“都请起吧!”
皇后的声音并不冰冷,甚至带着几分和煦,金声玉振的清脆中,带着凛然天成的威仪。
“我今日无事,所以来看看大家……”
她环顾左右,见众人裣衽垂首,不禁笑道:“本宫又不是吃人的老虎,大家何必如此,今后同处皇城之中,日日受此惊吓,可怎生是好?”
她微笑加深,又补了一句道:“难道本宫长得比那门神还吓人吗?”
众人一阵轻笑,顿时气氛缓和下来,大家这才大胆抬头,细细凝望着这位中宫之主。
皇后不过二十三四岁的年纪,雪白的姑绒斗篷下,着云锦褙子,一身凤纹淡紫长裙,映得肌肤象牙一般细腻。
她笑容可亲,双目顾盼间,一时秋水盈盈,一时又凛然含威。
她望定了自家堂妹,笑容慢慢收敛,道:“你刚才说的什么?”
“回娘娘……”
方宛晴被她扫了一眼,所有的跋扈任性都仿佛雪溶冰消,一时气焰全无,她低下头,讷讷道:“这教司坊的贱婢要以屏风与我等隔开,我一时气忿……”
她绝口不提自己的挤兑,这话说来,倒好似宝锦摆起了排场,旁人噤口不言,那位若羌的明月公主却存心跟她卯上了,闻言扬声笑道:“刚才却是谁说的倡优乐妓?!”
所有人暗自为她的大胆而心惊,皇后看了她一眼,居然点头示意道:“公主一路远来,我未尽到地主之谊,实在有愧。”
她微微一躬,显得礼敬周全,回过身来看向自己堂妹,眼神却转为冷肃,“你言行不慎,口出秽语,罚你闭口三日,抄十卷女则。”
方宛晴张口就要辩驳,却被她的眸光一凝,再也说不出话来,只得泄气应下。
皇后又问了众人名姓,四五人过后,便瞥了见了素衣而立的宝锦。
两人目光相对,电光火石的一瞬,竟似暖日寒冰相触,心中都暗自“咦”了一声!
宝锦和皇后素不相识,观其言行,也算明慧有礼,却在对上她的这一眼后,莫名生出异样来。
那是很为玄奥的感觉,就好似丛林中的小兽遇上天敌,浑身寒毛都直竖而起,连心跳都慢了一拍,那般纯粹凛然的难受,
皇后也凤眸幽闪,朱唇微动,却终究没说出什么来,转而看向徐婴华。
因着云贤妃的关系,皇后也温言抚慰了她两句,又赐下一些赏赐,关照管事多加照应,这才出门而去。
一行伞冕宫人随她迤俪而去,众人凝望之下,不禁又敬又羡。
羡慕归羡慕,有见识的几位官宦之女,都曾听父兄谈及皇后与今上的伉俪情深。
皇后出自陇西方氏,方氏乃是有数的名门大阀,宝锦和锦渊二人的母后也出身于此,可算是隆盛已极。
皇后乃是家主嫡女,却慧眼识英雄,偶然邂逅当时还一文不明的今上,就毅然相随,这几年辅佐夫君大业,可算是比翼并肩。
今上性情虽然严峻莫测,却始终对她敬爱有家,虽然与云家联姻,娶了如今的云贤妃为侧室,却是再无所幸。
如今今上大业已定,虽仍有几处枭雄割据,却隐隐有中原一统的态势,这一班臣子瞧着他妻妾甚少,惟恐被世人所讥,这才群议上奏,行这选秀大事。
今上对皇后如此爱重……我们还有什么机会吗?
众女心中暗想,患得患失之下,室内气氛一时沉寂。再也没人关心“教司坊来的奴婢”了。
****
“娘娘,宛小姐虽说少不更事,也毕竟是方家的骨血,您这样当众训诫于她,恐怕……”
亲信的侍女琳儿在皇后身侧搀扶着,小心翼翼道。
“怕是太落了她的面子,她父母面上也不甚好看,是吗?”
皇后声音平淡,却带着几分冷意——
“就是要让她牢牢记着,今后才不至于闯下滔天大祸。”
她回手望了望梨尚院的青墙,又道:“他们以为我权势滔天,便可以借着这招牌飞扬跋扈了吗?我这点刀枪箭雨里拼出来的薄面,还不够这些小姐少爷们败的!”
琳儿听她声音严峻,再不敢开口。
却听皇后沉吟片刻,又问道:“那个素衣少女,就是姑墨国的公主吗?”
得到肯定答复后,她眸光闪烁,应了一声,再也没什么话说。
一路辇行,到了昭阳宫中,却听老尚宫上前禀道:“几位阁臣大人求见,已等了半个时辰。”
皇后唇边泛上一丝冷笑,款款轻道:“又是为了新政的事!”
她微一沉吟,任由宫人们解下斗篷,又换过常服,这才进了正殿。
几位阁臣袍服齐整,正座上等候,双方分宾主谒见后,皇后也不避讳,让身边宦官以金丝如意将珠帘挑开。
“大家当初共处一座营帐,面都见熟了,又何必用这劳什子装神弄鬼!”
她微笑道,很是诙谐从容,那几人不由一笑,凝重的气氛稍微松缓了些许。
皇后端起翠玉盏抿了口茶,好似没看见他们眼中的焦灼,径自开口问道:“徐绩家中如何了?”
几人正是满腹心思,被她这一问,不禁一楞。
徐绩虽然才不出众,却因长年浸润朝政,又有迎今上入京的从龙之功,这才做了首辅,其余几人口中不说,心中却甚是鄙夷他这种贰臣叛徒。
他们听说徐绩遇害,都只是派人去府上吊唁,如今乍听皇后问起,也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虽然是前朝旧臣,却能顺应天命,辅佐新朝,这一点可说是功不可没。”
皇后款款说道:“徐夫人遭遇丧夫丧子之痛,唯一的爱女也应选宫中,可说是孤苦伶仃,我看着甚为不忍,你们各家的夫人和女公子若是有暇,也该多多照应才是。”
众人唯唯称是,皇后由云氏夫人说起,谈及云时在姑墨的大捷,话题一转,又论及了此次的军费开支。
几人见此阵仗,纷纷以目示意,其中刘荀最为年长,也是今上器重的谋臣,他干咳一声,委婉道:“此次战事封赏不少,国库中虽然仍有赢余,却也架不住多方支用——江南今岁水患连连,江州又有蝗灾警讯,惟今之计,朝廷施政需缓,不宜有什么大动作。”
皇后闻听此言,秀眉一挑,似笑非笑地将茶盏放下,“刘卿这话说得奇,国库空虚,正要开源节流,新政十二条刚刚颁布,犹如久旱甘露一般,又怎么谈得上什么大动作——难道看着百姓饿死才是正理吗?”
“娘娘,新政十二条虽然不乏真知灼见,却是与民无益哪!”
一旁的李赢年少气盛,禁不住喊了出口。
皇后手中一凝,面沉如水,那一抹笑容也化为冰冷,“怎么个与民无益,我倒是想听听清楚!”
“启禀娘娘,这十二条看似革新弊政,消去冗繁,却是用事太激,用时太急,用人……也太偏!”
李赢背上冷汗直下,却仍咬牙把话说完。
皇后听完已是大怒,却仍隐忍不发,她抬起头,凤眸中不怒自威,光芒摄人,阁臣谁也不敢跟她对视。
“你们如今居身中枢,却是越发因循守旧……哼,也罢,我们也不必耽于口舌之争,且看成效好了!”
她端起茶盏,却不就饮,一旁宫人会意,于是上前轻道:“娘娘已经疲倦,请改日再来吧!”
几人无奈,鱼贯而出,从中庭而出,到了照壁前,才听李赢低声怒道:“牝鸡司晨!”
众人心中一凛,无不变色,环顾四周无人,惊恐之外,却都深已为然。
“我们殚精竭虑,推翻了景渊帝,以为救民于水火,却没曾想……”
刘荀捋着长须,怅然叹息道,其他人亦是面带愁绪,无言以对。

*****
梨尚院中,日已近午,今日的课程便告一段落。
秀女们络绎出门,乘了自己的小轿离去,片刻工夫,只剩下宝锦一人。
论起身份,她不过是一介乐者,当然也不会有什么轿辇接送。
她朝前走了一段,却听身后有人唤道:“玉染!”
愕然回身,却是那位若羌的明月公主。
她紧走两步,与宝锦并肩而行。
风吹起了两人的衣袂,明月的身上环佩轻响,丁冬悦耳。
已今初冬,她却只着一袭红锦长袍,红得似火焰一般,一头青丝也不梳髻,只是纷纷落下,以金蝶扣卷,白玉般的耳垂上缀有大颗髓玉,粉光莹莹,摄人魂魄。
她肌肤似雪,眉目深刻,自有一种塞外绝丽。
“我曾经见过你父王一面。“
半晌静默后,明月终于开口了。
“城破之时,他已经自尽。“
宝锦低声答道。
明月深深地望了她一眼,“你知道吗,我很羡慕你。”
这没头没脑的突兀一句,宝锦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却听明月又道:“若我父王也能知些廉耻,我宁可去教司坊,也不愿受此礼遇。”
这话几近大逆,已十分危险,宝锦望着前方——她的居处已近,正要辞别,却听身旁砰的一声,很是沉重。
她回眼去看,却见明月已摔倒在地,面色苍白,嘴唇发紫,全身都在颤抖。
“你怎么了?!”
宝锦俯身就要把她扶起,刚一接触,却好似浑身都坠入了冰窖之中,不禁打了个寒战。
“快去叫太医——”
她急声呼唤经过的侍卫,却被一只冰凉的手牢牢攥住——
“不要叫太医!”
这沉痛的,撕心裂肺的一声,几乎让人心颤。
明月雪白的牙齿都在打战,她勉强露出一道微笑来,“不要让我丢人现眼了……”
宝锦捉过她的手腕,微一把脉,不禁变色——
“这脉息……!”
她扶紧了明月,一字一句问道:“是谁做的!”
“还能有谁?”
明月笑得宁静,眼中染上了绝望的死寂,“十六根金针刺我的背后重穴,就是想费了我的武功——他们还怕我在龙床上*了当今圣上呢!”
“他们……是谁?”
宝锦艰涩地问道。
“当然是……我的父王,母后,还有……兄弟姐妹了。”

空旷的夹道上,这一瞬只有北风呼啸的声音,宝锦缓缓抬头,琉璃瓦的明光刺得她眼生痛。
她牢牢握着那一双冰冷的手,因为惊愕,再也说不出任何言语来。
“真是不甘心哪……”
明月的头靠在她的肩膀上,微微喘息着说道,笑容美不胜收,“我曾于千军中来去自如,也曾亲赴大漠深处探险,如今却是手无缚鸡之力,还要忍受经脉的寒毒发作……人生如此,也实在可笑!”
“为什么?!亲生骨肉也要下这样的狠手?!”
宝锦骇然低喊道。
“因为只要我在若羌一日,就不会容忍他们这般低三下四地称臣,若羌虽是小国,却也该有自己的尊严……”
明月的眼中射出凛然光芒,苍白的面容上染上无穷自信,“而我手中掌握的,却是若羌的大部兵马!”
“是这样!”
宝锦想起自己看过的宗卷,道是若羌有位公主深谙武略,曾以千人驱散来袭的瓦剌骑兵。莫非就是眼前这位吗?
“把我这废人送入宫中,一则安心,二则,我这张脸还能看,还能给他们换些圣眷!”
明月的唇边露出阴冷微笑,眼中光芒逐渐黯淡,她望着远处跑来的侍卫和医官,低低道:“不过是白费功夫,谁也救不了我……”
宝锦低低攥着她的手,心中千万道念头闪过,她咬紧了唇,却浑然不觉身边的嘈杂。
“这是怎么了……”
一道熟悉的声音将她从昏乱中惊醒,她抬起头,这才发现侍卫和医官在身旁围了一圈,圈外一人,头戴玉制梁冠,着一袭绣金蟒袍,雍容华贵之下,却透出别样的清俊儒雅。
“靖王殿下!”
众人一齐上前参见,云时命他们起身,看着这混乱一幕,他第二遍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宝锦抬起头,云时看入她的眼中,为那份清冷幽凛而微微一惊——
“是你!”
他百感交集地低声道。
“明月公主……身体虚弱,所以晕倒了。”
她缓缓说道,嘴唇静静开合,语声如飞雪溅水,让人心生悚然。
“把她抬到附近殿中,先行诊治要紧。”
云时虽然觉得气氛诡异,仍指挥众人开始施救。
一阵忙乱后,太医虽知有异,却仍含糊其辞,不多时,明月有所好转,自有她院中的侍婢将她搀扶回去。
宝锦见事已了,也不惊动旁人,自行出殿回返。
到了殿门前,却见云时已等候多时了。
两人走在青石铺就的宫道上,谁也没有说话。
直到馨园的林中小道,眼看北五所已在眼前,云时才拉过了她的手。
“你的手怎么了?”
云时沉声道,方才虽然混乱,他却一眼瞥见,心中大痛。
原本洁白柔嫩的纤纤玉指,因这几日频繁的练琴而伤痕累累,被锐利琴弦划破的地方,犹有血痕斑斑。
“他们竟敢这么作践你?!”
云时眼中冒出凛然火光,咬牙道。
“宫中乐官都是技艺娴熟,只我一人是新进的……”
宝锦淡淡道,谈起那些若有若无的刁难排挤,只是一句带过。
“混帐……”
云时又怒又急,沉吟片刻,毅然道:“我来想办法,定要设法把你从宫中调出……”
“然后再回教司坊?!”
宝锦轻嘲地笑了,“靖王,你身为今上的义弟和好友,应该知道他是什么脾气——我父王悖逆不从,他正好拿我*鸡儆猴,又怎么会让我好受?!”
她语声淡漠,眼中清辉潋滟,冷然中带着奇异的凄楚,一双重眸让云时几乎沉溺。
爱恋与心痛在这瞬交织在他心头,又因这重眸想起母亲的身亡,云时心中昏乱纷繁,将嘴唇都咬出血来,却也无言以对。
宝锦懵懂不知,犹自冷笑道:“靖王殿下知道了这层利害,也不要想着救我于水火了——你难道要以下抗上不成?!”
“你住口!”
再也忍耐不住胸中的岩浆,云时咬牙低喝,宝锦只觉得胳膊上禁箍似的剧痛,身子一轻,被云时拽入树后,羽毛似的靠在树干上。
“你听着,无论如何,无论要与谁抗衡,我都要救你出来!”
云时深深凝望着她,语声坚如磐石,决然沉稳。
在宝锦惊愕茫然的目光里,他悍烈的黑眸逐渐平静下来,仿佛一根甭紧的弦缓缓松下,他低低道:“无论如何,我都会做到……”
高大的阴影从上方投下,他微微俯身,两人的面庞逐渐靠近——
灼热的唇印上她的,他的身躯有着冬日的松木清香,宝锦睁大了眼,在这一瞬惊得手足无措。
“你们在做什么?!!”
阴冷莫测的低喝声在不远处响起,云时全身一颤,毅然回头——
“陛下?!”
只见皇帝着一袭玄缎常服,正站在花径外三丈远。
淡金日光下,他袍服上的翟纹龙饰烨然生辉,映得眼光也越发冷冽。
他缓缓行来,广袖玉冠,映着身后落英缤纷,好似神仙中人。
只那眉目间的阴骛森寒,让人心中一颤。
他深沉的黑眸看着两人亲密贴近的身躯,最后凝定在云时紧握的手掌上——
“二弟……“
他终于开口,却是好久不用的义军中称谓。
“你看上了她?!”
声音不高,也听不出什么喜怒,却偏有一道凛然冰冷,让人心中刺痛。
云时咬牙不语,林间凋落的秋叶仿佛也受他心境所扰,纠缠乱飞起来,半晌,他决然抬头,“是!”
皇帝的目光在这瞬越发凌厉,云时迎着这份刺痛,向前踱了一步,声音不改平日的清澈平静——
“还请皇上成全!”
皇帝望住了他,目光深邃难测,他冷笑道:“朕往日赐你美人,你都坚辞不受,如今却是非她不要吗?!”
他看向宝锦,后者只觉那黑眸中一片冰冷,下一瞬,一道强大的手劲将她拽出,不顾她的挣扎,朝着林外而去。
“姑墨国的其他人随你取用,除去她以外……”
皇帝的声音,漫然传来,云时僵立不动,手间青筋甭出,一拳捶在树上,惊得飞鸟直匝四起,一时叶落如雨,疯狂地打在他的脸上。
****
张巡自被擢为皇帝的亲信太监,对他的秉性也算有了些了解——今上虽然阴晴莫测,在女色上头,却一直不甚乐衷,就连这次选秀,亦是在重臣的催促之下举行的。
这一日他正在殿中督导,却听廊下微微有人声嘈杂,随即,殿门被粗暴推开,他愕然抬头,却见今上拖着一位女子径自而入。
他不顾对方的惊呼,将她摔落地上,轻瞥了一眼四周,宫人们心领神会,匆匆而出。
殿门随即紧闭,龙涎香的熏染下,满殿皆是寂静无声。
宝锦跪了半晌,青金石的地面磕得她双膝酸痛,却仍是没有得到起身的允许。
她想起方才被拖曳着长驱直入,阖宫上下宫女太监的惊诧目光,心中越发苦涩——
这一幕片刻之后便会传遍六宫,到时候,会是何等的轩然大波……
清晰的脚步声打破了沉寂,她的眼角余光瞥见一双锦靴伫立眼前。
“在林间与人偷**,这就是你们王室的家教吗?!”
冰冷的声音,从头顶响起,语声中带着讥诮。
宝锦心中大怒,压抑了良久,终究忍不住回道:“我云英未嫁,靖王亦未娶妻,有何不可?!“
“好刁利的一张嘴!“
皇帝怒极反笑,宝锦只觉得下颌被他强硬抬起,双目相对,她看入他眼中的冷怒与阴霾。
“云时是朕的义弟,亦是不世出的帅才……你依仗美色,就想离间其中吗?!“
“我不过一介奴婢,又怎么能离间得了你们这些贵人?!”
宝锦微微冷笑,声音清脆如刃,“就算我欲学貂禅,陛下也要自认董卓才是!”
这般辛辣刻毒的讽喻,让皇帝眸光一盛,怒不可遏。
宝锦只觉得浑身一轻,竟被他掐着玉颈提起,狠狠仍到了御案之上。
与云时的小心翼翼不同,他紧紧钳制着她的手腕,剧痛从腕间传来——怕是青肿一片了,宝锦自嘲地想。
头顶的阴影压下,仿佛将所有光亮都遮挡,满殿昏暗在这一瞬染入她的眼中。
冰冷的唇印上她的,近乎凶狠的咬噬,冷戾近乎惩罚。
宝锦……不要怕……
她在心中默念着,强迫自己不要闭眼。
只听嘶的一声轻响,她的衣衫被扯裂,冰雪般的肌肤裸露在空气中,一阵凉意从心中生出。
无法挽回了吗……
宝锦的重眸中一片茫然,极度的狂乱,反映在眼中,却是无边的黑寂宁静。
唇边一阵湿热,她的眼缓缓清明,却见他停止了侵略,以指蘸了她咬破的鲜血——
“说话这般凶狠,到头来只能咬自己……你难道想嚼舌自尽吗?!”
冰冷的声调,不带任何情绪,听入她的耳中,却似凉薄的调侃一般。
他的黑眸望定了她,奇异的,居然漾起微妙的笑意。
“看着你的重眸,就好似……”
后半句,他再也没有说下去。
皇帝缓缓放手,任由她从书案上滑下,随即惊跃而起,掩了衣衫,冲出殿外。
本故事来源于QQ阅读《景帝的爱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