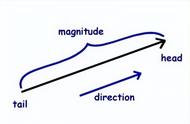小时候,我家门口那棵大香椿树已经好大了,树干一个大人都抱不住,高也接近二十米,是小村里最大的一棵香椿树。
香椿树离地五六米高的地方才分了枝杈,树干笔直,是少见的良材。这香椿树还是优质品种,当地称为白香椿。每年春天,总能长出壮壮实实的香椿,翠嫩可爱,叶肥茎粗,采摘香椿每每都是很热闹的事。采香椿用的是当地土话叫扳钩的工具,长长木杆杆头装上一个铁钩。爸爸爬上那高高的树干,用扳钩把香椿枝扯坏,从树上扔下来,奶奶和村里许多乡亲都在地上捡。那肥美的香椿纷纷从高处落下,所有参与的乡亲都有份。爷爷奶奶出奇得大方,从来没有舍不得。乡亲们拿剩下的,奶奶会仔细收起来,一般是切碎,焯水,放点盐和醋,就是美味了。那时鸡蛋都用来到供销社换煤油、食盐等日用品,都舍不得吃。如果饭桌上有一盘香椿炒鸡蛋,那可是奢侈得不得了。
童年家乡春天蔬菜是极缺的,奶奶往往把香椿切碎晾晒。晾干后,小心包起来存放,遇到没有菜时,用水泡泡,再调制。有时候也把干香椿和自制的豆酱一起炒一下,如果放上辣椒面,那味道可真是美极了。我上初中时,学校离家四十多里,每两周休息一次,馍是从家里带的,学校灶上没有菜,这香椿豆酱加辣椒就是日常下饭菜了,那滋味一生都忘不掉。
采摘香椿记忆中大多是爸爸上树,偶尔也有村里年轻的乡亲上树,当我十岁的时候就也能爬上那大树采摘香椿了。在那高高的大树上,俯瞰可以看到小村的每一个角落,就连那大犍牛也变小了许多。风在耳边嗖嗖地吹,树枝在晃,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就站在大树枝杈上采香椿,很气派。
这大香椿树是很有个性的。每年收香椿时,都要把树顶上留下来。有一年村里一个乡亲没有留顶上的香椿,全扳了下来,虽然多采了许多香椿,但光秃秃的树干、树枝在春风中很是落寞凄凉,用了好长时间才又长出椿芽。也许是生气了,也许是对贪心的抗议,第二年开春,大香椿树迟迟不发芽,从那以后,人们再也不敢把顶芽采走了。
忘记了什么时候,树上多了个喜鹊窝。那喜鹊有时也偷吃鸡窝里的鸡蛋,尽管奶奶、妈妈都很心疼,但从不让我们掏鸟蛋。劳作之余,奶奶总喜欢坐在大门槛上,笑眯眯地盯着鸟窝,说鸟该下蛋啦,小鸟出蛋壳啦,小鸟饿啦,小鸟该出窝啦,有时也哼着只有奶奶自己懂的小调。每每清晨或黄昏,喜鹊在枝头喳喳叫,奶奶总会说有喜事要来了。自从有了鸟窝以后,鸟窝以上的香椿就再也没有采摘过,怕打扰到喜鹊。
后来大香椿树被大爸砍伐做家具了,我失落了许久。没想到第二年开春,树茬上又长出许多嫩芽。扳去多余的嫩芽,只留下最粗壮的一枝,第一年居然长到三米多高。不出几年它又长成像模像样的一棵树,那模样几乎就是那大香椿树的翻版,分杈的地方也几乎一样,照例是每年都能提供许多鲜香椿。大香椿树的生命就以这样倔强的方式延续着。
后来爷爷奶奶、爸爸、外祖父外祖母,以及许多乡亲都走了,香椿再也没有人采摘了,树枝树干就在老屋前疯长着。
近期回老家,惊喜地看到更粗壮的香椿树上赫然有了一个喜鹊窝。在乡村人们的心目中,喜鹊是祥鸟,喜鹊的叫声会带来幸福。但愿这喜鹊会为我们小山村带来生机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