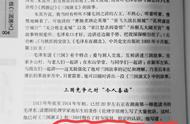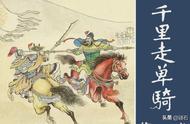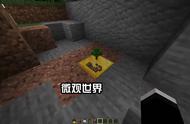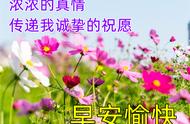纵观中国古代的小说,那些影响最大的作品,都是亦雅亦俗、雅俗共赏的作品。譬如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如此。老百姓喜闻乐见,文人学子也津津乐道。像《儒林外史》《红楼梦》这样的作品,虽然也划入通俗小说,但比起《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来说,又要雅了一点,但在民间的影响力却无法与之相比。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宋江、武松、李逵、孙悟空、猪八戒,比王冕、范进、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知名度高多了。说雅俗共赏则影响最大,实际上是同义反复。雅人欣赏、俗人也欣赏,当然是影响最大。问题在于,《三国演义》雅在哪里,俗在何处,又是如何做到雅俗共赏的。

三国演义
从《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来看,既不是一种由俗到雅的过程,也不是一种由雅趋俗的过程,而是一种俗和雅不断地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又互相排斥、互相摩擦,终于交融在一起、难分难解的复杂过程。《三国演义》雅的成分主要来自《三国志》。《三国志》是史学巨著,从叙事来说,《三国志》要排斥想象和虚构;从语言来说,《三国志》采用纯正文言文;从趣味来说,《三国志》感兴趣的是探索兴亡成败的道理和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从风格来说,《三国志》追求的是严肃简明的风格。《三国演义》固然不是史学,而是小说。可是,《三国演义》既然要以《三国演义》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文字依据,它就不能不受到《三国志》是巨大牵制。如此一来,《三国演义》的想象和虚构便不能离开史实太远。《三国志》中的很多奏章、书信、诏书被直接抄入小说,或是稍作加工,便吸收进去。《三国演义》的行文中更是大量地出现文言文。国家的兴亡成败、人物的功过是非,便自然地成为小说的兴奋点。凡此种种,都为小说注入雅的成分。

三国志
《三国演义》中雅的成分不仅来自《三国志》,而且来自裴松之注,来自《世说新语》一类的笔记小说,来自唐诗宋词。它们给小说所注入的营养要比《三国志》复杂得多。裴注引书一百四十余种,其中多有野史,这些野史往往带有较多的感情投入,带有细节的描写,也不排斥想象和虚构。野史中那些杂有爱憎、不乏想象和虚构的故事,虽然与民间的说唱还有所不同,但与严肃的《三国志》已经是大异其趣,而与《三国演义》只有一步之遥。至于诗词和笔记小说,那就更不用说。野史和笔记往往在偷偷摸摸地追求故事性和趣味性,这就是它们与小说相同的地方,也是它们常常因此自降身份的原因、但野史和笔记毕竟是文人所作,所以又带来文人的爱好、趣味,带来了文人的学问、语言。我们看演义中诸葛亮那种名士风度,那一份超凡脱俗的胸襟气度,便不能不承认《世说新语》和唐诗宋词对小说的潜在影响。除此之外,历代文人墨客,还写下无数关于三国人物史论、杂文、辞赋。

世说新语
无论是《三国志》和裴注,还是笔记小说和诗文辞赋,都未能像说话艺术及戏曲一样体现出一以贯之的拥刘反曹的倾向。陈寿虽然已曹魏为正统,但也称刘备为先主,刘禅为后主,对诸葛亮推崇备至。裴松之对三方的人物更为客观。杜甫写了一些赞颂诸葛亮的诗篇脍炙人口、人所共知。但是他对曹操也并不反感。他给左武卫将军曹霸写了一首诗《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第一句就说:“将军魏武之子孙。”这里显然是一种赞扬的口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虽然以曹魏纪年,似乎是以曹魏为正统,但只是为了叙事方便。苏轼写《前赤壁赋》提到曹操时,说:“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承认曹操是个英雄。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对周瑜佩服得不得了:“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他的诗歌《隆中》对诸葛亮极表仰慕之情。他的《诸葛亮论》又不满于诸葛亮的“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这就是说,雅文化虽然也有感情、有褒贬、有倾向、有取舍,但还是比较客观。即使在追求故事性、趣味性的同时,也不敢离开学术性。雅文化是在保持学术性的前提下追求故事性和趣味性。当然,这种说法也是相对的,追求故事性、趣味性总是难免会让学术性遭到一些损失。

曹操横槊赋诗
尽管《三国演义》从《三国志》及裴注,从笔记小说和唐诗宋词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但是。如果没有俗文化的发展,没有说话艺术、宋元戏曲的浇灌,要产生像《三国演义》这样伟大的历史长篇小说还是不可想象的。是民间文化给了三国故事以拥刘反曹的倾向,这就使三国故事染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是这种娱乐大众的功能给了小说创作以巨大的推动力,使三国故事借助大胆的艺术虚构不断提高故事性,使人物越来越生动传神。说话艺术和戏曲艺术是商业化的艺术,是投入市场的艺术,是民间艺人的衣食父母。文化市场的激烈竞争大大加快了三国故事的进步过程,一方面也不拒绝从雅文化中汲取营养。南宋罗烨所著的《醉翁谈录》中就说: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
这种兼跨雅俗两大文化的说书艺人,虽然常常被有学问的雅人讥讽为“村学秀才”,但他们的确也是《三国演义》的重要功臣。

民间说书艺人
从史书到小说,大胆的艺术虚构是关键,文人不容易跨出这一步,民间的艺人则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和犹豫。他们其实也并非因为读过《文学原理》《艺术概论》,懂得了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区别与联系,才勇敢跨出这一步,为了娱乐大众、为了谋生、同时也为了自娱自乐,他们视艺术的虚构㘝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地位卑贱的人又一次显得比文人聪明。虽然最初的虚构显得非常稚拙,甚至十分可笑,但它的方向没错,终于越来越成熟。与此同时雅文化却显得十分保守,对文化新形势看不惯,他们一味地在虚实问题上纠缠不休,蔑视一味“媚俗”的小说,表现出俗文化的误解和隔膜。明朝大文豪王士祯写诗来吊庞统,题目是《落凤坡吊庞士元》,被人传为笑柄。原因就在于王士祯混淆了雅文化和俗文化的界限。清朝学者袁枚在所著《随园诗话》中说:

庞统
崔念陵进士,诗才极佳,惜有五古一篇,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说演义语也,何可入诗?圮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语,被毛西河诮其无稽,终身惭悔。
也是不允许混淆雅文化和俗文化的界限。
通俗小说显然是感受到了来自雅人的压力,于是,小说中的序跋中便常有寓教于乐的自辩。即便是充斥着性描写的《金瓶梅》,前面的序跋也要说该书是如何有益于世道人心。将嘉靖本与毛本相比,后者显然是为了加强封建说教。这种说教色彩的加强,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毛纶父子的思想,另一方面,也不妨看作面对雅文化的压力,俗文化的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反应。
小说毕竟有审美的功能,这种审美的功能对于雅人有一种诱惑的力量,这种诱惑造成了文人的分化。于是。一部分文人出来替俗文化辩解,一部分文人则激烈地咒骂。辩解者认为小说之感人,犹如晨钟暮鼓,胜过四书五经。咒骂者则认为小说之可恶,简直是洪水猛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