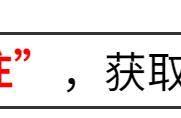(Boyan Topaloff/图)
“人们相信追逐繁星会有回报,而最终却像金鱼缸里的金鱼一般了结残生。”
在小说《刺猬的优雅》开篇,法国作家妙莉叶·芭贝里(Muriel Barbery)借12岁富家千金帕洛玛之口道出“身处鱼缸之中的创伤”,由此开启对孤独、自由、生死等生命议题的拷问。
当那个看透世界虚妄、计划自*的女孩结识寡居、博学的门房老太太勒妮之后,她的人生渐被照亮,帕洛玛眼中的勒妮“从外表看,她满身都是刺,是真正意义上的坚不可摧的堡垒”、“从内在看,她也是不折不扣地有着和刺猬一样的细腻”、“喜欢封闭自己在无人之境,却有着非凡的优雅”。
《刺猬的优雅》出版后即获得法国书商奖,两年半内销售达200万册,“继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之后,以长销之姿雄踞畅销传奇”(《法兰西晚报》)。芭贝里认为,读者也许在她的作品中寻得共鸣:“我们都是孤独的刺猬,只有频率相同的人,才能看见彼此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优雅。”
芭贝里1969年生于摩洛哥,曾在法国诺曼底教授哲学。她的第一部小说《终极美味》获得2000年度最佳美食文学奖和2001年酒神巴库斯奖。哲学出身的她相信美食具有奇妙的治愈力。“正如我们对待生活那样,我们也应该以负责、美好、纯粹、颇具精神性和仪式感的方式饮食,那样我们才会变得更好!”
2023年底,芭贝里携新作《狐狸的灼心》(Une heure de ferveur)中文版来华与中国读者面对面交流,其间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这一次,她将视角转向痴迷已久的东方文化,坦言自己喜欢像“刺猬”那样静静观察,但也喜爱狐狸的智慧和野心——“一切不曾炽热的终将消逝。”

《小王子》因结合孩童的纯真与成人的智慧而成为经典
南方人物周刊:中国读者认识你最早缘于那本《刺猬的优雅》。此次《狐狸的灼心》中译本出版,译者对小说原标题进行了意译。据我所知,法文原书名直译为《一小时的炽热》,出自圣-埃克苏佩里的《风沙星辰》。
芭贝里:编辑希望改下原标题,让它更符合中国读者的期待。我认为小说的法文原标题非常美,它取自圣-埃克苏佩里书中的一句话,他曾解释说,当他自己还是名年轻飞行员、第一次在北非摩洛哥的沙漠上空飞行时,他对那片沙漠充满敬意,他热爱它的原始、纯净。在他看来,那是一片没被任何战争污染的“贞洁之地”,仿佛是一座天堂,但它已不复存在,他在书中写道:“棕榈树也好,贝壳粉也好,它们已将最珍贵的东西赋予了我们,它们给予了我们一小时的炽热,而我们将是那一刻唯一的见证人。”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它提示我们,也许生命中只有那么几小时满怀虔敬和热情,但我们必须努力追寻,当它降临时,我们要牢牢抓住,别让它溜走。
南方人物周刊:说到圣-埃克苏佩里,我想到《小王子》里狐狸也是主角。你书中“狐狸”的隐喻是否与《小王子》也有关?你如何评价《小王子》这部经典和它所蕴含的人生哲理?
芭贝里:你比我敏锐,我还没想到这点。当然,《小王子》其实也象征着我刚才说到的:那种孩童般的纯真和高浓度的热情。我这部作品与纯洁有关,我们需要保持灵魂纯洁的能力,能够直面那些真正的问题。我喜欢圣-埃克苏佩里,他的作品具有某种孩童般的纯真,这种精神气质同时又与成人的智慧结合,最后形成那些永恒的经典。

南方人物周刊:提及孩童,我小时候读过一本法国故事集《列那狐的故事》,我很好奇,法国人怎么看狐狸这个形象?也请聊下你书中“狐狸”这个意象的诞生?
芭贝里:我们对狐狸的看法也分正反两面,它在很多寓言和神话传说中出现。在许多故事里,它是个狡诈的家伙,擅长钻规则的空子,使些小手段,因此不可信;另一方面,它也被视作美丽、诗意的动物,尤其是那种迷人的颇具诱惑力的女性。日本传说中的白面九尾狐“玉藻前”也是这样的形象,我想在亚洲古老的传说中,常有这类“狐狸精”的隐喻。
我觉得中译本标题《狐狸的灼心》也是个美妙的标题,因为小说中的狐狸象征着我前面提到的那种“一小时的炽热”,如果我们在死前还没明白这些生命要义,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事。此外,这个故事的背景设置在日本,事实上,狐狸的形象在日本很常见,在他们的寺庙和各种书籍中都有狐狸出没,旅居日本时,我差不多被狐狸包围了。
南方人物周刊:古话说,“狐狸知道很多东西,刺猬却有一个绝招”,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后来将思想家也分为这两类人,哲学专业出身的你,觉得自己更像“刺猬”还是“狐狸”?
芭贝里:事实上,写下《刺猬的优雅》这个标题时,我不知道伯林那个著名论调,直到小说大卖,有读者提及伯林这个说法,我既惊讶又觉有趣。虽然我学哲学,但我真的不是那种思想型学者,该写论文时,我最后却写了本小说,我最终都没完成自己的论文,我放弃了,辞去哲学老师的教职,离开大学成为一名全职作家。至于刺猬和狐狸,我两方面都沾点边。我喜欢像刺猬那样静观,如果你走得太快,许多东西就看不太清,但我也喜欢狐狸的智慧和野心。

电影《刺猬的优雅》剧照
对于涉及人类事物的东西,不要笑,不要哭,不要恨,要理解
南方人物周刊:当年写作《刺猬的优雅》时,你是如何开启“刺猬”这个意象的?
芭贝里:事实上,那部小说初版本中并没提到刺猬。小说原题《一杯茶》,因为书中的帕洛玛偏爱茶,她开玩笑说:好人饮茶,坏人喝咖啡,茶与日本、亚洲有关,我觉得是小说的一个线索,但编辑看到这个标题后告诉我,恐怕你得换个更有意思的标题。当时,我前夫看了书稿,提到把“优雅”和“刺猬”两个词放进标题,但他马上又说:算了,这不是个好主意。我说:不不不,这个标题完美!然后我在小说中加入帕洛玛将勒妮比作刺猬的那句评论,这个比喻很清楚。她们两人都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外界伤害而极度防卫的个性,但内心却非常温柔、甜蜜、美好,所以我觉得那个标题堪称完美!
南方人物周刊:你将“优雅”和“刺猬”两个看似矛盾的元素并置,这次新书中译本标题“狐狸”与“灼心”(虔诚)又似是一组矛盾意象,你致力于挖掘表象之下隐藏的人性特质?
芭贝里:当然!我感兴趣的就是人类的复杂性。我们都是如此,但很少意识到。我写小说不写论文的原因就在于,当我思考某个人物时,我能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矛盾冲突,写作时我需要成为另一个人,在思想和情感上与其共生,由此更能理解人性的复杂。
南方人物周刊:介绍下你成为小说家之前作为哲学教授的生活?
芭贝里:我喜欢当一名教师,很享受与学生的互动。《刺猬的优雅》成功后,我渐渐厌倦了教学生活,这与学生无关,而与教学条件、各种考评、行政程序等有关,我觉得那些琐事比较无聊,我想离开学校,所以就辞职了。
南方人物周刊:哪位哲学家的思想对你曾产生过深刻影响?
芭贝里:我欣赏巴鲁赫·斯宾诺莎,因为他不断提醒人们,论断前要三思,“对于涉及人类事物的东西,不要笑,不要哭,不要恨,要理解。”最重要的不是论断,而是理解。
南方人物周刊:说说你最欣赏的女性哲学家?
芭贝里:我想应该是西蒙娜·薇依,因为她那份热情和纯真:追求心灵的绝对诚实。她的书写更像是文学作品,不太像哲学论著。
南方人物周刊:从早年在工厂的重体力劳动到去世前的“禁食”,薇依似乎主动选择了一种“受难”式的生活。
芭贝里:我真高兴,你是我在国外谈论薇依时遇到的第一位也读她作品的朋友。关于这些“苦难”,她曾在笔记中写过,即使身心俱疲,她依然会坚持下去,这些论述对我产生了极深的影响,我由衷钦佩她。
南方人物周刊:除了薇依,你还会推荐女性阅读谁的著作?为什么?
芭贝里:我还会推荐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她是小说家,写过《东方故事集》等作品,但她也有不少谈论写作的论述,我发现那些精彩文字同样在论述人生,尤瑟纳尔是一位了不起的、强大的女性。
南方人物周刊:我喜欢她的《哈德良回忆录》。
芭贝里:你知道吗?关于这本书,她还有一部创作笔记,在我看来,那是又一部杰作。

我笔下所有角色都以不同方式面对孤独
南方人物周刊:说起你最畅销的代表作《刺猬的优雅》,其中的天才少女帕洛玛和门房勒妮可有原型?最初创作这部小说时,你是如何打造这两个女主人公的?
芭贝里:这正是创作最神秘的部分,写小说有技巧,情节你能控制,细节你可以改进,但人物的出现就是如此神奇。我的创作从来都没有原型,我笔下的人物都是完全虚构的,这也是我写作中最需要的,因为这是我理解他人的方式,我喜欢创作与自己截然不同、完全来自其他生活背景的人物。如果我创造这个人物,我就知道自己想从中学习些什么了。
南方人物周刊:我记得门房勒妮最早在你的处女作《终极美味》中就已出现?
芭贝里:没错!感谢你的阅读,对我的作品如此熟悉。其实我不认识什么门房,通常只有富人住的房子才有门房,而我们家也并非富贵阶层,我小时候都不住在巴黎,完全没有故事中这些经历。进大学后,我从外省搬去巴黎,在那里,我和来自巴黎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混在一起,对我而言,那是个全新的世界,我饶有兴趣地观察着他们,有时觉得自己就像是在一个动物园里。
南方人物周刊:记得《刺猬的优雅》中有这样的句子:“政治,不过是小富人们不借给其他人的玩具罢了”;“会做事的做事,不会做事的教书,不会教书的教教书的人,而不会教教书的人的就搞政治吧。”
芭贝里:这是我笔下角色想出来的,我不会分享他们脑袋里所有的想法,但我很同意帕洛玛说的这点,这是种极其有趣的看待事物的思路。我们必须认识到,政治世界并不完全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事实上,我曾经也是一个教教书的人,(笑)我认为讽刺是治疗一切的良药,对于自己的所思所想,我们应该经常保持这种批评和讽刺的态度。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作品经常探讨对“死亡”的认知,你怎么看待书中天才少女的自*倾向?人们应该如何帮助那些青春期躁动的孩子破除“自*”的心魔?
芭贝里:《刺猬的优雅》出版时,我遇到不少十三四岁的年轻读者,他们告诉我,他们真的在帕洛玛身上认出了自己,这让我很惊讶,因为她完全是我创造出来的。这些年轻人告诉我,唯一能让他们免于自*的是与他人分享,当他们遇到另一个同类或坐下来阅读我的书时,他们不再感到孤独,能与那些同样感到绝望、有类似想法的同龄人产生联结。所以,分享是唯一的良药,但如何让他们敞开心扉去分享,我并不知道法门。
南方人物周刊:从《刺猬的优雅》到《狐狸的灼心》,两部作品中的中年人也都需直面“孤独”,人当如何战胜孤独带来的负面情绪?
芭贝里:这其实是我所有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我笔下所有角色都以不同方式面对孤独,我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个问题。面对爱与被爱,他们各有难处,天才少女、贫穷寡妇、富有的中年男人……对他们每个人而言,都需要直面孤独,我看到其中的矛盾,也看出其中的共性。你说得一点没错,他们都是些孤独的灵魂,我在观察他们能否找到走出孤独的路径。因为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体验,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如何摆脱孤独并与他人建立联系。这很困难,也很棘手。这是我们所渴求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分享,也在生活中与之斗争。
南方人物周刊:提及《刺猬的优雅》结尾,有评论者指出,勒妮最后的意外死亡,是因为你也不知道那种超越阶级和文明的爱情和友情是否会有结果,对此你如何回应?
芭贝里:说实话,关于勒妮,我收到无数读者来信,差不多可以填满一个小书店,太令人震惊了!这些信件,有的非常友好、充满善意,有的表达了他们的极度失望,有的甚至指责我是个“罪犯”,因为他们太爱勒妮。我也读到过讨论超越社会阶层的爱情不可能,但这不是真的,事实是,所有人最后都要面临死亡,我笔下好多角色在小说结尾都死了,我觉得这就是人生。

生命中最重要的任务是获得自由
南方人物周刊:新书《狐狸的灼心》与之前的《我将一生赠予你》有相同的故事背景,你为何要反复写日本父亲上野春和他的法国私生女罗丝的故事,希望借此探讨某些社会议题?
芭贝里:与其说社会议题,不如说我想探讨的是心理议题,两种情况引发的思考都很吸引人:如果你的父亲缺席不在身边,你如何长大成人?如果不能看到自己的孩子,你又如何做一名父亲、在没有任何回报的情况下毫无保留地付出和给予?为了理解这些,我创作小说,落笔前我必须弄明白一些东西。
我最初写《我将一生赠予你》,是关于一个14岁年轻女孩的故事,她由法国母亲抚养长大,得知自己的日本父亲去世后前往日本。她从没见过他,对他一无所知,因为母亲不想让他们父女相见。她在京都呆了一周,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她不断学习去理解过往、去原谅自己的父亲,并在京都与一个男人坠入爱河,曾经遭遇的挫折转化为爱情。写完这本书,我很高兴,但很长一段时间,那些角色始终萦绕不去,我终于明白,这个故事我还没讲完,所以选择从父亲的角度来叙述同样的故事,并将时间往前推移,《狐狸的灼心》就此诞生。这两本书密不可分。《我将一生赠予你》中,父亲缺席,罗丝在场,我们通过法国人的眼睛来看这个故事;第二本书《狐狸的灼心》,女儿缺席,我们试图通过她父亲这个日本人的视角来看整件事。这有点像某种镜像对照。
南方人物周刊:从《刺猬的优雅》到《狐狸的灼心》,小说中的女孩都需直面原生家庭的创伤,你觉得女性当如何冲破并超越原生家庭的创伤,真正成长并站立起来?
芭贝里:确实,我的书中经常有年轻女性寻求解放的历程,无疑,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获得自由。我会再次搬出斯宾诺莎的话:去理解。我们探索、阅读和思考,与人联结,试图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文化,在各种书籍和声音中与他们对话,并尽力推动事情向积极面前进。我认为反思和分享是解放男人、女人、每个人的最佳方式。
南方人物周刊:在《精灵的生活》中,你又一次写到不同背景的女性的友谊,你如何看待女性之间的这种友谊互助与双向治愈?
芭贝里:这是个好问题,还没人问过我。其实很久以前我就知道自己想写关于友谊的书,但最后友谊会如何发展却不得而知。我与少数女性朋友之间的友谊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她们中的一些人我们已经认识几十年了,我们彼此分享了许多经历,我们没聊什么女人的事,我们只是谈论男人,(笑)关于亲密关系中令人生气的各种矛盾等等,我认为女性友谊中有种非常原始的东西,她们必须互相帮助,才能面对她们不得不面对的一切,我和这些女性是生活中共同前行的伙伴。其实我也想写下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之间的友谊,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描绘出那种理想的友谊,相信有一天会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