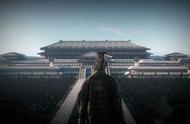《勃朗宁诗选》,[英]罗伯特·勃朗宁著,汪晴、飞白译,海天出版社
纳博科夫(1899年4月23日)
《洛丽塔》
如果仅仅看《洛丽塔》的故事简介,那么无论你喜欢还是厌恶,可能都将从情色的角度阅读这部小说了。事实上,纳博科夫的态度是严肃的。在男主人公亨伯特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欧洲文学史上一长串浪漫主义的男主人公形象,从痴恋朱丽叶的罗密欧,到少年维特,再到普希金笔下玩世不恭的叶甫盖尼·奥尼金,即便是花花公子的做派,喜欢上的女人倒是一律秀外慧中的传统纯情少女。然而亨伯特所面对的女人,却是一个12岁就把床笫间的男女情事当作游乐场那么随便玩儿的美国小女孩。亨伯特起初提心吊胆的那种道德压力,亦即当年《红字》中海丝特所不得不承担的道德十字架,在刚刚过去一百年后,就变成了一出错位的喜剧。与莎士比亚以喜剧写悲剧恰恰相反,纳博科夫是用悲剧的态度来面对人间喜剧的,而这正是纳博科夫能比同时代作家更上一阶的地方。

《洛丽塔》,[美]纳博科夫著,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布尔加科夫(1891年5月15日)
《大师和玛格丽特》
“假如像布尔加科夫和普拉东诺夫这些作家的作品,写完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我们所有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金蔷薇》的作者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临终之前曾如是说,言语之中不乏惋惜。布尔加科夫花费十年之功写成的巨著《大师与玛格丽特》,是在去世整整二十六年后才与读者见面的。这个魔王撒旦拜访莫斯科的故事,如此诙诡幻怪、绮丽奇特、举重若轻,那种幽默而不失从容的行文之下,处处潜藏着象征、隐喻、反讽、荒诞,又处处指涉现实,精妙绝伦,令人拍案。布尔加科夫被后世戴上了一顶“魔幻现实主义鼻祖”的桂冠,以至于马尔克斯不得不以祖母的名义发誓说,自己之前从没有读过《大师和玛格丽特》。

《大师和玛格丽特》,[俄]布尔加科夫著,曹国维、戴骢译,漓江出版社
阿斯塔菲耶夫(1924年5月1日)
《鱼王》
这位出生于西伯利亚一个农民家庭的孤儿,品尝过流落街头的艰辛,在二战中受过重伤,退役后做过形形色色的底层工作,然而生活里的苦难并没有马上转化为文学上的才华与声名,阿斯塔菲耶夫是在灯火阑珊处越写越得心应手起来的。人们往往望文生义地以为“抒情”即是优美,是鸟鸣山更幽,然而阿斯塔菲耶夫抒的是苦难,是长歌当哭。在“征服大自然”的社会建设中,作者眼睁睁看着“我可爱的土地”只是被破坏、损害、践踏、摧残,人变得愈加思想复杂,“仿佛人人都中了蛊毒”,和自然界失去了任何有机的联系,郁结之气,沉积于胸,形诸文字。阿斯塔菲耶夫是“大地之子”,故而《鱼王》中沉郁滞重的抒情,有着“万窍怒号”的震撼性力量。《鱼王》这首“俄罗斯田园颂”,不是王维式的,而是杜甫式的(阿斯塔菲耶夫非常喜欢杜甫),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强大而有力的悲伤。

《鱼王》,[俄]阿斯塔菲耶夫著,夏仲翼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巴尔扎克(1799年5月20日)
《高老头》
但丁似乎对人类生活毫无兴趣,他的“神圣喜剧”目光只打量地狱、炼狱和天堂这类见不到人的去处,大概有人的存在就难称神圣吧。巴尔扎克将其全部作品命名为“人间喜剧”,他的故事里全是一片发酵的人世间的*嚣*。波德莱尔那句“我爱你,臭名昭著的城市!卖笑的、逃缉的,自有他们的赏心乐事”,是巴尔扎克笔下巴黎最贴切的题记。他的代表作《高老头》,仿佛是对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的重写,但莎士比亚是黑白的,巴尔扎克是彩色的,莎士比亚笔下是灵魂的悲号,巴尔扎克笔下是*的挣扎。巴尔扎克明白,他本人是色彩大师,描绘巴黎的光怪陆离,由他出马比谁都更为合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