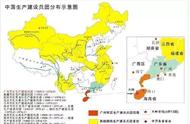刘烨在《琥珀》 新华社记者王建华摄

袁泉、刘烨在《琥珀》 新华社记者王建华摄
上观新闻:您在《悲惨世界》台词特别多,一上场就是8页纸,早上5点开始背台词。有观众开玩笑说您应该上《最强大脑》。
刘烨:导演选择大段台词还原小说情景。当然我们也不能全部都演,否则演完雨果一本书可能要10个小时、15个小时,我们选择书中的一些观点,这对我来说是个挑战。小说背景描述很长,我需要不断跳进、跳出角色,给观众完全不一样的体验。观众看《悲惨世界》是一种放松,也是一种修行。
演电视剧、电影还是话剧,没有太大区别。它们有最重要的共同点,贯穿所有表演形式的就是真诚,不管演什么都要真诚。话剧要注意的是,肢体、表情、台词可能要夸张一点,因为舞台与观众席有距离,但是演员的真诚一模一样。
上观新闻:都说表演是真听真看真感受,这么多场话剧演下来,您会不会“麻木”,需要用技巧去调动情感?
刘烨:态度特别重要。这个剧需要我有时在演,有时候又要讲给观众听。如果我单纯地背台词,不够投入剧情,观众能一眼发现,感觉到不同。
这是演员的态度问题,认真演出,真的很累。比如下半场开始,观众陆续从场外回来,可能有20%的人动作没那么快,我已经开始对着他们讲述了,我有意识地停顿,等他们全部坐回座位,再讲下一句。观众也许认为演员忘词了,其实不是。
我也遇到过观众在开场前发生小争吵,开场了,我不讲话,就站在台上,等一切恢复安静再开口。台上停顿是蛮可怕的,需要演员有强大的心脏,“逼”一千多人坐着盯着我,这是舞台有魅力的时刻。
上观新闻:如果您觉得观众应该笑的时候,他们没有笑,该悲伤时没有悲伤,您会感到挫败吗?
刘烨:我不会。如果演员与观众纯互动的话,感觉话剧变成了相声,要掌声,要反应。我们还是在做一个完整的剧目,演员有自己的节奏。巡演每到一站结束,我们会检讨自己的表现。有时候,舞台上“拖”五六秒钟,物理时间很短,心理时间极长,我们可能调整一下节奏。其他部分,只能相信演员。到了台上,演员主宰一切,包括导演在内的其他人都不存在了。
来上海前,我们因为春节那几天排练中断了,大家回家过年,走亲戚。我和我太太带着孩子去度假,不像一月初剧组在苏州合成以后,到北京演,一直在话剧的节奏中。所以春节后首站上海,宣传活动一结束,我们当天就到上海大剧院排练,跟大伙说,“好呀,都紧张起来了”。要等最后一场演出结束,我才敢说成功,因为每一场面对新的观众,要对得起这些观众。
上观新闻:您主演过话剧《琥珀》,每一轮都是五六十场,汲取到什么经验吗?
刘烨:《悲惨世界》190分钟,《琥珀》135分钟,时间短了很多,不过《琥珀》11幕,我有9幕在台上,时时刻刻也是压力巨大。
时隔12年,我重回舞台,刚好也是十二生肖的小轮回。我需要在12年之后重新锻造自己。这么多年,我在影视剧表演投入更多,但我是学戏剧出身,对戏剧有一种没登过台的人理解不了的热爱。话剧带给我很多自信,让我重新成长。
我现在的年龄,碰到突发状况不怕了。上回《悲惨世界》演出,有一个麦克风坏了,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看得出有点慌,好在我现在四十几岁,过了四十不惑,思路更坚定了。个别演员受影响没关系,我作为主演,要把自己的相信与坚定传达给大家,掌控全场。
是夫妻,还是合伙人
《悲惨世界》是刘烨与妻子安娜伊思·马田首次真正以合作者的身份共同工作。妻子是该剧总制作人,也是他每次表演的第一位观众。刘烨说,“这次合作让我从我太太对工作的敬业和专注中发现了她不一样的美。”
上观新闻:安娜伊思·马田提到,她虽然看您演戏,但不太提意见,怕影响到您。她说,演员非常脆弱和敏感,所以话剧最终靠导演与演员去磨合。
刘烨:排演话剧,我太太做了挺多工作,因为她的中文和法文都好。我们不但是夫妻,还是合伙人,有自己的优势。剧组有大量中方和法方工作人员。我和我太太在一起18年,我特别懂法国人的表达方式。他们说话经常带着手势,我知道手势背后想表达什么样的情绪。我就和中方工作人员说,“你看,导演现在在给我们讲什么,包括他用一些像诗一样的语言。”
我和我太太真正合作的时候,更加发现对方身上以前看不到的优点,是一次非常美妙的体验。她看到我站在台上,可能也重新认识了我。

2023年7月,刘烨与安娜伊思·马田出席《悲惨世界》北京发布会。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上观新闻:《悲惨世界》从萌发想法到最后落地演出,您和妻子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刘烨:我们是完全原创,最开始剧本选的是雨果儿子的作品。导演来中国之后,我们重新创作,从规范的中文翻译本里选取语言,构成剧本。整个创作方式独一无二。别说从法文到中文了,中国南方北方的表达方式都不一样。从法语翻译过来的剧本,我们尽最大努力保留原汁原味的雨果。
我来演,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被冤枉,我会怎么样,愤怒悲伤时,我会怎么样。不同艺术版本之间肯定有对比,我不担心。作为中国创作者,我挺有成就感。中法合作,我们自己的元素也要很强烈,才能对得起“合作”概念,不是去迎合,而是合作。
剧里冉阿让一直在原谅,一直在宽恕。有时,我和我太太聊,家庭生活会有各种各样的小事,我会向她吐槽,某某事怎么这样啊,然后我们就会聊起戏,冉阿让遇到这种事会怎么样。

2024年2月底,刘烨与妻子在上海宣传《悲惨世界》
上观新闻:您觉得法国观众会怎么看刘烨主演的《悲惨世界》?
刘烨:我是中国人,我在表达愤怒,表达原谅和爱的时候,有着特有的东方文化,这是这版《悲惨世界》的最大特点。我们把话剧作为一个礼物,用中文去法国人民剧院演出,明年计划在巴黎歌剧院与蒙彼利埃戏剧节演。
北京首演时,让·贝洛里尼导演的父母专门从法国飞过来看戏,看完特别激动,他们理解每个角色。不管换成哪种语言,话剧讲的都是人的事。法国观众不需要去看翻译字幕。他们对雨果作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熟。
我们先选择《悲惨世界》,让法国观众对中国戏剧团队有了解,在真正的大众市场建立起信任。他们接受中国团队的演绎后,我们再有新作品,他们会主动去了解故事背景,我觉得得一步一步来。
上观新闻:去年7月,观众在上海YOUNG剧场看到诺一与霓娜演的话剧《本草纲目》,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和妻子把孩子也送上舞台,接触戏剧艺术。
刘烨:我的两个孩子对我的了解,最多的是电影、电视剧,他们从小有先天的熟悉感。我的妻子一直参与舞台工作,她创作、唱歌,也表演。小朋友有机会成立自己的剧团,我觉得挺好的,除了日常的生活、学习之外,让他们的思维能够更拓展。
不管戏剧还是音乐,小朋友能站在舞台上,都挺不容易。我闺女第一次正式上台才八九岁,面对一千多观众表演,锻炼她的小心脏。
珍贵无比又小心翼翼的共鸣
少年成名,人到中年,刘烨对于名声、职业的认知,有变化,也有不变。他说,“演员被观众环绕,讲自己的感受,表达生活中羞于表达的愤怒和热爱,大家共同完成某种情绪,珍贵无比又小心翼翼。”
上观新闻:您提到,现在的戏更像是对自己某一时期的一种纪念,自己干过的事儿里面,能被深藏心底去记忆的,其实不多。回顾从艺路,您觉得现在算是成熟的中年人了吗?
刘烨:我是中年人,但成不成熟,我不知道。2000年刚出道那会儿,我年纪小,拍了电影,会觉得自己当明星了。我当过不少年明星,谁都想一直拥有艺术青春,时间能更长,希望有观众的认可,我也是如此,但是没像22岁中戏刚毕业的时候那样强烈了。那时和现在很多东西完全不一样,因为一直在变嘛,一直在往前走,演员要适应不停变化的环境与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