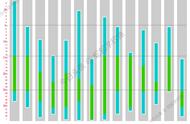恳请您点击右上角,订阅“媒介之变”的头条号。
白惠元

在少女电影的双主体场景中,如果女观众的凝视是自由的,那么,她们究竟会把谁投射为理想自我呢?这是一个有趣的命题。《少女哪吒》、《左耳》、《七月与安生》三部电影主力塑造的人物形象存在着高度相似性,即叛逆少女。这一形象序列也成为近年中国少女电影的主要文化症候,其中投射出新一代电影观众的认同焦虑。在这三部电影中,少女们不是生来叛逆就是渴望叛逆,她们与父母的关系是持续紧张的。李小路和王晓冰是因为相似的叛逆性格才相知相惜,李珥为了做“坏女孩”甚至把自己活成了别人,而七月与安生更是完成了叛逆生活的互换,总之,“叛逆”成为她们共享的精神特质,并具象化为一个中国古典文化符号——哪吒。
作为印度佛教的夜叉神形象,哪吒是中国神话的外来者,而他如今头戴乾坤圈、臂绕混天绫、脚踏风火轮的形象,则是佛教中国化乃至佛道融合的结果。哪吒的梵文全名是那罗鸠婆(Nalakūvara或Nalakūbala),也可译作“哪吒俱伐罗”,他是北方毗沙门天王的太子,职责是守卫佛法,保护世人。据刘文刚考释,哪吒形象的中国化过程主要经历了三次演化⑩:第一次是在南宋时期,由于李靖演化为毗沙门天王,哪吒也就成了李靖之子,获得了中国血统;第二次是在《西游记》中,由于李靖再次演化为道教玉皇大帝的天兵统帅,哪吒也就成为了孩童神,他的形象是外道内佛的并置状态,其本相依然是三六头臂、莲花化身的佛教夜叉神;第三次是在明代通俗小说《封神演义》里,哪吒的起源又被改写为道教灵珠子转世,至此,哪吒终于演化为纯粹的道教神。虽然哪吒最终完成了中国化,但是他的名字仍保留了梵语的外来痕迹。换言之,当我们把少女形象定义为“哪吒”时,我们的文化潜意识依然将其指认为他者,或者说,是指认为某种异己的力量。这种文化距离感是十分微妙的,也是值得深思的。
电影《少女哪吒》对“哪吒”符号的征用,主要集中在他剔骨还父、割肉还母的故事上,其文化内涵是叛逆之子。在小说《西游记》里,这个故事的经过是:哪吒年幼任性,大闹龙宫;父亲想*哪吒,哪吒十分愤怒,一气之下剔骨还父、割肉还母;佛祖借莲花之气将其化身再生,并亲自出面,调和了父子矛盾。而在小说《封神演义》里,哪吒对儒家孝道的反叛性被消解了,他剔骨肉还于父母的真正动机是“不累双亲”,因此,哪吒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也逐渐被改写为孝子。梳理“哪吒”演化史的必要性在于,我们必须明确电影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文化符号,具体使用的又是哪一段故事。显然,《少女哪吒》追求的是一种更为决绝的反叛,是精神上的“孤儿”。从小说到电影,创作者的立场态度是更接近《西游记》的,甚至走得更远:
我却明白晓冰。她像哪吒,剔骨还母,彻彻底底自己把自己再生育一回。只是她能力有限,没办法把自己养育得更好。{11}
从哪吒神话到《少女哪吒》,主人公所面临的代际情境已然发生了变化。从家庭结构上看,神话里的哪吒还有两个哥哥,他诞生于传统血缘家庭,他的愤怒、仇恨与毁灭性是异质性的,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反观近年来的“少女哪吒”,她们置身于现代核心家庭,而且大多是婚姻破碎的单亲家庭,这构成了原初的、内生的创伤体验。对于现代核心家庭而言,父母的离异通常以争抢孩子抚养权告终,而在被争抢的过程中,孩子对双亲的信任感都将消耗殆尽。于是,孩子只能相信自己,自我的封闭性也就越来越强。王晓冰父亲出轨,母亲抑郁,所以她想参军,她无时无刻不渴望逃离那个原生家庭;黎吧啦和奶奶一起住,双亲完全不可见,她因而成为了不用上学的酒吧歌手,她所歌唱的自由无拘的“蓝莲花”就是她自己;安生的妈妈常居国外,偶尔回国也异常冷漠,母女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这让她从小就习惯流浪,她从不相信自己可以有所依靠。

以上种种破碎家庭的创伤体验,或可看作“独生子女一代”{12}的情感结构特征。在《少女哪吒》、《左耳》、《七月与安生》这三部电影中,六位女主角全部都是独生女{13},这绝不是偶然。在中国,独生子女一代大多具有城镇家庭背景,从小衣食无忧,因而将注意力更多地投射于自我,关注“存在”的意义。从小到大,独生子女一直是家庭的中心,一直背负着父母双亲的外部期待与情感负荷,因此,其自我价值实现总是受到诸多制约。独生子女一代最爱追问的对象是“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或许是少女电影在近年中国市场中逐渐崛起的社会现实基础。当然,一旦人的内在自我过于强大,其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冲突就会放大,而独生子女一代的外部世界首先就是家庭和学校。在这些电影中,学生(主体)与学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总是处于一种持续的紧张关系,而独生子女一代的学生身份则凸显了青春期的重要性。作为一种话语发明,青春期一方面将少男少女的叛逆行为合法化,另一方面又将这种抵抗性放置于成长论的视野之内,将其降格为终将消逝的荷尔蒙冲动。如果说,哪吒本是依靠宗教力量再生于世,并与世界和解,那么少女电影则是在现代性的时间之维上改写哪吒神话——从七岁孩童变成青春期少女。哪吒的前世与今生被*为同一个少女的青春期与成年,在“长大成人”的*面前,青春期只是“不够成熟”的病态。这才是电影里的安生从四处流浪到回归家庭的内在逻辑。
既然哪吒被改写为青春期少女,那么其生命状态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只是年龄上的。作为神话故事,“哪吒闹海”的重点是“闹”,这一动作依然是充满孩子气的,是孩童对成人世界的游戏或恶作剧;而少女哪吒的核心动作是“流浪”,她们渴望走出封闭的生活空间,奔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因此,若要深度讨论少女哪吒的精神内涵,则不可绕过她们的生活环境,也就是小镇。无论是《少女哪吒》中的“宝城”,还是《左耳》中的“铜陵”,又或是《七月与安生》不曾说出的“镇江”,皆是典型的小镇空间。进一步说,“少女哪吒”其实是“小镇青年”形象序列的一个分支,她们的反叛对象不只是父母双亲,更是小镇空间。
在使用“小镇青年”之前,我们必须明确这一群体近来受到持续关注的根本原因:“小镇青年”首先是电影受众意义上的经济事实。随着中国三四线城市的地产开发,地方影院数越来越多,同时,“80后”、“90后”日渐成为文化消费的主力,这使得“小镇青年”崛起为中国电影市场的“新观众”。新观众必然形成新审美、新趣味,于是,“小镇青年”又成了某种不雅品位的代名词。究竟该如何描述“小镇青年”的审美趣味?张颐武将其阐释为中产群体布尔乔亚与波西米亚的两面性:“一方面是要布尔乔亚的俗世成功,现世安稳,通过力争上游来获得现世财富和事业的成功;另一方面则要波西米亚式的反庸俗,要的是愤世嫉俗的反叛和对于俗世日常生活的厌弃来追求某种超越的价值。”{14}正是在“庸常”与“脱俗”之间,我们得以更为准确地理解少女们的反叛性。王晓冰热爱阅读三毛却走不出家门,安生流浪多年却终于回归,说到底,她们的“超越”只是一种文化姿态。
同时,小镇作为一种叙事空间,仍是基于消费主义和资本逻辑的选择,它流露出创作者逃逸历史的冲动,这和《情书》的文化症候性如出一辙。正如邱静美所言,小镇不只是地域景观意义上的城乡结合部,更是一种寓言性的空间:“小城镇显示出一种中间性,有一种凝固状态,而非快速地顺利地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从这一意义上讲,小城镇叙事与其说是体现地域意识,不如说它们是以一种‘慢下来’的方式,在高度浓缩的现代化中缔造了空间,为正在被湮没的对真诚的渴望进行‘悼念’,让作者和观众面对内心成长的坎坷故事,在新的大历史的景观外进行自我日常书写。”{15}当少女遭遇小镇空间,我们终于得以体认“哪吒”的危险性:少女哪吒不是小镇空间的绝对他者,而是一种内在的他者,她们爱做梦的、不安分的生命形态恰是对小镇沉睡状态的破坏。她们是秩序的扰乱者,她们必须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