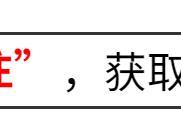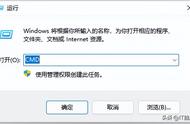在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1#竖井内,工区技术主管唐健查看隧道岩层。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
工作服洗了晒、晒了湿,不到半年就从深蓝色变成浅蓝色,掘进的速度却异常缓慢。唐健记得,哪怕24小时不停施工,一个月也才向前10米,蜗牛一样往前爬。“正常来说,700多米的隧道只需要三四个月。”唐健说,这条通路却已经修了5年。
工人们必须格外小心,2018年,竖井已经挖到了640米深,突然出现一个碗大的溃口,水汩汩往外冒,14个小时就从井底淹到距离井口5米,项目部用了一年多才清理好。
他们遇见过大型机械设备无法直接挪到井下的情况,只能把它们拆成一个个零件,到井下再组装;也遇到过岩层破碎的罕见困局,专家会开了一场又一场,烟抽了一根又一根,白发长了一簇又一簇,办法总能找到。
往隧道去的通路有4条,都在山体里。其中两条是跟隧道垂直的竖井,一条是带点坡度跟隧道侧面相连的1#斜井,凭借3.85公里的长度跻身国内最长铁路斜井,还有一条是隧道的出口端——工人们只能坐在铁皮焊成的简易火车上,摇晃40多分钟抵达作业面。每处通路都是这样一点一点费力挺进的。

每天7点20分,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出口处,早班施工人员搭乘铁皮小火车进出施工现场。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斜井所在的点位在开挖前甚至没有通车的路,六七十个人带着定位仪,沿着河道来回徒步施工,晚上睡在帐篷里,渴了就煮河水,3天修出了6公里,带子一样缠在山上。后来,运送材料的大车把路面轧得坑坑洼洼,工人驱车上山只能一路颠簸,急弯一个接一个,稍不留意就可能冲下旁边的悬崖。从这里去最近的村镇也要一两个小时,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工地上的人绝不轻易外出。这是工地上的“围城”:“出去了就不想回来,回来了也不愿意出去。”
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由云桂铁路云南公司负责建设管理,中铁隧道局承建,工程项目经理部首批参建员工从2015年11月28日开始进场施工,直到8年后的2023年12月,才将这些有辅助通路陆续修好,全部转入隧道正线施工。
2020年6月23日,1#斜井成为第一条跟隧道正洞贯通的通路。项目部的员工们特意在昏暗的隧道里扯了横幅合影,也在外面摆了酒。酒是动工前在洞口挖了大坑埋好的,每到一个节点,他们都要挖点儿出来庆祝。
那天也是项目副总工程师贾建波印象最深的一天,尽管他并不在现场。贾建波觉得这毫不矛盾:“这么长的隧道,其他入口都那么难,就只有那一个点位还算顺利。实现了一个阶段性目标,大家都很激动。”

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1#斜井因为内部高温,洞口飘出白气。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一场冒险
哪怕是最顺利的点位,掘进也耗了4年。
“跟我们设计好的完全不一样。”从业20多年,贾建波从没见过这样出乎意料的情况,按照惯例,设计单位给出图纸,施工单位照着做就好了。图纸上写得很清楚,通路和隧道的围岩硬度还算不错,工程师们也很乐观,很有信心。
“第一任项目经理还说,我们最多五六年就把它干通了。”贾建波说,谁都没想到,高黎贡山的地质条件这么复杂多变,真正的山体几乎每米都在变化:“前一炮岩石挺好,后一炮岩层就烂了,出水成泥了。”
1#斜井工程部部长王欣也头一次碰见这种情况。“别的地方再难干,最起码打出来的还是石头。”他在这里最常见到的“石头”像柔软的豆腐,用手一捻就碎,很难撑住。
从没想过会出现的最为破碎的围岩,则跟脓包一样,已经将国内最大直径硬岩掘进机(TBM)困在隧道里两年。专家们给这些岩层起了个独属的名字——大规模高压富水泥化沙化花岗岩蚀变带。

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1#斜井,工程部长王欣查看隧道岩层。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
每次掘进都是一场冒险。其他项目可以每次爆破三四米,在这里,一次最多推进1.2米,有时则只有0.6米。
裂缝的破碎岩体里是丰富且高压的地下水,雨林一般,从头顶和两侧墙壁往外流,在地面汇成小溪。有的地方湍急、没过小腿,因为混着水泥和砂石而浑浊,施工者们看不清地面,行走只能缓慢且谨慎;在清澈的地方,工人直接用它涮沾满泥浆的雨靴,泥罐车司机则掏出一块抹布,沾水擦拭车头。日积月累,一些墙壁被富含矿物质的水流冲刷,生出了红棕色的印记,长出钟乳石样的石头。
北方人王欣很喜欢云南的气候,四季如春、全年温润,空气里都是植物的香气。但隧道里却异常潮热,光是站着就冒出一身汗。穿着雨衣干活不方便,每次进入隧道,王欣都做好了全身湿透的准备。
这些水最热的时候,让隧道内的气温升到42摄氏度,即便是夏天,洞口也呼呼往外飘白气。冬天工人们穿着棉袄出工,一边往里去、一边热得脱衣服,口罩戴不住,每天都有中暑的人,伴随着眩晕、呕吐的症状。
项目部购置了两台大功率制冷设备,还有不少防暑降温的药品,甚至在工地附近建了一座制冰厂,每天生产60吨冰块运进隧道,直到把环境温度降到28摄氏度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