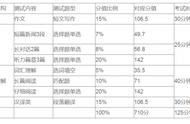作为剧作家的布莱希特是著名的“间离理论”的创造者,有些戏剧首演时即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而作为诗人的布莱希特则相对低调。不过时至今日,他那些朴素、直接的诗句成为他洞察力与勇气的最佳证明。他在诗中讽刺希特勒为“粉刷匠”;他在二战爆发前几年就说“当德国武装到牙齿/大祸便要临头”,“战败国的底层人民/挨过饿。/在战胜国/底层的人民同样挨饿”;他写下自己的流亡历程,就像在为无数和他一样的流亡者保存一份证据。
他意欲提醒所有人,那是一个“被恐惧扭曲的世界”,不要被骗。其实他的愿景很简单(简单的事物往往最珍贵),就像他在《孩子们的心愿》一诗中所说:生命不该是一场惩罚。是的,无论如何,都应如此。可惜,人世并非如此。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年4月12日专题《生命不该是一场惩罚: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中的B06-07版:
B01「主题」生命不该是一场惩罚: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B02-B03「主题」布莱希特 恐惧驱使我走向书桌
B04-B05「主题」流亡中的布莱希特与中国
B06-B07「历史」图中画里寻宋风,谁人识得君王面
B08「文学」《夜奔》 向每一个逆时代而行者的致敬之书
撰文|程一身
我对布莱希特的第一印象并不算好。
我是从《本雅明传》中读到他的,在他和本雅明不平衡的友谊中,他显得很强势,常常像老师训斥学生一样对待本雅明。由于我热爱本雅明,便觉得布莱希特这个反专制的人在某种层面上看就是一个专制者,至少有一种导师倾向,毕竟他在剧团里经常指导演员工作。在《斯文堡诗集》第一部题词中,他坦承自己是以教导为业的人:
“倘若我们重逢/我愿意重操教导的旧业。”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德国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导演、诗人。生于奥格斯堡,1933年后流亡欧洲大陆,1941年前往美国,1947年返回欧洲。1949年起定居东柏林,创办柏林剧团。
“他的诗如同提前写好的挽歌”
布莱希特的戏剧影响很大,他的诗歌只是最近才在中国被广泛阅读、引用,似乎此前低估了他作为一位诗人的分量,目前布莱希特被接受的热度迫使评论家对他的诗歌成就进行再判断。在诗歌判断方面,布罗茨基一向非常自信。在《怎样阅读一本书》中,他列举了世界范围内的杰出诗人。关于德语诗人,他这么说:“如果你的母语是德语,我推荐的是莱纳·马里亚·里尔克、乔治·特拉克尔、彼得·胡赫尔和戈特弗里德·贝恩。”在这里,他没有提到布莱希特。在名篇《取悦一个影子》中,布罗茨基记录了他和奥登的一段对话:
尽管你最终可能会附和奥登本人的话:“我认识三位伟大的诗人,每一位都是婊子养的。”我:“谁?”他:“叶芝,弗罗斯特,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现在来看关于布莱希特,他错了:布莱希特并非一个大诗人。)
奥登在布罗茨基的心目中简直就是一个导师,也许当时布罗茨基附和了奥登的看法,但后来他还是没有认可布莱希特是个“大诗人”。可以说,对布莱希特诗歌的评价存在着这种不稳定性,在某些方面他似乎达到了大诗人的水平,但在其他方面他又很难被视为大诗人。

《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论诗和诗人》,作者:[美国] 约瑟夫·布罗茨基,译者:刘文飞,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版。本书收有文中提到的《怎样阅读一本书》。
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布罗茨基的看法。我认为布莱希特是三分之一个杜甫。他们都用诗歌及时记录并回应了时代,都有“即事名篇”,都属于即兴现实主义写作,但有两方面是杜甫有而布莱希特没有的。一方面是回应时代的艺术性,布莱希特是个朴实率真的写作者,他敏感地把握了时代的重大问题,不事雕琢地把它们直接写出来,如同脱口而出。后代读者认同布莱希特,是因为他说出的时代问题在后世重新出现,他的诗如同提前写好的挽歌,让那些有意说却不敢说的人心有戚戚:
这将是被谈论的一年。这将是讳莫如深的一年。老人看着年轻人死去。蠢人看着聪明人死去。大地不再孕育,只吞噬。天空不再下雨,只下铁。
《这一年》写于1940年,二战爆发初期,最后一节写的是战争对世界的残酷破坏,第二节写的是成批的青年人死亡,布氏之前的中文译者黄灿然把此诗的第一节译成“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这是人们说起就沉默的一年”,广为流传,因为它兼具寓言与预言的性质,适用于历史上的很多年头,这样的年头此后还会出现。1950年,汉娜·阿伦特赞誉布莱希特是“在世的最伟大的德语诗人”应与此有关,因为她是一个密切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