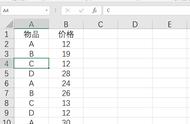外婆这一生居然收到过彭建的两次信笺,原来他一直活着。
第一次在中年,具体哪一年,外婆也不记得了。当时她激动得手都颤抖着,那信笺的封皮也早已污迹斑斑,因为信件辗转太多手,最终都无法追寻源头。信里只有寥寥几字:
“澜沧江畔,望北嗟叹,念君念故乡,终不得返,愿安好。”
落款是“彭建,于清盛”。
小时候我常常溜进外婆的房间,从她古老的梳妆台抽屉的铁盒子里翻出那封泛黄的信来看。我感兴趣的是信纸背面一个男子的扫描画像,他很年轻,带着眼镜,身上挂着很多勋章,表情冷峻,尊贵异常。我觉得他简直就是白马王子。
“他就是彭建吗?”我问外婆。
“不,他不是。”
“那他是谁?”
“我也不知道呢。”
“彭建也这么帅吗?”
“嗯……他经常笑,笑起来脸就跟大葵花一样灿烂。”
这时外婆会笑得特别开怀,仿佛彭建也是那样笑的。

80年代的某个盛夏,古老的大宅院又收到一封来自远方的信笺。
我从没见过那封信,外婆说弄丢了,信的内容大概是他在山坡上种了一片野菊花,每年等待花开,那一年也许等不到了。
署名的地方仍然是那个叫人陌生的地名——清盛。没有人听过那个地方,也没有人知道彭建后来过得怎样,是否有家人在身边,更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死的时候是否安详。
刚好就在我出生的月份外婆收到的信笺,所以她用他名字的谐音给我取名“初见”,当时只对别人说,名字取自诗句“人生若只如初见”,后来她在跟我讲故事的时候悄悄告诉我的。
外婆说过,她这一生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去一次他待着的那个地方,看一眼他种的那片野菊花,看他生前过得好不好,吃得饱不饱,曾经有没有冻着。
“清盛很远吗?有多远?有没有北京那么远?”我总是这样问外婆。
“应该很远吧,说是在澜沧江呢。”
“你要把我带上,我也想去看一看。”
“好呢,到时候就由你做我的拐杖。”
我们一次又一次约好了之后,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岁,我就把它给彻底忘记了。

03,守护野菊花的向日葵
外公身材很魁梧,性情却敦厚腼腆,他和外婆是在父母安排下以媒妁之言完婚的,他当初一见外婆就傻痴痴地随了她,一随便是一辈子。
外公比外婆大七岁,在我十来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所以我对他的记忆很有点模糊,感觉他一直都是老态龙钟、行动蹒跚的样子,整天除了整理院子,就是乐呵呵地坐在天井的柿子树下,我们在那里耍游戏,他宽容的目光洒在我们身上,而阳光洒在他身上。
外婆说,外公就像土壤一样温厚纯良,蕴藏着无与伦比的力量,明明留过洋,身上却没有丝毫洋气。
婚后,外公看外婆每日都要回大宅院护理菊花,于是亲手把那片菊花移至新家的院子里,还在旁边种了一排向日葵,像一排军队一样护卫着那些小菊花儿。他知道外婆很重视那些野菊花,所以他也一直像宝贝一样悉心照料着,一直到老。

外公走的那天,外婆很宁静,没有丝毫失态。
她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一边为外公装身,很仔细、很仔细的,一边像在跟他聊天一样,嘴里细细声地念念有词。
她在平日晒好了的野菊花中挑选最上好的一下扎,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擦得发亮的淡青色的小圆瓶里,剪一块小红布作封口,以红绳子仔细地打好结,放在外公的枕边。她还亲手去把开得正艳的向日葵摘了,剪好枝叶伴在外公身旁,漂亮极了。
办丧事是要哭丧的,姨妈姑姐们都在道士的指导下间歇性地嚎啕大哭,我妈也在哭,唯独外婆没有,大家哭的时候她就低头垂眼,默默注视着自己的手。
那天外婆几乎都是蹲在外公旁边折冥纸,应酬前来凭吊的亲友,偶尔轻轻整理一下外公的衣领、帽子,还有那瓶野菊花和向日葵,一样很仔细的。
我挨在她身边好奇地看她。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接触死亡,因为外婆,我对死亡没有一丝恐惧,更多的反而是好奇。
只见外婆整理好外公的帽子后,看着他的容颜,微笑着低喃:
“人生若只如初见……初见啊!”
她的声音比往常都要低沉,一个一个字说得极慢,最后的声音仿佛是一声无奈的叹息,又仿佛是圆满的感叹。
“嗯。”
我应她。当时我是纳闷的,不确定她是在对我说,还是对外公说。
丧礼的那几天我常常想起外婆说过,外公当初一见她就傻痴痴地随了她,一随便是一辈子,我突然对“初见”产生了怀疑,我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初见”是属于彭建的,也许我错了,也许“初见”还属于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