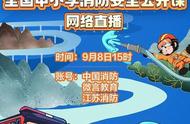干巴爹是庄子上的五保户,干巴爹是有兄弟姐妹的。
干巴爹像缺水受旱哂蔫了的茄子一般,长得很结巴。他的个头才一米五左右吧,到后来他老了的时候,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只老年的猴子。
干巴爹有两个哥哥,大哥最早是在大庆油田那边部队里当兵,并且还是一名军官,大哥的家属也早早的随军去了那里。二哥是生产队里的一名治保主任,说话办事在队里也是有权威的。就到了他这,情况怎就突然的变化了,这是谁也没有搞清楚过的一件事情。我们小的时候,常听得庄上大人们戏谑他是结不熟时,干巴爹则急急忙忙地辩称,那是他妈妈生养他之后,因家里穷,没有吃食营养,自己的奶水不够,才让他受了这委屈。
最早的时候,干巴爹和庄上所有人家一样,住在低矮的草屋里,那是他哥哥出门参军前留下来的两间祖产。平时,房屋因为缺少收拾,屋顶有几处滴漏垮塌的地方可见日光,而地上也是因为从不修整,也是凹凸不平。两扇破旧的木门裂开了几道大缝,活像庄南头四老太太脸上几条干枯的皱纹。干巴爹的床是用土坯垒成的,上面铺了厚厚的稻草,床顶上方有用坏破的薄膜展开在树棍之上,以期遮挡落灰。这屋破床散的光景虽然残败,但干巴爹却还是庄子上最早能穿得上一件中山装的人物。那是他在部队的大哥一次探亲回乡时特意留给他的。但他没能穿出它该有的样子,不是胸前总有滴上似洗不去的粥粘,或者是上一颗纽扣怎就纽在了下面的扣眼里面。
那个时候,大家的生活都很单调,乡亲们忙碌之余寻乐子,也都喜欢拿站在一旁的干巴爹说笑话。问干巴爹怎不娶个马马(媳妇)回来,干巴爹眼睛一翻回说,娶马马干嘛?累死个人了,多不值当,哪怕出个门,也要先给她挑上一担水才能走呢。人们问他想不想娶个马马,干巴爹这个时候便不会立刻回答了,而是脸上露出一丝苦叽叽的表情,谁都知道,干巴爹是想娶马马的。而马上,庄子上的妇女们马开玩笑说,干巴老爷,要不要我给你说个媒,我娘家那儿有个寡妇,人好还能生娃要不要?干巴爹马上红着脸说,好也,你帮我说说看。没一分钟,干巴爹又回说,我这死样,就怕人家看不上。干巴爹说了这话,引得大家一起哈哈大笑。干巴爹知道她们又笑话他了,脸一沉,悻悻的离开了。
干巴爹家的锅灶台几十年了都没有倒过。庄上人家一般十几年至少要把家里的旧灶台支一回,人们只知道干巴爹的锅,是一直没支过的。没有人因疑问而推开他那两扇木门,谁要是出于好奇探头向里面看个究竟,那屋里东拉西扯的蛛网必定会给进去的人,如戴上一个绵绵的头罩般难以脱解。干巴爹说屋里不掸尘,夏天连蚊子苍蝇都不敢飞进屋里去,只要有进去的,就会被蛛网给网住了。所以,谁也没见着干巴爹夏天买过一次蚊香,床上那顶比他脸皮还黑的蚊帐,都不知道是哪一年有机会亲靠过水了。
无论干巴爹有多不堪,其实,我们这些小孩子还是挺喜欢和他玩耍的。大概也只有像干巴爹这样的大人,才会不计时间的与孩子们撒闹的缘故。我们小时候,有时也有害怕干巴爹的,害怕他红红的头皮上只长了数得过来的几根头发。干巴干巴,我们这儿称呼干巴,不仅仅是对身体瘦小体弱者,还有是对满头生辣子的人也有这样叫法。所以干巴爹经常也有被人喊着为辣干巴这个令他恼火的称呼。叫他干巴,干巴爹一般不太会生气,只要你是个上了一点年纪的人,或与他年龄相仿的,他都乐于应承。但如果哪个叫了他辣干巴,性质就大不一样了,这多有骂人的语气,他是能够分辨得出来的。所以叫他辣干巴的人,大多会被他当面给骂回去,如不能当面反击的,他也会低下头背过脸,声音压在喉咙管,嘴巴则不停的叽咕六咕的骂着脏话。当然,人们都晓得他在这样的时候,是没有好话说的,祖宗八辈子基本上都被他拜托遍了。
干巴爹因为个矮力小,在生产队的时候,经常是把他派在了和老年妇女们一起干事情的行列。棉花田里摘摘棉花,或铲草皮挑挑猪方(有机肥),大家虽然有拿他开玩笑逗乐子,但做事情的轻重都会考虑到他的体力与体格。那时候,我爷爷是队里的饲养员,爷爷负责三条耕牛的饲养与看护,干巴爹虽然和我爷爷同属一个辈分,但我爷爷要比他年长四五十岁,他是懂得尊重老年人的,有次,我爷爷跟队长说了,让干巴爹随他放牛放一段时间,队上应允了。
从八几年起,家家户户都推倒老庄台的土屋,沿马路盖起了新居,干巴爹借得机会,托人把这事写信告诉给了他那已转业到地方当干部的大哥,他当官的哥哥得知情况后,则专门回来了一趟。他出钱找人给干巴爹盖了一间有十几平米的小房,门窗虽小,但总要比以前的环境齐正了许多。小屋座落在原房旧址上的边边上,与各家的新房是拉开了一长段的距离。干巴爹自从住进那间小屋,明显有觉得他并不很喜欢,他每天出早入晚,一个人常常是玩到人家点灯了,才见得他一个人往那条巷子里去。我父母健在的时候,数干巴爹来我家玩的最多,不论他没事专门来的,还是捧着碗转过来的,爸妈都会招呼他坐门口凳子上,或是家里也正吃饭,会给他碗里夹些肉菜,或是与他搭话。你别说,干巴爹他天天外面转悠,他的来路多,消息广,庄头人家的纠纷,北边田里的瓜事,他讲的神神叨叨的,妈妈也陪着他演,装着是不知道。干巴爹也很喜欢和我家两口子说话,他说我们夫妻俩人好,见到谁都是一脸笑,不似旁边人家的媳妇儿,眼界高,看不起人穷。干巴爹能说,说的话有一大半都是废话,一小半是无用的话,他的话里,隐藏着他的空虚与寂寞。自从干巴爹单独住在老庄台,我能晓得他为什么每天晚上都迟迟的不愿归家。真不知道,那么多寂寂长夜,他是怎样一个个挨过来的,只有他自己知道。
干巴爹拾废品了。自从分田倒户、分乡建镇,村里就给干巴爹弄了一个低保加五保户的名额。干巴爹没事干了,他串门子,可别人一家家的都关着院门,进去也不似以前的方便了。干巴爹闲得久了,就开始了捡废品的营生。我们的庄子是紧靠着集镇的,因为他的特殊形象,所以大家也都认识他是谁。他整天穿着不合身的脏衣服,一条与他个头差不多高的蛇皮口袋驮在他的身后,他似乎对一切都是很感兴趣的,地上的垃圾,天上的飞机,路上的行人,一个与这个世界来说,既微不足道又可有可无的人,一个卑微到如他自己捡到的垃圾一般平价不值钱的人,他在这个世界上能有什么作为呢?不过是占了一席地方,脏了一点空气,惹得一些口水罢了。他人看上去虽显愚钝,但他能知道自己的渺小。他总是走在马路的边边角角之上,他总是随时给别人哪怕是个小孩让路,只有看见被扔在地上的烟盒或他认为有用的东西了,才会小心翼翼地探出自己的身去,然后,低头弯腰把那个废弃物捡进自己的口袋里,他有时也会搞怪,把捡到的东西会反反复复的打量几眼,似乎是想要弄个明白手中的东西,怎会遭遇到如同自己一般的地步。他这种对一切事物都感同身受的作法,大概是对自己近乎一生的深深体会所至吧。
干巴爹也老了。这些年,干巴爹看上去老了许多。很多人是不相信干巴爹会老的,像干巴爹这种人,应该是一生都不曾年轻过,一生也不会变老了似的。干巴爹的老,老得有点滑稽。代表一个人的老,有从一个人的头发变白变得稀少,也有是看一个人的眉眼脸庞,还有是看一个人走路时的身形步伐。可干巴爹头顶上的头发早就一根没有了,他那张常年都不清洗亦从不漱口的脸,根本就看不清它哪里是皱纹哪里又才是划痕。大概还只是从他的步伐上,远远的你会觉得他移动过来的速度变慢了,活像一只什么灰头土脸的东西那样,再没有了原先的精神头。
干巴爹的废品卖不出去。近两年,干巴爹小屋周围堆满了各色垃圾。干巴爹他不知好歹,什么垃圾都去捡,这种不分门的作法,后果是垃圾站根本就不要他捡的东西。原先我听说了回收站不收干巴爹的垃圾,觉得一定是店家欺负他这人老实,后来听妈妈告诉我,干巴爹捡的东西远远要比别人的多,原因是他捡的,大多是别人都知道的真正废物。
干巴爹没有了这项经济来源后,我有替他担心过。但转念一想,干巴爹不识字也不识钱,他即使是去卖了废品,人家哪里会真正替他过一眼秤呢,都是给他拿来钱时,则是随意给他丢个三毛五毛的,算了事。
曾有过一段时间,我回家来的时候,多少天都没看到过干巴爹的身影。我问过妈妈,妈妈说,干巴住院了。干巴爹会生病,这事还真是挺新鲜的。干巴爹该是个五毒不侵的人,所有人都感觉像干巴爹这种人,身上所积攒的毒素轻轻松松就能毒死掉一条牛。就凭他七八十年身上没擦过肥皂,一口黄牙没沾过一回牙刷,那还不把天下的毒物都比了下去。还真是的,至少干巴爹这过去了的几十年时间里,没有进去过一回医院。我有想过,是凡干巴爹真的头疼脑热了,大概也只是自己一个人踡缩在自己的草窝里,忍着忍着也就过去了。
那次干巴爹住院几天,从医院回来之后,大家就开始为他操起了心。虽然他的二哥是住在同一个庄子上的,但好像对于他来说,并不会有多大的实际帮助。这几十年里,除了无偿的使用、或指派他去干什么,反而是干巴爹他自己离不开这种被利用才获取到的人生价值。我想,大概干巴爹自觉的价值,真是还有人需要他去干活由此而表现出来。这种被人使唤才能显示自己存在和存在价值的感受,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都太平凡、简单而近乎愚钝。
然而有一天,干巴爹的生活和想法还是被彻底的改变了。干巴爹进了养老院。养老院离我们庄子一公里路都不到。干巴爹被村里送到养老院去,起初他是不愿意也不习惯。他放不下自己那一间小屋,怕没人去照看,他也烦恼小屋周围那捡拾了大半年时间才积累起来的废品,最后将何去何从。他还想像从前一样,每天脚拖着球鞋走过村边,遇着谁了,先打上一句招呼,然后,等人家是否听见了,能回应他一声。他生活了近八十年的一个地方,仅离了一公里的路程,却不能轻轻松松地回一趟家。
干巴爹呆在养老院里,呆在一群没有儿女没有家人的老头老太太中间。他不愿给这些人打招呼,他也试图抬高一下身板以示自己比这些人能耐。他每天都郁郁寡欢。一个人坐在对着养老院大门口的那一级台阶之上,伸头望着铁门外的那个世界,那儿是他捡废品时经常来回走过的地方,既近,又是那样的遥远,远过这他将要度过的这一生,仿佛再不能到达。
干巴爹,名唤谈玉宏。一个被人们忘了近八十年名字,他人还依然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