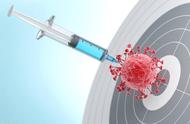这个名为“山居笔记”的专栏从2011年元月起开出,你的散文名篇《约会星鸦》《拍溅》陆续在《文学报》露面。后来我把你发在《作家》上的长散文《蘑菇课》推荐去了当年度在场主义散文奖的评选,我很高兴你得了奖,可见挑剔的评委认可你的文字。虽是单篇散文新锐奖,但那一届无论提名奖还是新锐奖,作者阵容都十分齐整,写作水准相当,应该说口碑和影响甚好。颁奖典礼在苏州大学举行,你转道上海特意和这个奖的媒体支持方、我们《文学报》的记者编辑汇合,我们同去苏州。之前你已在电话里大声强调:“你是我的恩人……”我一笑了之,没想到你真的以礼相待,行前说要给我带一盒林蛙油,你热切提醒:“知道那东西吗?美容养颜!……”我知道它的珍贵,可实在我是个很怕麻烦的人,尤其对山珍一类的稀有物,不知道怎么对付,给我简直是暴殄天物,于是坚辞婉谢,你急了,在电话里沙哑着嗓子嚷嚷,切成画面,就是一头想要知恩图报的狮子或大熊发出急切的呼吼。后来我从晓枫写你的文章里印证,原来你就是那样的人,“有什么好事总想着朋友”,“对人有种执拗的热情”,“总是热衷分享好东西”,“每年都打电话,邀约朋友同往(长白山森林)”。(周晓枫《森林里的老孩子》)我也因此知晓了你的性格和不幸的童年少年,热切总是和脆弱天真在一起,大大咧咧的豪爽和强烈爱憎是难兄难弟。你虽然顶着一个诗人、作家之子的称谓,可是因为右派下放的父亲和抑郁自*的母亲,你的童年和少年并不好过,你性格里的激烈执拗不管不顾和对灰暗地带的零容忍,你讨厌人群又渴望朋友、深居丛林又迫切渴盼他人认可的矛盾孤独……想必都是你的命运和人生。

你记了那么多森林笔记,可真正面对写作时却惜字如金,写得很慢,邱华栋说你每天只能写几百字。森林里的世界足够惊心动魄,可你按下性子不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其实你很急,你在日记里如实记下了对自己文字的不满、为修改好一篇散文结尾的反反复复以及盼着文章发表的度日如年般的煎熬。你多么慎待写作,几乎以生命般的热力全情投入不计成本。同样,你也尊重森林,每天的日记里都是你拍到和识得的各种蘑菇、鸟兽、花草,你陶醉其中,但是你只做一个记录者倾听者观察者,你小心翼翼避开正在喂食求偶歌唱昏睡的森林家族,大自然不是你攫取和猎奇的对象。
采摘蘑菇是例外——“晚饭吃青蘑(侧耳或美味侧耳),果然不错,清香肉厚,无异味。”“拍到一张好片子,夕照中原始森林一角,湿青苔上一树舌上有一只蜗牛。采到冻蘑、刺蘑,加入平菇可炖一锅汤,或炒来吃。”“昨天采的那一堆白色半透明的小蘑菇叫扁柄杯伞,也有清香气。”……几乎每天你的散步都有收获。读着你的日记,感觉是在纷披的菌类世界里穿行,记了这个丢了那个,单凭字面只能感受其香气和色彩……我这个发愿要写一本植物书的“伪植物迷”,看来即便森林向我敞开大门,也不能得其门而入了。

颊囊中塞满食物的花栗鼠
毫无疑问,你堪称博物学者,你通晓长白山森林里的上百种蘑菇,上百种鸟,还有数百种草木、灌木、乔木植物。你很熟悉帕乌斯托夫斯基、普里什文、梭罗、布封、艾特玛托夫这样一些大自然作家,对他们的作品了然于胸,你也渴望像他们那样去深入自然和荒野,你不满足于讴歌自然,更想以生态作家的方式思考和保护森林。对生态文学的思考,对环境问题的揭示,哈佛大学教授、生态文学研究专家布伊尔称生态文学是“为处于危险的世界写作”。你也说过类似的话:“当人类利益与野生世界发生冲突时,我永远站在野生世界这一边。”
对你来说,写作即命运,性格也即命运。两种命运相抵,时间不够。我接到你的最后一个电话,是你离世前几天,你来确认我一定要参加你作品的研讨会,我答应了。两天后,一样毫无征兆地,我收到出版社打来的电话,编辑女孩哭着说:胡冬林老师去世了……
这封信写长了。谢谢你妹妹来短信,虽然我们不认识,但仿佛相熟已久。经由你妹妹的整理,我并不觉得你的悄无声息,你写下的那些大自然的文字,不会随风消逝。而我的这封信,算是补上我的唠嗑。我愿意以半个同道的方式和你共勉:胡冬林,脆弱和天真永远是一个作家与命运同行的隐身衣。
断续记于2018年7月31日—8月31日,编后碎片时间。
本文发表于《作家》杂志2018年第11期
《山林笔记》选读
2010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