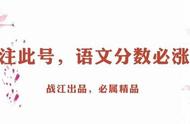草根——百度图片
第四节
粗糠难以下咽,哪晓得排便才是难题田里挖不到野菜会发愁,挖到野菜也发愁,因为没有油。
野菜吃多了会生病,但不吃就会没命。没有油也要吃,不吃就会饿死。
而最难吃的并不是野菜,却是那些谷物秸秆和谷糠!
我印象最深的,是吃大糠。那是公社的领导想方设法从外地协调过来的,分给大队再分给每家每户,我家分了一大口袋,要靠这袋大糠维持到麦收呢。
什么大糠?这糠有好多种,大麦脱的皮壳我们叫蓬糠,稻谷的皮壳分为米皮糠、细糠和大糠三种;米皮糠最好吃,它是靠近米粒的最里层脱出来的,米的糙皮和秕芽都在里面,这是最好的糠,吃起来有甜味,也有营养;稻壳和米皮混合加工出来的叫细糠,是熟米以外的副产品,平常主要用于喂猪,这种糠有点甜味,但也不能多吃,大便干结会把人撑死;而大糠则是稻谷最外层的,是粗糙的皮壳,几乎没有任何营养成份,比稻草秸秆好不到哪去,平常是用来作柴火烧的,拉着风箱烧火时,用手撒到锅膛里的,就是这大糠,实际上就是稻壳。这东西人怎么能吃呢?
但是,这年的春荒还真的要靠它来渡命呢。
妈妈把这大糠,放到锅里炒,炒到有糊味时,就知道已经炒熟了,接下来出锅,再拿到磨子上去拐。
这大糠太粗糙,嚼不动,吞不下去,需要在石磨上碾碎了,变成细糠一样,才能咽得下去。
妈妈把炒熟的大糠盛到簸箕里,两手端着,走到磨子旁边,准备上磨去拐,妈妈在后面抓着磨担准备拐,叫来大哥在前面往磨眼里喂。
我们都聚在旁边,闻到一种微微的稻谷的香糊味,盯着这个刚出锅的食物,等着磨碎了来填充我们饥饿难耐的肚子。
大哥走到磨子前面,伸手在簸箕里抓了一把大糠。我看到他并没有往磨眼里喂,而是猛地捂到自己的嘴里,费力地嚼了几下,就往肚里吞。
看着大哥被咽的脖子一伸一伸的,妈妈说,你等等嘛,等磨碎了再吃!
那么粗糙的大糠,没等到磨碎,也就是稻壳呀!不是饿到一定程度,怎么会咽得下去呢?
我没敢伸手去抓,等了一会,磨盘里已经有磨碎的细糠了,我去撮了一点,塞进嘴里,但光在嘴里打转,嗓子在硬顶着。但一转头却又吞下肚了,可能是肚子有一种强大的吸力吧。
接下来,次生灾害便发生了,我们几个全都拉不出屎来了,都在那里疼的光叫唤。
因为没有油水下肚,也没有别的食物平衡,光靠吃糠,大便干结是必然的,怎么使劲也拉不出来,肛门像是炸裂似的疼,上趟厕所就跟上刀山似的。但是,不上又不行。
实在是没有足够的力气来排便,走路的力气也没有。
从家里走到屋西边的茅坑,这是个大家都犯难的问题。我吁了口气,蹩足了劲,两手撑了一下,才从板凳上站起来。
从家里走到门口,得要用手摽住门边,才能抬步跨上门槛。再从门口走到茅坑,我挨着墙,用手扶住墙壁,慢慢地往前挪开步子,这上茅坑的路,距离总共十几步,我却花费了十几分钟。
我用尽洪荒之力,才走到茅坑边,努力蹲了下来,迎接那撕裂的痛感。
还是懂我的妈妈,她走了过来,让我趴在她的怀里,撅起小屁股,让她用手扣。那些屎橛子,干巴巴的,像铁蛋一样。
我痛得大叫,眼泪汪汪的,妈妈也心疼得眼泪巴巴的。
说来也怪,没粮的时候就没有油,这粮油怎么成为一家了。油,就是油脂,人体营养三大项,碳水化合物、蛋白和脂肪。吃野菜吃大糠,需要的就是油来滋润。没有油,这大糠比观音土还难吃。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大哥抓起一把大糠,没等得磨碎就往嘴里捂的情景,一直在我的记忆里定格,每次想起来,心里就难受。

大糠——稻谷的外客
第五节
河边水里,也能找到好吃的东西没有树皮和草根了,妈又想出了别的法子。妈想到了河里——河里有水生植物,应该有人能吃的东西!
妈妈不会游泳,可是她还是拖着病弱的身子下到了齐腰身的河水里,拿上一把长柄镰刀,伸手去割那些水里的漂浮植物。有一种水草,妈用手一掐,觉得很嫩,弄点回家去试了试,还行!
这种水草的叶子漂在水面上,圆圆的,有鸭蛋那么大,有海绵状的弹性,它的茎又细又长,一直拖到水底扎根,水流风吹,这根茎牵着叶子,就像一个个永不断线的小风筝。这种水草我说不准它的名字,它的学名可能就叫荇菜。
河水里还有别的好吃的。我们蹚到河滩的水里,发现几棵野生藁草,那是一种蒿瓜,也叫茭白。它们长在齐腰深的水里。妈妈用长柄镰刀在水下兜底一割,整个藁草就飘浮起来,妈吗用手把它根部的芯子剥出来,这就是又鲜又嫩的藁瓜了,妈妈把它们放到篮子的下面,带回家给父亲吃。
意外的惊喜也碰到过,是那次跟着妈妈到西河滩去,准备穿过芦柴丛,到河岸远一点的外滩,去看看有没有藁草。我跟着妈钻进芦柴棵的深处,听到前面有鸟的呱呱叫声,我们循着鸟的声音慢慢的摸过去,只听“呼哧”一声,一只大鸟扑着翅膀冲天而起,我仰着头看那飞走的鸟,惋惜得心都痛了。要是能抓住它该多好啊,能炖一大锅鲜汤呢。
我正在懊悔时,却听到妈妈惊喜的叫声。我一低头,看见眼前的芦柴稠密的地方,有一个大大的鸟窝,里面睡着十几个鸟蛋!乳白色的,上面布满灰褐色的斑点。“啊!”我又激动又紧张,胸膛里的小心脏在砰砰的跳。妈妈小心翼翼的将鸟蛋抓起来放到篮子里,我抖抖霍霍地拿了一个捧在手里,还热烫烫的呢!
全家因此好好的改善了一次伙食,大大的增加了一次营养。那是打了炖着吃的,里面加上半瓢水,这种做法,份量多,能炖出一大钵子来,虽然没有油,但仍然是鲜美异常。
这种喜悦是偶然的,短暂的,而饥饿却是长期的,残酷的。
《诗经》里曾有相关的描述:“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可我们那个时候没法浪漫,几千年前的古人表达爱情用以比兴的水生植物,却在推翻了三座大山后的和平建设时期,成为我们用以续命的重要食材。

荇菜——百度图片
第六节
饥寒交迫,生存危机引发的奇思妙想忍饥受饿的时间一长,便能逼出一些有效的对策来。
其中一个心理上的方法,就是不想。故意不往这方面去想,越想越觉得饿,不想就会好的多,这种作用跟望梅止渴正好相反。
还有一个物质上的方法,就是多喝水。实在受不了就舀点水喝,用清水把肚子撑开一点,饥饿感就会好一些了。
再就是努力增加数量。一点点野菜杂粮,不够全家几张嘴吃的,就往里面尽可能多地掺和一些别的东西,比如,半瓢蓬面加一篮子野菜,一碗杂粮加三碗细糠等等,家里人口多,总要变出法子来让食材增量。
对付疾病也有几个方法,其中一种是,喝水发汗。一旦伤风发寒热,就猛喝白开水,然后蒙上被子,出一身大汗,过几天就好了,就可不用吃药打针。
对付寒冷的方法也有好几种。
一个方法是跺脚取暖。这一招在后来上小学时,更被普遍推广。脚冻了疼得难受时,就跺脚。当老师一离开课堂,教室里便是一片声的“咚咚咚”声音;
还有一种活动叫“挤麻油”。下了课,就站到走廊里晒太阳,做一种挤撞的游戏。大家都贴住走廊的墙壁站成一排,两边的人往中间挤,被挤了冒出来的人,就添加到两边去,再从两边用力往当中挤,如此往复,几个回合下来,身上就暖和了;
还有一种取暖方法叫二人“斗鸡”,盘起一只腿,两手提住左腿裤脚,另一只右腿在地上蹦跳,两人蹦得靠近了,就把自己盘起来的腿抬高,往下猛地打压对方的腿,以一方手松开或腿落下为败。这种方法不太可取,因为太费力气,肚子饿,我没力气来参加这种活动。
还有一个方法,是利用温差比,来使自己夜里睡觉不会感到太冷,这能算作“人工降温”或叫“淬火”吧。因为好多人家没有足够的被子,有的全家共用一床,也是精绡的,又旧又死板,一点都不暖和。有的人家好几口人,一床被子也没有,夜里睡觉,只能把身上的棉袄脱下来盖,但这样睡下去会很冷,早上起来更感到冷。而床上根本是谈不上垫被或毛毯的,大都只有一层芦席,人的身子一靠上去,冰凉冰凉的。有一种有效方法是,临睡觉前把自己身上的棉袄脱下来,先不急于盖上身,让自己光着身子在冷风中冻上一阵子,等身上冷透了,冻得打哆嗦了,然后再躺下,盖上棉袄。这样,通过这种极限手法处理一下,自然就没那么冷了。这是河东的陈亚二哥向我们传授的经验。
但是不管怎么说,任凭人们如何动脑筋想办法,寒冷和饥饿总是挥之不去的。
饥饿寒冷和疾病,都是贫穷派生出来的。要真正改变这种状况,这些小门道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根本问题是,怎样才能让老百姓不挨饿,彻底告别贫穷和饥饿。
同时,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严重的饥荒的?
其实,人们心里很清楚,这种持续几年的大饥荒,跟三年前那场运动式的大跃进有关,而大办公社食堂也是引发的因素之一。

大跃进宣传画——百度图片
第七节
早期印象,大食堂是饥馑岁月的开端我更早的记忆中的场景,是去食堂打饭,时光也是春三月。
妈妈领着哥哥和姐姐,抬着一个木头箍的小桶,我拽着妈妈的褂子角,跟在后面。其实算不上是打饭,而是分粥。六一年的春季,公社食堂已经到了维持不下去快散伙的时候了,一天只能分发一餐,都是很稀的粥。掌勺的大爷拿起比人还要高的长柄木勺,在大蒸锅里搅动了半圈,兜起一大勺子,哗啦一声倒进我们的小木桶。哥哥和姐姐抬上肩,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往家走,尽管肚子很饿心很急,但也必须慢慢地走,不然那小木桶中清水似的粥汤就会晃荡晃荡地激出来。
一进家门,我们姊妹几个都迫不及待的拿碗来盛,经常是后边的人还没盛到碗里,前面先盛了吃的人一碗粥就已喝下肚了。我那时才几岁,一顿也能吃三碗粥,是那种三号碗,最大的碗是一种黑窑子碗,这三号碗比普通小碗大很多。而我人虽小,在喝粥这个重大问题上已经喝出一点门道来了,那就是,好东西懂得了慢慢享用。具体方法是,头一碗和第二碗,不拿筷子在碗里面搅匀,只是抿着嘴唇光喝上面的汤,而把前头两碗的米粒留到第三碗,在等第三碗的稀粥汤喝掉后,再将集中到一起米粒一大趸子刨到嘴里,这样,似乎更带劲,似乎更能解馋些。其实,三碗粥加起来的米粒,也不到半碗。
而我在美美地享用最后几口那丰盛的米粒时,看到妈妈也跟我一样,也是光喝上面的汤,把米粒留在碗底。但妈妈后来并没把聚起来的米粒吃进自己肚里,而是偏过身子,喂到了我三弟的嘴里。
为什么是春荒而不是秋荒呢?因为我们这是夏秋两熟的地区,收麦一般在农历的四五月份,收稻一般在八九月份,期间间隔大约四个月左右,而秋收以后再到年后的夏收,却有近八个月时间,是前者的两倍。加之中间有个春节的大消耗,在产量低,分配少,人口多的情况下,如果说一年的基本口粮是三百斤,收成分配只有一百斤,任你怎么节省,怎么使用糠菜补充,还是不够吃。而过了年以后,各家各户的余粮基本上就都没了,从正月挨到二月,再从二月坚持到三月,这每一天的二十四小时都是难熬的。
我们家,如果不是妈妈,我们几个恐怕早就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