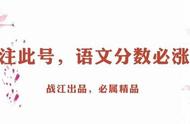浮夸风旧照——百度图片
第十二节
元麦秂秂,已消失但却永恒的美味为了尽早从饥饿的悬崖边上走出来,把青黄不接变为早早衔接,蔉麦,就能承担这生死托付的重任。
通常,都是麦子黄了,完全成熟了,再收割,脱粒,然后加工出来下锅;而吃青嫩的麦仁,便能提前七八天。两三天不吃东西就能饿死人,何况七八天,更何况,断粮的人们靠吃糠菜勉强维持已经几个月了。
能吃到粮食,一天也等不得,一刻也等不得。
我家有一小块十边地,可能是在墩坎上面,地势稍高点,成熟得要稍早些。因此,长在上面的蔉麦,就发挥大作用了。
这都是妈妈的良苦用心。
妈妈把这块田里较大的麦穗摘下来,搓出麦仁,炒了大半锅,足足有十几斤。
妈妈今天要给我们做一种更好吃的东西,秂秂。
这些麦仁在锅里炒的时候,清香味就出来了,妈妈不让我们吃,叫我们等等。说要上磨去拐。
(拐磨,近似与推磨,不用人绕着磨盘转圈。磨盘不太大,人站在一端扶住磨担发力,带动磨头的杠杆,使磨盘转动;另一人在前面控制磨头,并往磨眼里填喂)
那一颗颗青色的并不饱满的麦仁,炒过以后,身子是软软的。上磨去拐过以后,经过磨齿的搓压,就成了一条条絮状的秂秂,软绵可口的,不仅能当饱,更是顶级的美味,其清香的味道和鲜美的口感简直是盖了。
(秂秂,方言,音ren忍 没有特别对号的字,只查到这个“禾将结实”音意相近的“秂”字)
妈妈种的蔉麦成熟得早,因此,每次做秂秂时,都会和左邻右舍共同分享。这么好吃的东西,妈妈不会忘了乡亲们。往往是一炒一大锅,上磨子拐好,妈妈用瓢装上秂秂(瓢是用干葫芦锯开的,是农家的常用器具),每家送半瓢,妈叫我一家一家的给他们送过去。大家都饿到极顶了,见到有人送吃的来,谁不喜出望外。不仅能充饥,而且还这么好吃,他们嘴上都很客气地谦让推辞,说四奶奶自己舍不得吃,还老是想着我们!(我家辈分高,父亲排行老四,庄上大都喊我妈妈四奶奶)但是嘴上说归说,几双手早就伸进瓢里,几乎没等得我转身离开,那半瓢秂秂就被他们风卷残云般的吞食了。他们虽然那么迫不及待没有一点风度,其实倒也好,我就可以随手把空瓢带回家了。
不仅是蔉麦出来给邻居们送秂秂,以后家里几乎每次做饼吃的时候,妈妈总是叫我把那香脆面饼给他们一家家的送去。
这次做秂秂,妈妈打发我们跑到堰南去,要把四姨娘叫过来一起吃,我们嫌远,面有难色,其实也就五里路,但刚从饥饿的死神手里挣扎出来,还没缓过气呢。妈妈教训我们说,自己有一口吃,就不顾人啦!四姨娘家人口多,日子也难过呢,我家蔉麦出来了,还不赶紧去救救她们?
我跟着大哥上路了,走走歇歇,五里路花楼一两个小时,才到唐家庄。见到四姨娘有气无力的坐在床上,脸上像是铺了一张黄纸,一听说喊她来吃秂秂,马上就来了精神,二话不说就往我家跑,我们在后面紧赶慢赶也赶不上她。
到了我家,妈妈已做好了半簸箕的秂秂,四姨娘在她二姐跟前也不扭捏,伸手抓了一把捂到嘴里,大吃了起来,一会,四姨娘吃饱了,她说,还想再带点回家给唐井(她最小的儿子)呢!说罢,解下头上系着的方格子三角巾,摊在桌上,捧了两大捧秂秂在三角巾里,妈妈走过来,又抓了几把给她,说,多带点回去吧,还有唐江唐玉呢!四姨娘小心翼翼的把三角巾打叠成包袱状,提在手里,欢天喜地的走了。我再看看簸箕里的秂秂,还剩下一点点。而妈妈是前一天的下午就下地摘麦穗,今天天没亮就烧火炒麦仁,又一搐一搐地在磨上拐出来,一直忙到现在,自己还没吃呢。
有句剧本台词:穷不帮穷谁照应,人是越穷越大方,越是自己困难越愿帮助别人,越是农村里出来的人越朴实,而本质善良的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改变不了那原本善良的本质。

文革时期宣传画——百度图片
第十三节望眼欲穿,终于等到了麦收
青麦仁接上伙,几天后麦子就黄了,最艰难的春荒时间段过去了。
蔉麦的产量很少,只能是先垫垫肚子;大麦收割以后,才能真正吃饱肚子。
大麦加工比较复杂,先要去掉外皮,这必须要靠舂碓才能形成麦仁。而舂碓是重体力活,效率很低,要靠人力把碓脚踩得翘起来,用下落的碓头的冲击力,将放在碓臼里的大麦粒挤压摩擦,才能把大麦的外皮去。一笆斗大麦,一天都舂不完。这样的重活,都要靠妈妈。
脱了外皮的麦仁,要晒干后再上磨子去拐,拐上几个钟头,才形成可以煮食的大麦采子。这个活,仍然是靠妈妈。
采子粥、采子饭上桌,就说明,麦收了,吃到夏粮了。
再过半个多月,小麦就黄了,收获小麦,日子就好过了。
小麦加工没有大麦麻烦,不用去外皮,直接上磨拐,就可出来面糊,尽管是带皮的,但那味道比大麦采子好多了。如果前一天晚上在里面加上酵头,第二天一早就可以发出一大缸面来,做成锅贴饼,就叫糊子饼。届时,一揭开锅盖,满屋子的香味就散开了。
但是,做这种锅贴的糊子饼,也是需要油的,没有油挠锅,会粘锅,也不会那么香脆。但是,这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了。
重要的是,这一年的春荒过去了。
但是,糊子饼是平时是很少吃的,只有到亲戚是才舍得做这种饼吃。而遇到这难得的美味,我们也借用了喝稀粥的方法,明明能吃三块的,只吃一块,把另两块悄悄囥起来,过几天再慢慢享用。
采子干饭也不是天天能吃到的,只能隔几天吃上一顿,正常都是吃采子粥,好在不是很稀的那种,我们这也很满足了。
一家子七八张嘴,一年四季三百六十天,日子怎么过,妈妈不能光顾着疼我们,她要盘算着怎么搭配,要细水长流,尽管麦收了,也是不能放开肚皮来吃,离收稻还有四个月呢,即使秋粮收获了也不足啊。如不掐住,多喝点粥,再到年后的二三月里,那春山头上,吃什么?
要是还像今年一样,还能再熬过去吗?
(采子,麦子磨碎的小颗粒,学名为“糁”,当地方言所称的采子,一般单指大麦的颗粒,因为大麦的产量大,是人们一年当中占比最多的主粮。平时都是采子粥就咸菜,煮采子粥的时间较长,要煮的烂一点,不然就有点糙嘴,因而,在有大米吃的时候,是不愿意吃这种采子的)

快黄的麦子——百度图片
第十四节
蹉跎岁月,阳光大道上风雨交加所幸的是,第二年情况就明显好转了,虽然仍不能吃饱肚子,但粮食供应量增加了一些,自家再用糠菜补充补充,饥饿的程度已经大为改善了。
又过了两三年,到了六五年六六年,就已基本恢复常态,告别糠菜,不怎么挨饿了。
但是,仍然是稀粥为主,干饭每天一顿还是奢望。但每逢八月半,过冬,腊八,妈妈总要安排全家吃上一顿干饭。记得上小学二年级,过冬那天中午,放了学,没等得集合站队,就一路小跑赶回家了,因为,前几天妈妈就已通知我们,这一天要给我们煮胡萝卜饭吃。
能吃到大米饭,即便是稻子收获以后,也是很少能吃得到的。
那一锅大米饭的大米,充其量也就五分之一吧,一大半都是胡萝卜,但那香甜的味道,随着锅盖揭开,扑面而来。
妈妈做的是插饭,他盛了一碗雪白的给三弟,父亲和我的碗里有红有白,而妈妈自己的碗里,却是通红的一片。
我家每天能正常吃上大米饭,那都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了。
那时已经改革开放,包产到户。生产效率高了,产量也高了。同时,随着我们长大,外出工作,吃饭的嘴也少了。
还有一个小小的因素,就是我们的饭量也小了。
人哪,也真怪,越是没得吃,吃的就越多;有得吃,反而吃的很少了。
还有感到奇怪的是,没饭吃的时候,连草都没得烧,要经常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捡拾柴草;而现在吃的多了,烧草反而过剩了。田里的麦草稻草都懒得收割堆垛,想放把火烧掉,又怕影响环保。
世事沧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吃饱饭已不再是问题的时候,人们体味的就不再是饥饿难熬的痛苦感觉,而是膏粮美馔的舒适受用。
但是,我伤心的是,我的妈妈没能等到这一天,父亲母亲都没能等到这一天。
他们熬过了那连续几年的饥馑岁月,但没能躲过那十年狂热的风潮,父亲在动乱中的七零年蒙冤暴卒,母亲也在曙光初露的七六年抱憾辞世。
(父亲早年带队打游击,与日伪周旋,经常游河过港,热身子下到冷水里,落了一身病,得了末梢神经炎,刚解放就不能工作了,后来病情加重,四肢末端就发炎,剧痛难忍,后来腿和手就只能一截一截地锯掉。而解放初期任职乡长却在政府建制形成以后病残在家,工资福利就没有了,而巨额的治病的费用,更加剧了家里的困难。饥荒过后没几年,在六八年又遭受冤案,全家人一起又陷入了更大的政治悲剧里面。该话题不再展开,以后专篇另述吧)

脱贫庆功大会——百度图片
第十五节
背景溯源,政治斗争与民生经济的角力也须有人会问,你们那里是鱼米之乡,不应该有这么严重的饥荒啊。这个疑问有点道理。
我的家乡串场河畔,的确是丰腴之地,黑色的油黏土,属于高产良田。适合稻麦两熟。早在唐宋时期,这里就开挖了连接各大盐场的串场河,那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修的笵公堤后来成了通榆公路。串场河的西侧为里下河平原,串场河的东侧为滨海平原。
这一片沉积平原作为良田来耕种的年代很早,明朝洪武赶散,我们祖上来到这串场河东岸,看上这方沃土,定居了下来。靠一代代先人们的辛勤劳作,已是良田连片,衣食丰足,几百年来,生生不息。
而为什么解放了,还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饥荒呢?是自然灾害吗?
我说不是,那几年其实并没有很大的自然灾害,洪水,台风,蝗虫都没有。即便是干旱,也是发生在河南那些老远的西部地区,这里并没有很大的旱灾。因而,现在许多比较严谨的学者就称那个时期为三年困难时期。
那么,现在很清楚了,本来是高产粮区,又没有大的自然灾害,怎么就突然闹饥荒了呢?
简单来说,是国内国际直接间接多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
五八年运动式的大跃进,步子太快不切实际,发现问题后没能有效纠偏,反而在接下来的公社化和公共食堂诸多问题上,继续盲目冒进,口号火热,效率低下,产量下降,农业凋敝,办了两三年的大食堂又造成坐吃山空。
而六零年开始,中苏关系交恶,国家不能再继续得到苏联老大哥的支持,反而要在五年之内还清52亿元的债务,使国内经济雪上加霜。而贫穷却很硬气的我国,竟然在六一六二两年,就已还掉了一大半,这都不是货币,其中14亿是用矿产抵债,而21亿则是用粮食、猪肉、鸡蛋、水果来偿还的,这21亿,可都是从六亿多人民的口中省出来呀。
这样的国内国际情势,出现饥荒就是必然的了。
人在穷的时候,腰杆反而是很硬的。我自己也曾瞎想过,如果,六零年中苏论战关系破裂,愤然还债的时候,这还款的节奏如能先少后多,或者期限不是五年而改为十年?另一个如果,不去和老赫撕破脸正面硬刚而采用智斗,不跟他闹翻,斗而不破,不就能避免整个国家和民众遭此大难么?我知道,这种如果是不成立的,因为在政治和民生两者做选项的时候,选择前者是那个时期的决策者的必然。
有人曾问我,六二年以后的那几年,又是怎样从饥荒中走出来的呢?
其实,中央早就有所反思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已在六一年初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接下来就着手恢复国民经济,这段时期,全国上下一心,心无旁骛,效率显著,到六五年,不仅还清了外债,还提高了粮食产量,发展了经济
其实,党的八大早就已经确定,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以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矛盾了,发展生产力,大搞经济建设。这八大的总路线在1956年就已经确立的啊。
谁知道,几年后,又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开始了,八大制定好的方针被扔到一边。这一乱,就是十年。国家十年的发展进程,我们这代人的十年青春。
而当十多年后,能真正把我们的肚子填饱的,却是包产到户这种方式,而不是我们本该坚持的集体化道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没能发挥该有的作用,虽然肚子饱了,心里却是酸楚的。
如果(我又说如果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从1956年起,就按照八大的路线走下去,完善集体化道路,稳步推进,恐怕早就过上好日子了。
但总算有了石破天惊的一天,2021年年底,全国十四亿人口全部脱贫。中华民族有史以来,这个最简单而又最艰难的问题,在根本上得到了解决。
很庆幸,也很欣慰,但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丰衣足食,永远不再出现粮荒。
但愿我们国家的决策者,永远不要忘了初心,不要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可能是我这个经历过饥寒的人,会更懂得饱暖的可贵吧,当前两年那四个字的大标题首次在主流媒体的荧屏上出现时,当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把那四个字作为主题思想写进去时,我是那么异乎寻常的激动。
我们都知道,那四个字是:人民至上。
阳春三月,气暖风和。
但我却想到了枚乘的名句:甘脆肥醲,腐肠之药;出舆入辇,蹶痿之机。忧患意识,总不敢丢失。
现在,很难有人去深切体会叙利亚乌克兰难民的饥饿状况。但如果,战争在自己家门口爆发呢?
同样,也很难有人去感悟苏丹索马里遍地饿殍的悲惨程度。但如果,大灾频仍,粮荒临到自己头上呢?
近来一个多月,我也被困在上海。当两千多万人的大都市断了供应,大家都在为一袋米面无奈发愁的时候,是否能引起自己的反思和警觉呢?
羁旅之中,写了这篇气氛压抑的文章,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心情,但如果能使你产生一点共鸣,我就很慰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