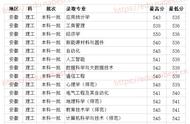很难有哪个时代比今天更称得上是一个「考研」的时代。考研,甚至不再像是个人选择,而是一种集体趋同。人们期待靠这种最普遍的选择,找到人生的更多可能性。而考研这股风潮,也改变了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
文|邬宇琛
编辑|楚明
图|视觉中国(除特殊标注外)
难也要考
没有办法停止考研。
当曲阜师范大学的大四学生陆婷从硕士研究生考试的考场走出来时,被「忍」了两天的新冠病毒终于在身上起了症状。考最后一科时,她腰疼,头晕,很困。
战斗结束,回到宾馆,她才意识到自己身体如同「碎尸万段一样」,一量体温,38度多。
好在一切都结束了,她挺了过来。考试十天前,学校里阳性病例一个又一个增加。陆婷很害怕,她知道自己不能错过这次考试。宿舍的一个同学成了密接,她和其他三个人不敢回去,生怕感染。她们在自习室打了三天地铺,没有床单,没有被子,也没有暖气,在北方的冬天里穿着袄子、鞋子也不脱就睡着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她戴着三层口罩背书,一层口罩睡觉。每次背书背到感觉喘不上气的时候,她就走出自习室,到走廊里像剥洋葱一样摘下口罩,偷偷呼吸一口,然后又戴上。即便如此小心翼翼,考试前3天核酸检测时,她的结果显示出阳性。她被一辆大巴接到了学校建好的隔离宿舍,在那里度过考前最后3天,然后上了考场。
在广州,陈雅轩已经将近3个月几乎没有与外界接触,一直把自己关在家。但没关系,她告诉自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碍她走上考场。12月24日,坐在考场里的第一天,她数了数教室里的人数:19——近一半的人没有到场。
王璐来自重庆,11月,她到成都参加一个招聘面试,寄宿在亲戚家,期间学校被封控。她拿着为数不多的一点复习资料在成都待到12月。由于考点在重庆,在这个月的硕士研究生考试之前,她向成都当地申请了「异地借考」。
对考生而言,2022年年末的这场考试颇具挑战性。受疫情影响,考生们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根据已公布的数据,弃考率最高的地区广东省,26.3万报名人数里有5万人没有参加考试,弃考率达到19%。另一方面,今年考研人数再创新高。457万人报名,比上年增长80万,增幅为21%,这些数字史无前例。
30岁的李文洁今年也踏入了考场。她是在职7年的公务员,今年借调到一个新的部门做管理,到了之后才发现,本科毕业的她在下属面前毫无学历优势,「大部分都是名校的研究生」。
今年5月,她开始考非全日制管理类专业研究生,希望用更好的学历帮助自己在单位站稳脚跟。在她之前,一个老同学因为经营的培训机构营收不好,转而全职读研,跨专业考了金融硕士。今年这名老同学毕业,去了证券公司做投资辅导。
男女老少都在考研。跟过去十年的任何一个时候相比,考研更成为一种现象级的趋势。根据中国教育在线的数据,从2016年开始,我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在高位上保持增长趋势。2015年-2022年的7年,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年平均增长为15.8%。很难不说,这是一个考研的时代。

2022年12月25日,长沙,考生有序进入考点
选择和宿命
决定成为考场的一份子,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理由。
对陈雅轩来说,这个理由是「不想上班」。大学毕业时,陈雅轩给很多公司和行业投了简历,但大部分公司都写明「要有经验」,对应届毕业生来说不太友好。最后,她进入一家跨境电商公司做快时尚买手,试用期工资6000元,每天加班到晚上10点以后。有段时间,她每天晚上到家就开始哭。
不去企业上班,就被父母鼓励去考编,但广州市大多数的编制岗位都不对设计学专业应届生开放。也就是那时起,因为专业就业前景不好,陈雅轩心生了通过考研换个专业的念头,父母也支持。2021年毕业不久后,她就辞职在家专心考研。那是她第一次考研。
在成都读本科的张然不是一开始就笃定要考研。材料学工程专业的他有一个自己的观点,「读研究生其实也在打工,只不过是给导师打工」。大三下学期,他开始纠结给谁打工。这在大四参加的某车企招聘会上有了答案。「品质工程师」的工资只开税后6000元,张然把这个岗位视为质检,没办法接受。
面试某工程局的室友兴奋地从招聘会回来,说「工作也太好找了!面试问的问题很『水』,不用穿正装,就问我会不会喝酒。」张然心里大吃一惊,想着还是要读个研究生找个更好的工作,索性放弃了那年的所有招聘,开始专心备战考研,「给导师打工」。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冯雨奂在做「慢就业」的研究时,访谈了10余名毕业生。她在论文里提出,「慢就业」的现实表征通常是毕业生未能实现满意就业而做出的现实应对,方式之一就是通过考研来增加进入高端劳动力市场的文化资本。
不过,仅凭一个「史上最难就业季」无法酝酿出逐年增长的考研人数。考研对于一些考生来说是对高考的弥补,是应试的「再循环」。「高考失利」这四个字,是不少考生选择考研的理由。
徐伶俐在河北读的高中,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在高考上获得好成绩,于是来到重庆的一家民办本科读书,专业选的是资产评估。她记得自己来到重庆的第一天,就被天气热得够呛。那时她下定决心,4年后要通过考研来证明自己,不能让大学和高中一样遗憾。在民办本科,一个专业有200多人,大四那年,有一半多的人选择了考研。
山东人罗小粒说自己从初中开始就有名校情结,但在班上排名前几的她高考失利,去了广州的一所双非一本。她打听了以前高中同学在大学后是怎么上课的,发现他们都很「乖」,而自己所在的大学师资力量和985名校相差很大,而且大家上课都比较散漫。她有了危机感,害怕因为怠慢学习而和原来的高中同学拉开差距。
她发誓自己4年之后要去更好的地方读书,「211都不行,必须是985」。
只有稀少的考生像王璐一样完全因为学术兴趣才考研。她在重庆一家双非一本读广告学,上大学之初参加了学校的读书会,跟老师一起读李普曼和麦克卢汉的原著。疫情还不严重时,学院邀请了很多北京的知名教授到学校授课,读书会的人可以优先参与。「很爽」,从那时起,王璐就坚定了自己要考去上海读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生的想法。
到了大三,班上有个同学问她考不考研,她说考。那位同学说,「我报了7000多元的班,你为什么不报班?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报了。」王璐有点震惊,「为什么要报班?考研考不上就算了,为什么还要花7000多元,非要考上呢?」
她突然感到疑惑,第一次感知到「竞争对手」的存在,也第一次才知道,原来考研还要报名买课。她觉得自己被拉扯进了一个超出想象的赛场,这个赛场需要策略、规划甚至是金钱,而和她并肩作战的人并非和她一样目的纯粹。
有时,人们考研只是因为它变成了一阵风。加入的人越来越多,跟上的人也越来越多,如果不跟上队伍,就会掉队。考研像是机缘巧合下各种环境编织起来的大网,人们难以避免地涌入网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数字就这样被竖起。没有人能够说清,在这个时代,到底什么样的理由考研才算得上足够正当。或者,所有理由都正当。

山东济南一高校食堂变身「考研自习室」
「时间不值钱」
对个人而言,考研是具体的,是难以浪漫化的。晚睡、早起、看书、背书、睡10分钟然后醒来,它像是日复一日的机械运动。
2020年,为了考研,张然牺牲了春招和秋招的机会,但他最后还是失败了。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开启第二年的考试。他要考深圳大学,于是第二年夏天,把房子租在深大粤海校区附近开始专心备考。粤海校区就在传说中的「中国最牛街道办」粤海街道上,租金很贵,一个单间就要3600元以上。最后他挑选了一个最便宜的房子,每个月1750元,10平方米不到。他把床单铺好躺下,在孤零零的房间里给朋友发消息,「好想哭」。
「一战」的失败并非那么难以接受,真正艰难的是需要继续消耗家里给的经济支持去做一件不容许失败第二次的事情。每个月,张然都向家里要5000元生活费。「时间不是很值钱,吃饭、租金,这些是真正的钱。所以我真的怕考不上,这些钱就打水漂了。」
「二战」,甚至「三战」对考生而言都不陌生。当前各大研究生院给出的招生计划没有明显的扩招痕迹。激烈的竞争里,注定有过半数的人成为考研的陪跑者。它是一场牺牲,一场拉锯战,一场谈不上有趣的循环。
2023年将是毕小芬的「五战」,她已经27岁,但还在坚持着。作为一个医学生,她从2016年年底开始考研。那时她正在读五年制的第四年,因为正值医学生的实习期,一周上5或6天班,每天下班在图书馆睡半小时后继续学习。那年她报考了医学专业的顶尖名校,不出意外地失败了。
毕业后,她按照医学生惯例到医院规培(轮岗工作)。她本来已经暂时放弃了「二战」的想法,先完成规培。但同一个宿舍的其他人都考研,她想了想,觉得需要「跟上」。她调整了院校目标,降低标准到另一所985,在那年10月开始备考。时间依然稀少,下午5点半下了班,她和考研的舍友一起在医院自习室待到夜里12点。她依然没有进入初试。
前两次失败,毕小芬都能接受。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时间付出得不够。「三战」对她来说是转折点。这一次她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认真,也更沉默。因为失败了两次,她不敢告诉别人自己还在考研。她不去医院的自习室,转去新开的付费自习室,一天花个三四十元学习。她还去当时男友的家里,人家以为她谈恋爱去了,实际上是背着别人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