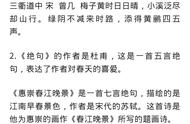报考者几乎没有一个问题回答完全、圆满,往往嗫嚅一阵,最后还是说不知道。(农健/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8月10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开招考科研人员工作纪事》)
我参加的另一场论文答辩,使我至今想起来都感觉心情复杂。我自己也感到我的提问像连珠炮,一个接一个,有些咄咄逼人。
自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被批准组建,1978年夏历史研究所宣布恢复处室建制,本所业务工作重新走上了正轨。这时,所里面临研究人才短缺的问题。十年动乱,人事编制、人才培养都基本冻结。只在1968年分配来几名大学生,但他们除留下一人外,其余的很快都走了。直到1976年,又分配来四五名工农兵学员。而在从1966年以来十有余年,自然减员和因解决夫妇两地分居问题而调走的人员,又不在少数。这就出现几近一代人的缺口和中青年研究人员(即调走者年龄层人员)的一些缺口。以小见大,历史研究所如此,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界并无二致。这是缺人才的一面。
另一方面,社会上又积累了一批愿意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在知识青年中,在临时工中,在他们供职但不甚满意的工作单位中,都有这样的人才。打倒“四人帮”后,他们已经可以通过考大学、考研究生的途径改变命运,但年龄和文化程度不适合参加此两考者仍需要另辟通道吸纳他们。197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广开才路,拟在全国公开招考研究人员,以充实本院和地方社会科学院的科研队伍,得到党和国家*批准,当即登报公示,留下准备应考的时间,于是有1980年组织进行招考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活动。这是适合需要、大得人心的。招聘改为招考,促进竞争性、透明性、公平性,是合理的进步的改变。
报考还比较踊跃。报考研究员、副研究员者602人,报考助理研究员、研究实习员者3757人。年龄没有苛刻规定,可见目的只在于得人。考试方法有二:
考正、副研究员要提交论文,进行答辩;考助理研究员和研究实习员者参加笔试。我不了解笔试情况,出题、监考、阅卷等工作我都不沾边。我只参加过几场明清史系统的论文答辩会,体会到招考的美好作用,能出珠玉于木椟,拔英豪于众人,使才俊之士不致埋没。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愿为此道奋斗且有此艺能者,莫若使他们自呈其身,招考自然是达到目的的适当方法。隔若干年举行一次是有益的。
据我所知,取录而可称为史学人才的,颇有其人。
袁行云先生,1928年生,江苏武进人,报考时已年过半百。因长期在新闻、出版、教育单位供职,业余做过大量文献学和史学方面的工作,酷嗜版本、目录、考据之学,是一位学识丰厚的学者。此次通过文献学论文答辩,录取为本所副研究员。1983年他出版史学专著《许瀚年谱》,1985年出版古籍整理作品《攀古小庐全集》,几年间还陆续发表有价值的论文《谢启昆《〈西魏书〉为胡虔代撰考》《梁章钜著述多非自撰》《吴荣光著述的代撰者》《唐以来诗文中所见敦煌述略》《新发现的吴敬梓佚文》等等,得到学术界重视,并引起日本学者关注。袁先生为学继承和发扬传统,重视考证,重视发掘新材料,研究新问题,追求有所发现、发明,得到新结论。其最后完成的大著作,名《清人诗集叙录》。作者倾注心血于此书达三十余年,阅清人诗集四千余种,每种撰叙录一篇,成稿一千五百余篇,总字数二百万。叙录每篇系诗集作者小传,中心内容“以证明史事提供资料为主。凡诗中山川、名迹、政治、经济、学术、文化、民俗等史料线索悉举其要,尤重于中外关系、少数民族、小说戏曲等资料掇拾。”“略及清诗源流派别及作者评价,评语采辑成说,间出己意。”(《清人诗集叙录》,《凡例》)诚如《清人诗集叙录》的《出版说明》所说,《清人诗集叙录》实在称得上是一种清人诗集总目提要。由于作者是历史学家,又着眼于以证明史事、提供资料为主,故对史学研究尤具参考价值。我自己研究柳敬亭、苏昆生的生平和艺术,就从中得到不少资料或线索。不幸的是,袁先生在历史研究所的专业研究,只持续了八年,刚到花甲,就因病去世,令人痛惜。(编者注:袁行云先生已于1988年去世)

袁行云(资料图/图)
胡珠生先生,1927年生,浙江永嘉人,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他从业道路曲折,曾任工厂铸工车间工艺员,长期游离于学术机构门外,治学条件极为困难。珠生先生在逆境中搏击,始终不忘所学,锲而不舍,执著地追求史学研究大目标。后来他到温州市文物处工作,基本上实现了长期心愿。1980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公开招考,通过答辩,其研究能力得到肯定,录取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未赴。珠生先生为学,崇尚逻辑思维,重视考证、驳议,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但明辨是非,不固执己见,敢于破立,以此多探骊得珠,成果丰硕。其主要著作已出版的有《清代洪门史》《温州近代史》《胡珠生集》(精选论文65篇逾60万字)三种,其《温州古代史》一种仍在撰述中。他热爱故乡,历来重视乡邦文献,以发扬光大地方文化,促进社会进步。历年来他编辑校点《陈虬集》《宋恕集》《孙锵鸣集》《东瓯三先生集补编》,校注《(弘治)温州府志》,点校陈怀《清史两种》等,都陆续出版。2001年7月,珠生先生将满74岁,还应家乡需要,出任《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兼编辑部主编,掌握学术工作大权。他受命以后,兢兢业业,夙兴夜寐,与同事诸先生一道辛勤工作,躬亲选题、组织、审读、编辑、校点各役,历时七八年,《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任务大功告成。《温州文献丛书》共收温州里老乡贤著作并有关乡邦故实文献四辑四十种(其中有书数种合而为一种者,有零篇散页集腋成裘者,若依入选文献的原始形态统计,其种数当远不止此)。工作做得很出色,我读过其中若干种,觉得编、校、注、点质量上乘。这是温州地区文献的最新结集,具有历史意义,也是珠生先生一项卓越的学术业绩。温州经济的发展和家乡人民的信任,促进了他在学术上的腾飞。(编者注:胡珠生先生已在2014年去世。据温州学者卢礼阳见告,胡珠生先生生前曾告诉他,当年浙江社科院以超龄为由,未录取他。)

胡珠生(资料图/图)
王纲先生,1932年生,土家族,四川人。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中学任教。但他心存高远,并对自己的功力具有强烈的自信,业余孜孜不倦,坚持史学研究。他选定的项目,是四川人喜爱的课题:张献忠及其大西军史。他勤跑图书馆,读了大量有关的史籍和方志,摘抄许多资料,辑为张献忠史料选编,经过研究,撰成《张献忠大西军史》文稿。王纲先生为学,是从读书、从积累点点滴滴材料入手的,因此他非常重视记载,重视史实,资料丰富是他的著作的一大特色。但他不是堆砌材料,而是对材料进行分析,从材料中挖掘和提炼出历史的信息,以构筑和概括出对历史的认识。1980年他通过公开招考的答辩,被录取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此他更加如鱼得水,奋发图强,撰成并出版《明末农民军名号考录》(1984年)、《张献忠大西军史》(1987年,加工原有成稿付印)、《清代四川史》(1991年),此外还有一些论文。《清代四川史》是王纲先生的代表作。全书分为30章213节,总字数逾110万言,内容十分全面、广泛、细致、周详,举凡清代四川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社会等诸多方面发展情况,无不备具、涉及。对历史问题的分析,一般都比较准确、深入,有的可说很精辟,例如总结四川抗清战争的严重教训、顺康雍乾治蜀方针的章节等等。关于经济、文化的章节,有的也写得很精彩。读书很多,充分利用了《清实录》,还从大量其它史籍中挖掘了很多史料,因此全书显得十分厚实可靠。《清代四川史》是同类地方史中的优秀著作之一。王纲先生还是著名书法家,行书刚劲、优美、自然,有笔扫千军之势。大量时间投入书法,明显制约了他的史学研究工作进一步发展(当然,推出了许多出色的书法作品)。(编者注:王纲先生已于2013年去世)
袁行云、胡珠生、王纲等各位先生的成就说明,取录他们进入研究机构,是此次公开招考成功的表现。
我参加过几场明清史范围的答辩。第一场就是胡珠生先生的答辩。答辩委员会由五人组成,按年龄说依次为王竹楼、王戎笙、周远廉、何龄修、郭松义,王戎笙先生为主席。我对珠生先生并不完全陌生,虽不相识,但我读过他在《历史学》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在思想上产生共鸣。看他填写的报考表格资料,发现他与我先后同学,他是我的学长、师兄。在一般情况下,他应是我的考官。他的道路曲折、坎坷。造化捉弄人,我们的位置颠倒了。我心里感到一种不安。他提交的论文,是发表在《历史学》上的《天地会起源初探》,答辩会进行正常、顺利,该文以郑成功为天地会实际创始人的论点遭到一些驳诘。不过珠生先生的水平是客观的。答辩委员会通过将他录取,后确定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但他最终未赴,留在温州市文物处。他在答辩中也受到启发,据他自己说,王竹楼先生(珠生先生误为王毓铨先生)提醒他改变思路,不要拘泥于郑成功创立天地会成说。此一点拨,解脱了坚持成说对珠生先生研究思维的束缚,使山重水复疑无路,变成柳暗花明又一村,推动他此后对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研究,朝正确解决的方向前进,终于完成《清代洪门史》的创作,建立起不容否认的科学功绩。
另有一次考试,我不记得报考者报考何职称,似乎不是副研究员,因为他没有提交论文,也没有举行答辩,可能是助理研究员,但其年龄等等似乎又不应再报考中级职称。总之我记不清了。考试的方法不是笔试,是口试。由谢国桢先生任主试,刘重日先生和我陪坐。谢国老好像早有准备,问了颇多问题,涉及历史人物、事件、典籍,主要的范围是南明,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发问。报考者几乎没有一个问题回答完全、圆满,往往嗫嚅一阵,最后还是说不知道。谢国老极为不满,说:这些都是常识,怎么能全不知道?报考者应有些家学传统,因此显得更难堪。刘重日先生和我始终一言未发,不想使气氛变得更紧张。口试结束,我向谢国老表示了一点疑问,我说:谢老,您提的问题,有的确是常识,但有的问题已经很专业了,如六狂生和华夏《过宜言》的问题,不重点注意,一般明清史研究人员很难了解这么细,不好说这些都是常识,您觉得是吗?谢国老想了片刻,连说:还是常识,还是常识。我以为老年人难免固执,就不吭声了。口试后,取录与否,怎么取录,我都记不清了。不过这位先生后来到了一个地方社会科学机构工作;是否这次报考取录分配的,我说不清楚。

谢国桢(资料图/图)
我参加的另一场论文答辩,使我至今想起来都感觉心情复杂。报考的先生也是一位中学教师,业余治史。十分勤奋,颇著成绩。答辩委员会事先研究了情况。一位先生说,听说报考者对研究成果自我评价很高,有目无旁人的味道,在这种情况下对话很难。由于我对报考人论文涉及的历史相对熟悉,便交给我任务说:“必须把他问倒。”我听了,觉得有预先算计应考者的味道,但又觉得并不违法,考试从来具有刁难的因素(如果能这么说的话)。我又觉得这个任务不难完成,首先是我处在优势地位,只有我问他,他不能问我;其次,史学涉及方面广泛,包罗万有,每个人在知识结构上都存在软肋,有精力照应不到的地方,重要的是发现这些弱点,追问下去,他必倒无疑。但是我抱定宗旨,问的问题不能刁钻古怪,必须合情合理。于是我研究他的论文,发现他对制度比较生疏,可能是他的论文的薄弱环节。我确信一件有效武器就可够用。
答辩按时进行一段时间后,我根据既定方针提问,先请报考人结合论文提及的清军军官职衔等情况,简述一下清朝的军制。这个问题立刻就暴露出,制度的探究是报考人一向所忽视的方面,因此不可能说清楚。在反复诘难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他对与论文相关的史籍的了解也不那么充分,于是我也提了些关于史料方面的问题。我自己也感到我的提问像连珠炮,一个接一个,有些咄咄逼人。当然,答辩委员会看到了他的研究功力和成绩,通过取录他入地方社会科学院。事后,监督和指导答辩的副所长熊德基先生,委婉地指出我提问的方式使答辩过于紧张、激烈。然而,令我深感意外的,是报考人谈的对参加答辩的体会。他甚至说,在地方上,他因自己取得了一点科研成绩,就沾沾自喜,“成为井底之蛙,到了北京,参加这次答辩,才知道天有多大。”这几句话给我一种很强的震撼,我清楚地感觉和毫不犹疑地承认他本质的谦虚,我甚至怀疑别人把他对科研成果表现出可能有些张扬的兴奋,误会成狂妄了。熊德基先生也充满感情地发表了一篇总结,肯定答辩委员会的工作,特别是对报考人表示了热情的勉励和期许。从此,我和报考人成了朋友,互赠著作,通信贺年,问候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