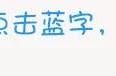史凤晓
在有机会来英国与熟悉威廉・华兹华斯之前,水仙花是我对华兹华斯与英格兰认识的重要的一部分。试问所有英语专业的人以及喜欢西方诗歌的人谁不知道“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飞白 译)”(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这首在国内被等同于、甚至以《水仙花》命名的诗呢?来到英国的第一天,在饭桌上,从没进过一天学堂的英国老房东听我说研究华兹华斯时,出口诵出“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这是多么让人惊叹华兹华斯以及这首诗的受欢迎程度。春天到来的时候,房东在院子里喊我去看“华兹华斯的水仙花”。那是2014年春天,我在英国度过的第一个春天。那一年,我在家里、路边、学校里、花园里、湖边、树下看到了华兹华斯笔下随风飘动比银河里的星星还要明亮的金黄色的水仙花。此刻,英格兰的春天湿哒哒的,风、雨、雪交错。但,窗外院子里的水仙花明亮娇艳金灿灿地开在我的眼前。呵,华兹华斯的水仙花!

华兹华斯画像
某个周二的傍晚,经过湖区小镇安布塞德(Ambleside)已有300多年的著名桥屋(Bridge House)与它所安然坐落其上的罗莎河(River Rothay)旁,看到水仙花在寒冷的风雨中舞动、盛放,旁边商店前的花坛上也是水仙花,我问贝壳先生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华兹华斯写了那首关于水仙花的诗吗?因为它原本是威尔士的国花,理论上来讲,威尔士应该是拥有水仙花最多的地方。祖父辈来自于威尔士的贝壳先生想了很久,说,应该有很大关系吧。罗莎河流经安布塞德、瑞德村与格拉斯米尔。这三个地方都与华兹华斯有着密切的关系。安布塞德是他担任本郡印花税务官一直到退休的工作所在地,瑞德村是他居住时间最长的家瑞德山庄所在地,他每天从瑞德步行去安布塞德工作时也要沿着罗莎河。格拉斯米尔是他居无定所流浪归来与妹妹多萝西在湖区安的第一个家“鸽舍”(Dove Cottage)的所在地。也是他与家人安息所在地。罗莎河便是流经他与家人安息所在的圣奥斯瓦茨教堂。这长长的、明净的、宁静的河流流过诗人在世时的半个世纪的岁月,在他离开之后,一百七十年里,依然流着。我想,这条河不仅以静静地水声陪伴着诗人,也会把偶尔落进去的水仙花以及花香带至那里吧。当然,他安息地是不乏水仙花的,水仙花开放之前,我看到他的墓碑周围盛开着他喜欢的雪滴花。水仙花在他身旁,在他旁边的水仙花公园盛开着。水仙花公园便是以他的那首诗命名啊。进门第一块石板上便是那句著名的“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这首几乎人人都可以默诵出首句的诗从灵感到创作再到接受、推广有着很多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精彩故事。它有着诗人与家人、朋友以及当时与后世的读者之间有形无形的联系。它的产生过程、真正的作者、名字、诗节的数量、叙述者是否真的如云朵一样孤独游荡以及诗人本人对这首诗的评价都掩在第一行以及这首诗的流行度之后,显得有些模糊。
诗作的诞生:是多萝西还是威廉?
1802年4月7日,华兹华斯在32岁生日那天骑马前往约克郡见自己幼年好友未来的妻子玛丽・哈钦森。此时的多萝西在位于英国湖区第二大湖奥斯湖(Ullswater)东岸的“尤斯米尔”(Eusmere)房舍,他们兄妹的好友,英国反奴制运动领袖克拉克森(Clarksons)夫妇家等着与兄长在那里会和然后一起回位于格拉斯米尔的“鸽舍”。在玛丽家呆了几天商量好两人的婚事之后,华兹华斯在4月12日回到“尤斯米尔”。4月15日,兄妹二人离开朋友家,在路上边走边看边停留,用了两天的时间走回格拉斯米尔。
多萝西在后来被命名为《格拉斯米尔日记》的日记中记下了在奥斯湖畔看到的水仙花场景:
在树下,在湖滨,我们看到一长片水仙花……我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水仙。它们长在生满苔藓的岩石间。有些水仙花慵懒地倚在石头上休息,石头宛如它们的枕头。其余的水仙花来回舞动,摇摆(tossed, and reeled and danced),看上去好像在与掠过湖面吹在它们身上的风一起欢笑。它们看上去如此快乐(gay),一直东歪西晃(ever glancing),永不一样(ever changing)。…… 湖湾与湖水中央波涛汹涌,像大海一样。我们一路听着湖浪(waves)声。
五年以后,也就是1807年,读者在华兹华斯的《两卷本诗集》(Poems, In Two Volumes)中读到了《水仙花》这首诗。华兹华斯后来在《芬威克笔记》中提到这首诗创作于1804年。也就是说,与多萝西经过奥斯湖畔的水仙花两年之后才完成了这首诗的创作,1807年与其它诗作一起被收录进诗集《两卷本诗集》中。当时的这首诗只有三个诗节,并非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四个诗节的版本。1815年,出版《诗集》时,华兹华斯在原诗的第一个与第二个诗节中间增加了一个诗节。无论是三个诗节的版本,还是四个诗节的版本,里面有一些语言与画面与多萝西的日记有些重合。比如,多萝西用“在树下(under the boughs of the trees),在湖滨(along the shore),我们看到一长片水仙花”(we saw that there was a long belt of them)形容他们一起看到的水仙花,并且描述水仙花的舞动(tossed, and reeled and danced)。华兹华斯在1807版的第一个诗节中的第四行几乎完全是用了多萝西的语言:“它们开在湖畔,开在树下”(Along the Lake, beneath the trees)/它们随风嬉舞,随风飘荡(Ten thousand dancing in the breeze)。只是华兹华斯稍作了修改,将多萝西的“shore”改成了他诗中的“lake”,用”beneath”取代了同样意思的 “under”,“the trees”取代了 “the boughs of the trees”(整体取代了部分)。总的来说,在这一诗节中,他把多萝西某些具体的、细节类的描述抽象化、泛化。第二诗节中,华兹华斯用了多萝西的词汇,比如“waves“, “danced”, “gay”, “laughing”。多萝西描述的水仙花好像在与吹在它们身上的风一起笑。华兹华斯的水仙花是一个“欢笑的陪伴”(Laughing company),他在1815年的版本中将”laughing”换成了“Jocund”,词形不同,但意思一样。1807年第三个诗节,也是最后一个诗节,完全是华兹华斯式的诗句。最后一个诗节是前两个诗节的升华。写的是,他在茫然独卧时,脑海中划过了曾经见过的水仙花,于是,他的心与水仙花共舞。他将此称之为“孤独的福祉”(the bliss of solitude)。1815年的版本中,华兹华斯将第一诗节第四行中“舞动的水仙”(dancing daffodils)改成了“金黄的水仙”(golden daffodils)。这时隔八年的变动,有很多原因。有些,比较明显,比如,为了避免重复。就“dancing”一词来说,最初的版本中,在第四行与第六行同时出现。有些,比较模糊,比如,为什么诗人突然增加了一个诗节。在增加的诗节中他把水仙花比喻成在银河中闪烁的星星。同时也增加了多萝西日记中的内容,比如,最后一行中“万花摇首舞得多么高兴”(Tossing their heads in sprightly dance)。“Tossing”, “heads”,“dance”会让人想起多萝西在日记中用的“tossed“, “heads”和“danced”。考虑到当时多萝西是为了让哥哥从外面回到家中时有些东西可以读,为了”让威廉开心“才开始写的日志。而,从最初在英国西南部,华兹华斯兄妹与柯勒律治初相识时,两位大诗人便有阅读多萝西的日记以获得灵感的习惯。因此,在这两版诗歌的八年间,华兹华斯可能是重新读了妹妹的日记,于是有了灵感,增加了这样一个诗节,不让读者错过水仙花摇头晃脑舞动的姿势。

华兹华斯画像(1798年)
正是因为华兹华斯这首诗的创作时间晚于多萝西的日记时间,并且诗中的词汇、画面与多萝西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以华兹华斯诗歌与书信的著名编辑同时也是多萝西最权威的传记者E.D.塞林克特(Selincourt)为代表的学者们都认为华兹华斯这首诗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多萝西的日记。二十世纪几次的女性主义运动中,一些女性学者指责华兹华斯对妹妹的剽窃。更有者批评华兹华斯将两个人的共同体验转化成他的个人体验。我们从多萝西的日记中也可以得知,叙述者并不是“孤独地漫游”,而是与妹妹一起。研究华兹华斯兄妹的牛津大学学者露西・纽琳(Lucy Newlyn)认为对华兹华斯如此的批评有所不妥,因为这样做无疑于是批评他创作的方式与体裁。在她看来,兄妹这样的创作方式会让我们意识到多萝西的日记在华兹华斯的家庭记忆尤其是共同记忆中与家庭创作活动中的关键作用。(Lucy Newlyn. William & Dorothy Wordsworth: All in Each Other,2013: 159)纽琳在此处用了“家庭创作活动”,但她并没有解释这一点。华兹华斯的“家庭创作活动”除了包括他写诗,妹妹多萝西写日记,妹妹与妻妹阅读、建议修改他诗中的一些内容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很容易忽视的一个人,诗人的妻子,玛丽对创作的参与。在对华兹华斯的研究史中,玛丽一直是一个掩藏在华兹华斯兄妹之后,存在感不是很强的角色。尤其是华兹华斯兄妹一生与彼此相伴和浓烈情感,让玛丽很久以来不太为人所了解。我记得很久以前,在一篇介绍华兹华斯的文章中,作者甚至写,华兹华斯一生未娶,终生与妹妹多萝西相伴。当时我只觉得荒唐以及作者的不够谨慎认真,现在想来,如果连他的写作者都会有这样的感觉,那至少说明,玛丽的存在确实是很模糊的。直到1982年,贝斯・达令顿(Beth Darlington)编辑出版了华兹华斯与妻子玛丽在1810至1812年之间不为大众所熟知的书信,人们才了解到充满炽热情话的书信并非只属于这一阶段,也就是说他们结婚后的第八年至第十年,而是诗人与妻子之间一生的状态。这些书信反映了玛丽作为细心照顾其生活,以及在创作中批评、督促甚至参与的角色与形象。也是在《芬威克笔记》中,华兹华斯指出《水仙花》这首诗中最好的两句“它们常在心灵中闪现,/那是孤独之中的福祉”(飞白 译 they flash upon that inward eye/Which is the bliss of solitude)系妻子创作。
或许我们可以循着纽琳所说的“家庭创作活动”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在1804年的一个晚上,华兹华斯与妻子还有妹妹坐在“鸽舍”的壁炉旁,一起回忆着1802年那个对他们三个来说都比较重要的春天。华兹华斯在为与玛丽的婚事来回奔走,多萝西内心也经历着自己是否在婚后的哥哥、嫂子的家中继续受欢迎的焦虑,玛丽经历了春天、夏天,在那年的秋天嫁给华兹华斯。各自的回忆与壁炉里的火焰交融,让房间尤其温暖。多萝西突然翻出那天的日记,在炉火旁读给哥哥和嫂子听。华兹华斯也许是在这样重现的回忆中萌生了创作水仙花这首诗的灵感。虽然几乎每个学过华兹华斯的人都记得他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所言的“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并且以此来指责诗人理论与创作实践不一致。因为,关于水仙花的这首诗并未出现在诗人兄妹遇见水仙花的当下。但大家容易忽略的是,那句话只是诗人为了铺垫后面的思想所用的引子,他的重点其实在后半部分,即,“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曹葆华 译)。而时隔或许半年、一年、甚至两年才出现的《水仙花》刚好是这种理念的完美体现。这首诗是不是出现在如诗中所描述的那般诗人独卧的状态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首诗来源于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这种回忆无论是诗歌所表达的个人回忆还是真实中的群体回忆也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与诗人心灵共舞的水仙花里,我们作为读者也感受到了回忆的诗情与哲思。
从三个诗节到四个诗节
华兹华斯对诗歌的修改有一种近乎强迫症的迷恋。虽然大部分诗歌只是经历个别词汇的修改,但有的作品,比如自传长诗《序曲》,从最初计划的五卷到1805年完成的十三卷再到1850年出版时的十四卷,华兹华斯对它的修改持续了一生!《水仙花》也属于修改幅度比较大的一首,除了修改每个时节中的一些词汇之外,最大的变化便是从最初的三节到1815年的四节。
1807版的三节诗中,第一节是描写“我”像山谷间的云朵一样孤独漫游,突然看见很多水仙花在湖边、树下舞动。第二节中,叙述者将视线投向水仙花旁边的湖浪。但诗人的落脚点还是为了突出水仙花的快乐。即使湖浪再舞动,水仙花还是胜它们一筹。有快乐的水仙花为伴,“诗人”无法不开怀。他盯着水仙花看了又看,但当时从未想过它们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财富。从第二节的第五六行开始,已经开始呈现典型的诗情与哲思的结合这一特点了。这也为第三诗节做了铺垫。因为在第三诗节中,在长椅上茫然独卧的“我”,突然在脑海中闪现过当时的水仙花。于是,“我”内心充满快乐,与水仙花共舞。华兹华斯惯常性在讲述完自己或别人的经历之后要进行一番评论,从对感受的抒写升华为反思性的表达,从外在眼睛对水仙花的“看到”(saw),到“内在之眼”(inward eye)即,“心灵”对水仙花光芒的看见与感悟,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是他思想的闪光点,是自然与人类心灵的交融。这也是华兹华斯之所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标志性要素之一。这首诗在当时的《两卷本诗集》中被诗人放在第二卷中的“我自己的心绪”(Moods of My Own Mind)类别中的第七首。
1815年华兹华斯将这首诗收录在《诗集》的第一卷中,归在“想象力之诗作”类别中,这首诗的位置在第一卷的倒数第五首处。第一节、第三节与第四节与1807版的三节诗相比,除了修改了个别词之外,基本意思保持没变。最大的变化是增加的第二诗节。增加的内容大概意思是说,湖湾成千上万的水仙花像银河里闪烁的星星一样接连不断,并且摇头晃脑地欢快舞动。
华兹华斯为什么要加入这一诗节?
应该不会如上文中所讲的那样,只是为了告诉读者水仙花摇头晃脑的舞动姿态。增加的这一节中,很重要的一个比喻是将舞动、闪烁、成千上万的大片水仙花比喻成银河里闪耀的星星。华兹华斯本人从没有解释过这一点。包括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诗人与思想家马修・阿诺德以及华兹华斯在二十世纪的后人乔纳森・华兹华斯在内的很多学者都认为华兹华斯修改后的作品不如修改之前的好。当然也有以扎卡里・里德尔(Zachary Leader)与华兹华斯的另外一个后人安德鲁・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认为应该遵从诗人本人的意愿与理念,以修改后的作品,尤其是最终版本为权威版本才是正确的。这种争议就如对于华兹华斯分为前期革命的华兹华斯与后期保守的华兹华斯还是只有一个从未改变的华兹华斯一样,从来没有定论。 但他们独独没有对这首诗的修改进行过好与坏的评价。事实上是,从1804年这首诗完成到今天,人们知道的几乎只有修改后的版本。很多诗歌选集也是自动选择修改后四个诗节的版本。国内对这首诗的所有译文也都是根据四个诗节的版本翻译过来的。不像《序曲》,我们现在依然有1799年两卷本的版本,1805年13卷本的版本,1850年14卷本的版本。诺顿出版社甚至将这三个版本并列,让读者来决定每个版本的优劣。若非1804年的五卷本《序曲》没有完整的清晰可认、可印的版本,诺顿出版社应该会同时将其并列印上。国内学者丁宏为教授的《序曲》译本选自1850年的十四卷,初次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出版于1999年,修订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丁教授在初版的前言中提到了《序曲》的版本问题。但对于水仙花这首诗,人们几乎忘记了这首诗还有一个三诗节的版本。青睐华兹华斯诸作品的未修订版的编辑与学者们也从未以水仙花这首诗为例来证明华兹华斯修改作品的失败之处。

1807年《两卷本诗集》扉页
1807年的《两卷本诗集》包含很多现在成为经典作品的诗歌,比如《我曾在海外的异乡漫游》、《水仙花》、《西斯敏斯特桥上赋》、《决心与自立》、《不朽颂》等,但当时这本诗集与诗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以致华兹华斯在接下来的七年内没有出版任何诗集。诗集出版后,一八0七年十一月四日,华兹华斯在写给其作家朋友弗兰西斯・兰厄姆(Francis Wrangham,1769-1842)的信中提到一篇文章批评诗集为一堆无稽之谈,而且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作品。华兹华斯提到的这个批评虽然听上去很多恶意,但这代表了当时大部分评论家对包括《水仙花》在内的这卷诗集的看法,主要针对其看似琐碎、细小且无意义的主题。在诸多恶评中,有不少评论家肯定了诗人的才华,但非常担心如此潜质太多浪费在雏菊、水仙花、小白屈菜等花草之类不入流主题的作品。兰厄姆与其妻子表示了对《水仙花》的欣赏,华兹华斯的艺术赞助人同时也是画家的博蒙特爵士的一个朋友也通过博蒙特夫妇向华兹华斯转达了对这首诗的喜欢。华兹华斯在给博蒙特的书信中特别指出,只有喜欢像《水仙花》这样安静、轻柔的诗作的读者才能快乐地穿过诗人幽深的诗歌之旅。华兹华斯本人对这首诗有很高的认识与期待,认为它代表了他创作的精神,但评论家对这首诗之琐碎、细小、微不足道等的批评也不是对华兹华斯没有影响。
或许是这些影响带来了1815版《水仙花》内容与结构的改变?
华兹华斯虽然从来对批评没有好感,他的书信中满是对朋友、家人、批评家批评与建议的驳斥以及对自己的辩护,但有趣的是,无论是妹妹多萝西、妻妹萨拉,还是朋友柯勒律治,以及熟悉不熟悉的批评家的意见,都会在华兹华斯修订版的作品中可寻得一二痕迹。如此,批评家对《水仙花》这类诗的批评并非让华兹华斯无动于衷。
他在增加的第二节中,加入了银河、星辰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这首诗的视野,不仅仅在小花儿与诗人自己的心灵之间了。因为无论是小花儿,还是诗人自己的心灵都是批评家批评所在。对他们来说,前者不值一提,后者显得诗人太过自我。1807版的《水仙花》第二节便是“诗人怎能不满心欢乐!”(飞白 译)这样对诗人自己心情的描写,兼之第三节是进一步诗人内心状态的描写。如此读来全是批评家笔下的“小花”与“自我”。1815版的《水仙花》第二节的前两行对星辰、银河的描写能让读者暂时离开眼前的水仙花与观花有感的诗人,或者可以让读者将水仙花与诗人放在宇宙的大空间中去。1815版《水仙花》结束处,华兹华斯特意注释:“这些诗节的主题是一种基于想象力的基础感受和简单印象(仅次于视觉的效果),而非极尽想象力之作(than an exertion of it.)”华兹华斯在“exertion”(用力)这个词处用了斜体,以示强调。他这样说明或许在回答一些批评家对这类诗的“简单”与“微不足道”的批评吧。除此之外,华兹华斯从未谈起过这次修改。除了内容上的顾虑,诗节的数量来说,四个诗节的诗歌是大家更为熟悉的。所以,这或许也是华兹华斯修改这首诗的原因之一。

《威廉·华兹华斯传》
水仙花有很多种类,颜色有不同。有浅黄色的,有金黄色的。就视觉的冲击来讲,金黄色应该更胜一筹。所以华兹华斯也是在增加诗节的同时,把第一诗节中的第四行“舞动的水仙”(dancing Daffodils)改成了“金黄的水仙”(Golden daffodils)。这个颜色,一方面对应“突然”(all at once)这个词带来的冲击与戏剧性,也是与原来第二诗节,修改后的第三个诗节中的 ”财富“(wealth)对应。
近半个世纪之后,英国批评家、诗人、文选编者弗朗西斯・泰纳・帕尔格雷夫(Francis Turner Palgrave, 1824-1897)在1861年编纂的直到今天还在印的影响巨大的《英诗金库》(The Golden Treasury)中收录了华兹华斯这首诗,帕尔格雷夫收录的是1815年四个诗节的版本。帕尔格雷夫的诗选被视为最好的诗选,不仅在英国很受欢迎,也被当时正盛的大英帝国推广到世上所有的殖民地去。帕尔格雷夫本人在《英诗金库》的前言中寄望:希望在任何英格兰的诗人们被尊崇的地方,以及任何说英语的地方,这本诗选都能寻得合适的读者。也是从这里开始出现在英语国家以及其他国家英语文学教育的教材中,四诗节的《水仙花》就这样走向了世界,直到今天。如帕尔格雷夫的儿子所言,《英诗金库》让很多原本会被遗忘的最好的英诗得以被各行各业的人喜欢。《水仙花》无疑是其中一首。索里兹波里大主教G.D.波义耳(Boyle)在回忆帕尔格雷夫时曾特别指出,《英诗金库》对华兹华斯诗歌的精心选择重新燃起了读者对华兹华斯的兴趣。197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杰弗里・达朗特(Geoffrey Durrant)研究华兹华斯的专著《华兹华斯与大系统:华兹华斯诗性宇宙研究》。其中一章大篇幅地讨论了《水仙花》里的大宇宙,以及宇宙之中人的位置。作者认为这是这首小诗经久不衰的最重要的原因。
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华兹华斯本人会对这两个现象有何解读。他不会想到这首曾被评论家讥笑的小诗成为世人认识他的入口,他亦不会想到他一直寄望的后人在这首诗里真的看到了大宇宙。
题目
华兹华斯在世时出版的诗集中,从未以《水仙花》作为这首诗的题目,那么《水仙花》到底是如何成为这首诗的题目的呢?尤其是国内的诸多译文均是以花名为题,有的以《咏水仙》(顾子欣 译),有的是《水仙花》(飞白 译),有的是《黄水仙花》(郭沫若 译),有的以《水仙》(孙梁)为题。
这首诗初次出现在1807年的《两卷本诗集》中时,位置在第二卷,归类在“我的思绪”之下,第七首。在目录中无题目,只有标示位置的数字“7”,后面直接是虚线和页码。诗歌起始的49页题目处只有一个数字与句点“7.”,下面是一个粗横线,然后是诗歌。这首诗第二次出现是在1815年华兹华斯出版的包括《抒情歌谣集》在内的两卷本合集《诗集》的第一卷中。在《诗集》中,《水仙花》被归在“想象力之诗作”中。“想象力之诗作”跨整个两卷,《水仙花》在第一卷的部分。华兹华斯在目录中用了“我孤独地漫游”(I wandered lonely)为题目。但是这首诗的起始页328页上题目处只有一个罗马数字与句点“XIII.”,并未用目录中所列的为题。此后1827年的五卷本合集中,1832年的四卷本合集,1836年的六卷本合集,1849-1850年的六卷本合集中均沿袭1815版的用法,只不过是1827年以后,目录中的题目变成了“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诗歌页的题目处均用的罗马数字。但自1807年以来,华兹华斯在书信中但凡提到这首诗时均用的是《水仙花》(The Daffodils)。奇怪的是,华兹华斯未选用《水仙花》作为题目。如果说他在1807年的诗集出版前曾有此想法,那么在诗集被批评写花花草草等无足轻重的主题之后,华兹华斯或许更谨慎用《水仙花》作为题目了。华兹华斯兄妹的研究专家帕梅拉・伍夫(Pamela Woof),她现在也是华兹华斯信托的主席,曾经给出另外一个原因。她认为从诗歌的第一节看来,诗人在独自漫游,突然看到一群水仙花。“突然”(all at onece)会对初次读这首诗的读者有一个冲击力。或许,华兹华斯本人并不想在题目中透露出这种“惊喜”。
1843年,华兹华斯被授予桂冠诗人的称号,那一年,詹姆斯・彭斯(James Burns)编辑的《华兹华斯诗选》(Select Pieces from the Poems of Wordsworth)中第一次用《水仙花》(The Daffodils)为这首诗的题目。1861年,弗朗西斯・泰纳・帕尔格雷夫在共有288首诗中的《英诗金库》中收录了《水仙花》这首诗,位列第253首,并且以《水仙花》(The Daffodils)为题。自1861年之后,这首诗便以《水仙花》而闻名,以致很多读者以为《水仙花》便是华兹华斯给这首诗的命名。这或许也是国内译诗以水仙花命名这首诗的根据所在。事实是,华兹华斯虽在书信中以此命名这首诗,但出版的诗集中从未以此为题。奇怪的是,《英诗金库》问世时,华兹华斯才刚刚离世11年,其书信与手稿尚未问世。帕尔格雷夫为这首诗命名的灵感肯定不是来自于华兹华斯的书信与手稿的启发。帕尔格雷夫命名的依据或者是这首诗的主题,或者是詹姆斯・彭斯的先例。他本人没有解释过,我们也无从猜测。但帕尔格雷夫的诗选影响了大半个地球,《水仙花》最初也是这样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吧。
华兹华斯曾经在1807年回给弗朗西斯・兰厄姆的书信中说,《水仙花》找不到它的读者。在深受各种批评打击的心态下,华兹华斯曾经写信给博蒙特夫人说他的声名在未来的读者那里。54年之后,帕尔格雷夫这位未来的读者不仅欣赏《水仙花》,而且理解到了华兹华斯这首诗的诗眼。这对已经仙去的诗人来说,是多么大的慰藉呵!
帕尔格雷夫在《英诗金库》的前言中说,好诗是那些与诗人的天才吻合的作品。华兹华斯的伟大性在于他在自然与人的心灵之间建立的联系,这一点在他同时代的读者与批评家那里并未很清晰地被看到。时间与帕尔格雷夫让更多后来的读者认识到华兹华斯的伟大性,也让这首小诗的经典性愈加明晰。华兹华斯早在1798版的《抒情歌谣集》中已经疾呼:以自然为师(let nature be your teacher)。他一生的生活与创作正是对此的践行。《水仙花》也是其中一个例子。我们今天已经很习惯地认识到大自然对人的心灵的作用。如果我们在一朵花中寻得平静与力量,不会再被人笑话。谁能说这里没有一丁点华兹华斯的功劳呢?

华兹华斯寓所(1813-1850)
华兹华斯自15岁开始创作直到生命的终点,创作生涯长达65年,创作长长短短诗作900多首,但在世时没有一部诗集像沃尔特・斯各特或拜伦的作品那样畅销。不乏像柯勒律治那样自一开始便认识到他的才华与伟大的人,但他的伟大得到广泛的认可与接受也是在两个世纪的起起伏伏中才最终发生。《水仙花》走过两百多年,给英格兰各个角落带来了水仙花,从二月开到四月。当时让华兹华斯兄妹惊喜与快乐的水仙花亦给无数的后来者带来惊喜与快乐。
1847年,华兹华斯痛失爱女,与妻子玛丽在家旁边属于他们的山坡上亲手栽了大片的水仙花,以寄托老两口的哀思。水仙花田在瑞德村的教堂旁边。现在以“朵拉之地”(Dora’s Field)而闻名,受华兹华斯信托保护。直到今天,每年的三月,大片的水仙花田依然在盛开。就如诗中所描述的,千朵万株的金黄水仙在树下舞动。1850年华兹华斯去世,1855年,多萝西去世,1859年玛丽去世。华兹华斯与家人安息在他们钟爱的格拉斯米尔的圣奥斯瓦尔兹教堂墓园中。与墓园有半墙之隔的是“水仙花公园”。没错,是以“水仙花”命名的花园。花园里铺满了世界各地的诗歌爱好者捐献的石板。走进花园的第一块石板上便是《水仙花》的第一诗节的前四行。描述的是,诗人如一朵孤云独自漫游,突然看见很多金黄色的水仙。进入花园,右手边便是墓园,春天的花园里开满了水仙花。在公园的尽头,是静静流经格拉斯米尔的罗莎河,河边有一块石碑,上面刻了《水仙花》的最后一节。站在那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华兹华斯与家人的墓碑。在这个季节,经常看到诗人的墓前有一大束的水仙花,金黄、温暖,如他当年所看到的那样。

英国为纪念华兹华斯诞辰250周年发行的邮票
2020年4月7日,是华兹华斯的二百五十诞辰。今年的水仙花也是格外美丽,但新冠病毒席卷英国,让很多原本从三月份就开始的一系列活动,比如在公交车上读华兹华斯的诗作,在华兹华斯故居研讨他的作品等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原本在扩建希望在诞辰当日重新开幕的博物馆与故居现在看来也没有太大的希望,我们三月中旬去看时依然是建筑工地的模样。新冠病毒定会影响所有庆祝活动的开展,但它无法影响的是,包括英国湖区在内的各个角落水仙花的盛开。在任何一个地方,大家看见水仙花,或许会说:“看,华兹华斯的水仙花!”然后再情不自禁地吟诵:“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