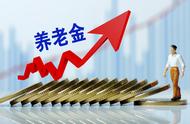他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情万丈,也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淡泊洒脱。
他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柔浪漫,也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缱绻深情。

同样的天纵之才,比之李白,他多了几分忧国忧民的情怀,同样的命运多舛,比之杜甫,他又多了几分乐观旷达的心态。
从眉州到汴州,他历遍了人生的繁花似锦、烈火烹油;从惠州到儋州,他也受尽了命运的大起大落、悲欢离合。
举杯提箸,便带起了满身的人间烟火,挥毫泼墨,又占尽了尘世的绝顶风流。
人生如逆旅,他竹杖芒鞋的身影在时光中轻轻走过,两宋三百年的绝代风华,才最终成就了一个光耀后世的名字——苏东坡。
眉州:用神话的开头为天才加冕北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7)冬天,四川盆地西南、岷江之畔的风雅小城眉州,一个名叫苏轼的男婴呱呱坠地。
据说其出生前一年,家乡附近的彭老山便开始百花不生、草木枯萎,连鸟兽亦避走它处,直到多年后当地人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此地灵气尽被苏轼一人吸走。
在中国历史上,每逢王侯将相诞生,必然伴随天地异象,如唐太宗李世民出生时,便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宋太祖赵匡胤降世时,也是“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
类似这种声、光、电毕现,色、香、味俱全的离奇故事,似乎是专门为了证明大人物们的“生而不凡”、“天命所归”而添加的注脚,而这种充满神话色彩的叙事风格,也几乎成为后世史书的惯用笔法。
但九百多年前彭老山那一场突如其来的气运流转,或许并非出自史家事后的刻意编排,我更愿意相信,那是大自然对这位中国数千年来独一无二的天纵之才,所给予的绝无仅有的慷慨馈赠。
长子苏轼出生两年之后,1039年,苏家又迎来次子苏辙的降生。父亲苏洵为两个儿子取名都与“车”相关,其中也是大有深意。
车舆,通常为负载之物,而承载万物的大地,自然便是最大的车舆,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与苏洵对儿子的殷切希望如出一辙。
只是苏洵可能也没有想到,“轼”、“辙”这两个字,冥冥之中也昭示了兄弟二人一生的命运。
“轼”是车上的扶手,是整架车最显眼、装饰最华丽的部分,苏轼天纵之才,无疑是两宋最耀眼的风流人物。

而“辙”是车辆碾压后留下的痕迹,虽与车的本体并无关联,但无论车辆发生怎样的灾祸,车辙都不会被殃及池鱼。
所以,“木秀于林”的苏轼,尝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而与兄长相比,苏辙的才情虽稍逊风*,但仕途却相对平顺,不似其兄一生坎坷、颠沛流离。
汴州:他一出场,便惊艳了时光仁宗嘉佑二年(1057),苏洵陪同苏轼、苏辙兄弟由眉山老家赴京城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
当苏轼第一次出现在开封街头时,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年轻人,会在今后的文坛掀起怎样的滔天波澜。
1057年的进士科,在中国科举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唐宋八大家”中苏轼、苏辙、曾巩三人均在此科及第,而且还涌现出了九位宰执和大批顶尖学者,因此也被后世公认为千年科举第一榜。

而颇具传奇色彩的是,苏轼的应试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令主审官梅尧臣拍案叫绝之余,其中又有“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人。皋陶曰*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这样的佳句。
作为整篇策论的支撑性论据,这个皋陶欲*人而尧劝其宽恕的典故,论点清晰、论据充沛,且用典十分到位。
梅尧臣虽倍感精妙绝伦,但饶是这位满腹经纶的大儒,脑海中穷尽四书五经,一时之间也不知典从何来。
连忙将此卷送至另一主考官员,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共同审阅。
从宋朝开始,所有科举试卷均采取“封弥”这一保密制度,即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等基本信息用纸糊住,以保证阅卷的公平。
苏轼的文章欧阳修内心也是大加赞赏,但其暗忖如此锦绣文笔,很有可能出自门生曾巩之手,为避免嫌疑,欧阳修只得将这份理应独占鳌头的试卷判为第二。
不过颇为尴尬的是,放榜之后,欧阳修才发现,原本位列第二、如今高居榜首的,正是其弟子曾巩,而那篇精妙的文章,竟是出自一位叫苏轼的四川举子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