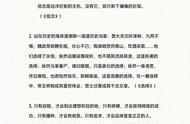作 者
林雪萍:北京联讯动力咨询公司总经理,上海交大中国质量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美国创新是一个系统。它就像是一座活火山,一直喷发出惊人的能量。在当下,创新成为人们渴望重塑板块的熔岩洪流,那么它到底从何而来?
美国的三个片段,或许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
硅谷传奇硅谷的缔造者,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晶体管之父肖克利,的确是他,将晶体管的技术引入到美国西岸,自此开创了大规模半导体的时代。有人认为是创立仙童半导体公司的八个“叛逆”之徒。这些受肖克利吸引却又无法忍受科学家多疑而自私的怪癖最后出逃,成立了仙童公司。仙童半导体是一个核裂变一样的存在,不断释放能量。它孵化演化成英特尔、德州仪器、美国国家半导体等,这是美国芯片公司的开山鼻祖。硅谷半导体公司的每一位工程师,几乎都在仙童公司待过。还有人感觉是惠普,它开辟了美国“车库创业”的文化,这成为美国创业符号的一部分,也是美国庞大的创新神话体系中的一个组成系统。
然而,真正的硅谷之父,还是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特曼。
他将斯坦福大学最早所拥有的高压电力学科的优势,转化为电子。
他开创了斯坦福大学的应用型研究,从而可以获取国防部合同的丰厚经费。这改变了美国国防部一直依赖东海岸麻省理工的传统。在那里,美国极负盛名的创新128公路,就是围绕麻省理工而来,国防部是最重要的赞助商。这诞生造就了雷神这样的公司。特曼,将这些近乎无限制的经费,分流到了美国西海岸。
然而,这些举措都还只能让斯坦福大学,成为一座著名的研究型大学,那对于创新是远远不够的。这才引出了特曼对于创新的贡献:推开大学封闭的大门,让创业者自由进入。这种将大学研究与创业公司的无缝连接,构建了美国创新体系极为重要的一块基石。
特曼在斯坦福大学周边开始规划创业园,这比美国东部创新的128公路,更加具备主动性。通过一系列的方式,特曼建立高校基础研究与初创企业之间的旋转门。基础研究,可以毫无保留地流向初创企业,这开始诞生了代表美国创业文化的惠普。惠普成立初期是做音频失真分析,给汽车使用。这种技术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基础研究,被特曼慷慨地赠予惠普的两位创业者。惠普是到后来才加入到个人电脑的系列,成为当今三大电脑巨头之一,且基业长青。
惠普并不是孤例。瓦利安公司的情况,并无两异。这是科学仪器磁共振最为重要的企业。初期也是从一个斯坦福做原子核的教授那里获得了共振技术,一种用来加速电子的空腔谐振器。瓦里安兄弟用这种菱形管做成飞机导航系统,而斯坦福大学则聘用他们担任无薪研究助理,提供实验材料,也可以免费使用实验室。而作为回报,斯坦福大学将获得瓦里安公司通过实验产生的任何专利的一半权利。
美国创新系统给人的启发之一,就是社会资源没有边界,商业利益清晰分割。大学没有围墙,大学实验室就是初创企业的家,但是大学也并非免费之地。科学和商业这二者的关系,会写的一清二楚。
因此,美国企业有捐助大学的传统,也就不难理解。创业成功的公司,也形成了慷慨捐赠的传统,让大学经费充裕。
斯坦福大学有知识共享的传统。“自造(homebrew)计算机俱乐部”,就是计算机迷的自发组织。这为硅谷计算机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智力胎盘。苹果电脑的乔布斯传奇就从这里开始。
特曼建立了大学工业园区,让学校成为工业地产创新灵魂的源泉。吸引了柯达、洛克希德等东部公司的加入。来自大学源源不断的创新人才、跃跃欲试的初创公司和大公司的研发体系,相互启发,相互振荡加速,成就了硅谷强大的计算机气场。
而灌溉硅谷土地的幕后园丁特曼,才是硅谷真正的缔造者。他让斯坦福大学成为一个大学、本地企业和城市火力的连接枢纽。
我们需要好的园艺大师,但我们也更需要大师级园丁。大学和本地城市的共生关系,也是令人极其期待的创新源泉。
智库神话就国家战略决策而言,兰德是一个神话,也是刻意创造出来的一个智库神话。美国擅长讲故事,将各种卓越的实践提炼成一种神话,超越了国家的界限。这是一种软实力的表达。
兰德很容易以智库的神话,出现在人们的脑海里。但它作为一台思想创新的机器的本质,也容易被隐藏起来。我们对它的决策过程却往往知之甚少。这容易导致对智力创新的无视和浅薄的认识。《兰德公司与美国的崛起》事无巨细地介绍了兰德公司在二战后非常活跃的三个十年。一看书名就知道,这又是另外一个美国神话的套路。但兰德对美国政府、美国民众的思维框架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神话的含义。
当年的朝鲜战争,对于中国是否会对美军进入朝鲜作出反应,兰德给出了惊人的预测。
1948年兰德成立,源自骄横跋扈的美国空军将领的任性臆想。起步看上去很随意,兰德的纲领非常简单,就是“运用民间技术资源研发新式武器”。而钱,则随便花,不求特定目标,但求有五年、十年的颠覆性技术。
在二战期间,美国国防部享到了科学无穷的好处。麻省理工的雷达研究,成为美军制胜的重要武器。更不用说曼哈顿计划的原子弹,直接终结了日本的抵抗。当时美国科学家,很多都接受了战时动员,科学家和企业家商人形成活跃的联盟,为军队服务。
但在和平时期,老派联盟精神已然*,许多科学家需要返回自由的岗位。如何留住二战期间的科学家对军事的独有贡献?
美国空军很快意识到这一点。这也是美国海、陆、空三军竞争国防经费所造成的。空军希望更有思想上的“制空权”,从而形成对另外两个军种的压倒性优势。空军将领的想法是,用专职的民间组织,来完成对科学家的笼络。兰德的定位,就是源自这样的动机。RAND这个名字就是取自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究与开发)——尽管兰德在后期则放弃了“武器开发”。这也限制它成为一个体量巨大的公司。兰德则专注于制造“思想原子弹”,用想法、思维框架来驾驭世界。
有了兰德运作的机制,我们终于可以去理解美国的国防武器和民用工业合二为一的“军工复合体”体制。二者并非天然没有缝隙。缝隙之间,它其实是有着强大的民间桥梁,在进行连接。
二战后英国和法国都把重要的军事工业国有化,美国却没有。它把科学研究发展工作承包给私有机构。这让军队的创新,保持了极大的灵活性。兰德,正是起着连接军事计划和民间发展的桥梁作用。
兰德的创立,正是确保科学家依然可以行之有效地为国家命题所服务。这样的民间组织,就是充当冷静的科学容器。
兰德精于计算,准确地说善于研判复杂系统的走向。它的基础毫无疑问是数学家,因此像冯·诺依曼这样的科学家天才在其中也就不足为奇。但真正令人奇怪的是,它的成员组成成分,远比人们想象得要复杂的多。提出了著名的“囚徒困境”的数学家纳什也是兰德成员。他关于博弈论的思想,回答了“人”作为最不可控的因素,如何改变了决策的模式。这对于美国的核威慑、星球大战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影响。
这些看上去是军事选项的刚性问题,其背后是柔软的人性心理和社会学问题。兰德所倡导的跟前苏联的“导弹差距论”,为赢得总统选举的肯尼迪,提供了影响民众心理的重要武器。深知国防部漏洞而无法正面回答的副总统尼克松,则在选举中败北。
正是这些影响深远的理论,才让兰德成为光芒四射的智库。兰德是数学家的乐园,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都是这里的常客。但它也小心地防范“数据至上”可能产生的漏洞——社会学往往就是数学家的软肋。因此,兰德也成立了社会学系和经济学系。
人性的多样性,一直是大系统最复杂的变量。而兰德通过跨学科,很好地驾驭了大工程所需要的背景多元化、人才多样化的特点。兰德就像是一种混合态半透明的科学实验室,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学科,都可以混合。它搅拌了那些本来互不关联、原料各异的烧杯。于是到处都是魔法般的火焰。
重要的是它研究的独立性,尽管它的捐助资金早期主要来自空军,但是它依然可以对空军骄横的态度置之不理,得出未必迎合金主的结论。兰德像是一个独立飞行的蜂群,博采百家花蜜,它的重要理论是,把起源于英军指挥部的运筹学,创建为一种“系统分析”的复杂系统最优化的理论。这是一种用量化来对待软科学的方法,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评估政策的科学性。
系统分析,成为美国国家决策机构非常依赖的一种分析方法,也让兰德得以声名鹊起。兰德的系统分析,被看作一种“美国精神”的表现。这种赞誉的本身,其实也正是美国善于造神的一种方式。
对于兰德的魔法,还有一个重大的创新视角有待厘清,那就是兰德本身是一个大工程组织。
人们对大工程组织,并不陌生,举国体制就是如此。然而,官方的大工程组织是昂贵的。曼哈顿计划不可持续,中国的“两弹一星”的模式,也很难待续。大工程组织,适合解决攻坚问题。然而,它要求供应链一直保持刚性而非弹性、私有而非公有,这都限制了供应链的连接力,从而无法长期发挥作用。因此,并不适合解决连续的型号迭代。
大工程组织的核心是协同。而美国保留大工程组织的方法是,激活民间的组织能力,而非采用国家编制下的国家机器,后者很容易产生刚性而无法适应创新所必须的弹性和活力。而兰德正是大工程组织的代表,也是民间大工程组织的样本。
民间大工程组织,有效地保留了基础科学家的冷静和独立社会学家的理性。只有如此,才能大规模地组织民间力量,在智力创新的领域闪闪发光。
工业研究院的闪亮登场创新的主体,自然是企业。因为创新的本意,就是要在市场中获得利润。创新本身是一个闭环,单纯的科技力量,其实并不是创新的全部。这就不难理解,美国企业的工业研究院,会成为美国工业创新强大的发动机。除了大学和政府机构的基础研究所形成的转化,企业自备的研究院贡献了大量的创新成果。
极负盛名的自然要属美国通用电气GE和贝尔实验室。GE工业实验室规模最大,它充分吸取了爱迪生对应用研究的理念,那就是创新是有规律的,可以像地里的庄稼一样按季节成长和收割。
而在此之前,人们都认为创新是一种自发的冲动,就像闪电击中一棵大树一样不可琢磨。
表露同样看法的,还有技术常青树的3M公司。3M一开始的创新道路很不顺利,但它从外部邀请的CEO,创建了一条“小物创新”的道路。简单地说,就是挖掘创新的规律性,使得创意产品层出不穷。3M属于藤蔓式创新,每种技术都按着自己的分叉点无限度延伸。
这意味着一种技术可以吃干榨净。一个菲涅尔透镜的原理,前后用上六十年,从反光服,到投影镜头。这就是3M研究院的创新魔法。
而杜邦的中央研究院,则进一步细分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使得化学合成品不断翻陈出新。
在这些星光灿烂的研究院中,生产柯达胶卷的伊士曼公司的工业研究院的价值,似乎被低估了。
伊士曼公司的工业研究院在1912年成立,这是当年非常时髦的一种做法。到1918年美国有不到400家研究院。而到了1930年,则达到1600家。这些研究院,为即将到来的美国制造巅峰时代,准备了充足的弹药。
虽然也是一个发明家,但伊士曼本人对研究院并无太深的期望。设立研究院,只是一种朴素的信念。他将无限的信任,交付给他请来的研究室负责人,并承诺连续投资十年,不求回报。如果说回报,那就是为“摄影的未来”而负责。
这种浪漫主义的科学信仰,其实并非全是乌托邦之地。
伊士曼所在的时代,美国专利保护也很差,诉讼周期也很长。伊士曼认为只有“以快制慢”,才是发展正道。他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每年都有质量更好的产品,让其他人无法追上伊士曼一样的原创产品 ”。既然专利容易走光,既然专利容易被侵权,那索性就做专利闪电侠,永远跑在前面。伊士曼决定用创新的速度,来摆脱无穷无尽的盗版者和追赶者。伊士曼采用奔跑战士的姿态,实施了“年度产品更新上市”的策略。而这种研发速度,自然意味着需要持续研究作为支撑。这就是战略的连续性,它的画卷往前进一步展开的结果,自然就是设立工业研究院。
伊士曼工业研究院,也是一个另类。它有几条基本原则,至今看起来值得玩味。
第一相信科学的力量。只要研究院积累大量基于实验的事实,企业必然就可以向着真相本质去迈进。换言之,只要做实验,企业自创新。
第二条原则,相信大蛋糕的力量。通过工业研究做大蛋糕,而不是争抢既有蛋糕。哪个行业不内卷,哪个国家不内卷?日本的光伏、电视机、相机这些曾经统治全球的产品,都在内卷中让给了韩国和中国。而至今仍然活跃的半导体设备,也都是内卷之后的幸存物。内卷并不可怕,内卷就是抢蛋糕。但要有气质不凡的企业家去做大蛋糕,这正是伊士曼的想法。这跟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想法一样。他对于工厂效率的提升有着无穷尽的好奇。他对于工业化的看法:重点不是盈余分配,而是增加盈余。只有盈余足够多,分配盈余就不会有分歧。这跟“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完全不同的想法。
第三条原则,相信“民众创新”的力量。这为大家都极为推崇的“创新英雄主义”敲响警钟。伊士曼研究院坚决避免对杰出科学家的依赖。这基于朴素的想法,工业应用研究需要积累事实和测量方法,它只需要时间坐在冷板凳上。即使没有天才之火,依然可以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伊士曼研究院自觉地用这三种观点,来组织日常活动。为了让研究员相互启发,搅拌机制必不可少的。因此,每周会议、完备的实验室和齐全设备的小规模生产车间,都在激荡着人们创新的能量磁场。
伊士曼逐渐抛弃了自发零散创新的浪漫主义,而采纳了组织严密的创新组织。而当创新的经济回报开始加强,专利保护进一步严格的时候,训练有素的创新体操,就会展示规模化的力量。那是美国制造最繁荣的时刻。
小记:复写创新公式美国的创新实践,验证了大学研究、民间智库和公司开发这三者的力量。当然,这一套实践,也在不断的转化,呈现出更加不易察觉的一面。这其中,昔日魔法看上去都已经褪色,诉说这样的故事,已经无法再能激起人们的情绪。人们追逐大模型、量子计算、核聚变这样的新式魔法。然而,那些逐渐被人忘却的创新传奇,完全没有远离,它们的要素已经平凡化,成为美国日常创新系统的一部分。谁能认为空气是昂贵的?既然它无处不在。
然而对于中国而言,创新的渴望才刚刚开始。人们开始对大学作为创新源头充满期望、人们对智库廓清时局迷雾有着刚性的需求,被美国企业所舍弃的昂贵的中央研究院,则正在中国逐渐兴起。一个创新求上的新时代,正在拉开大幕。回顾昔日那些创新系统,很让人容易意识到,创新之路是有规律可循。而那些看上去已经工业化的土地,还值得再精耕细作一遍。
(参考文献:本文的阅读素材来自《美国技术简史》、《兰德智库与美国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