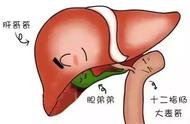“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从表面上看,这两句似乎是即景抒情,写词人纵目郴江,抒发远望怀乡之思,实则是词人积郁已久的情感的总爆发。
王国维的佳句“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句话用来注解秦观这首词的末句,是再恰当不过了。
词中结尾这两句,堪称千古名句,但历代词学评论家对这两句却有着各自的理解和看法,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记载了这样一件词坛轶事:秦观到郴州,作长短句云:“雾失楼台……”东坡绝爱其尾两句,自书于扇,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可见苏轼认为秦观的这两句是《踏莎行·雾失楼台》中最精美的句子,至于精美在何处,为什么精美,苏轼并没有说出来。

苏轼认为秦观此词的精华在末尾两句,对于这一点,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在《人间词话》中写道:“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为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秦观的这首《踏莎行》最精妙的句子是风格凄厉、音调哀婉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两句。
王国维倒是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只是他措辞有点不留情面,对苏轼颇的激赏之语颇有“文人相轻”的意味。
王国维认为苏轼对此词的理解属于肤浅之见。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苏轼是理解秦观的心情的。他自己的仕宦生涯同样受到新旧党争的牵累,也曾自叹“我被聪明误一生”。
苏轼和秦观同样是天涯沦落人,他对秦观的心境与处境是感同身受的,否则何必把这两句话写在扇子上?

倒是王国维未免会受到“皮相”之讥了,假如苏轼看到王国维的评价后,不知会作何感想,哈哈。
当代著名汉学家吴世昌先生认为王国维的看法也有问题,他在《词林新语》中说:“‘杜鹃’句,静安谓此联‘凄历’。又谓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余以为不然,东坡赏‘郴江’一联,正是更深一层,岂徒叹其‘凄历’哉!词下片‘砌成此恨无重数’,一‘砌’字最见功力。”
吴世昌的看法很有道理。按此种说法,“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也应是表达“无重数之恨”的。至于按什么思路,从什么角度来表达的他没有谈。

当代著名词学家唐圭璋先生对秦观的有更明确的看法,他说:“下片,言寄梅传书,致其相思之情。无奈离恨无数,写亦难馨。末引‘郴江’‘郴山’。以喻人之分别,无理已极,沉痛已极,‘宜东坡爱之不忍释也’”。
唐圭璋先生认为秦观以不合常理的方式,以“郴江”“郴山”喻人之分别,表达自己与亲人离别无穷之恨。不少有影响的评论者、欣赏者持这种“无理说”。
《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辞典》中所收录的叶嘉莹所写的欣赏秦观的《踏莎行·雾失楼台》的文章就说:“在如此深望坚实之苦恨中,所以乃写出了后二句‘郴山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的无理问天之语。”
在诗词之中,有时候看似无理之语,正是“至情之辞”。“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二句毫无理性可言。郴江的确发源于郴山,而它的下游果然是流到潇湘水中去的,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