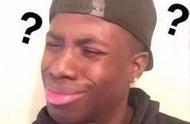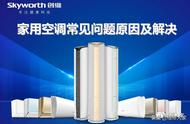“ 长安一片月, 万户捣衣声。 何日平胡虏, 良人罢远征。李白这首《子夜吴歌》描绘了自魏晋至唐代一个普遍的现象———捣衣。
何为“捣衣”何为“ 捣衣”?解释起来就是洗衣时将衣服放在砧石上,用棒敲打。但是捣衣不是洗衣, 捣衣的道具只有两件砧和杵,“捣”的对象是布料而不是衣服。唐代张宣有一幅《捣练图》,上面的女子手执细长的杵,将布料放在砧上,进行“ 捣衣”的动作。这么做的目的,是因为未经捣制的布料是生的,容易破裂,捣制以后称为“ 熟布” ,目的是使其“缕紧则坚” ,比较耐磨。所以“ 捣衣” 不是洗衣,而是对布料进行加工使之耐磨的一个工序。

《汉语大词典》对“捣衣”的解释是:“古时衣服常由纨素一类的织物制作,质地较为硬挺,须先置石上以杵反复舂擣,使之柔软,称为捣衣“。捣衣不是洗衣,因为洗衣服不必非在夜晚进行。洗衣离不开水,但捣衣诗中从未有水的意象出现过。从杜甫 《捣衣》 诗中“用尽闺中力,君听空外音”来看,捣衣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得用力才能完成,显然不可能是洗衣服。
根据有关学者的推测,捣衣即捣练,是秦汉时期产生的一种练丝工艺,是印染前的关键工序。当时的生丝要用微温的水浸泡,帛则要放在楝木灰中浸泡,利用水温和楝木灰中的碱加速化学处理,进一步使丝和帛上的丝胶溶解。浸泡后的丝帛,需用木杵反复捶捣,使丝帛上的丝胶易于随浆水析出,与现代制丝工艺中的“损经” 相似,可使生丝和坯绸更加白净柔软而有光泽。纨、素、流黄等绢类丝织品均须煮制成熟绢后再捣锤。
六朝至唐,捣衣不像现在洗衣,蹲着用小木棒捶打,而是两女子对面站着各执一杵舂打。南朝梁费昶《华光省中夜听城外捣衣》云:“金波正容与,玉步依砧杵。红袖往还萦,素腕参差举。”月光下,捣衣的女子脚步随着砧杵的节奏移动,充分证明是站着捣衣。而红袖往来萦绕,女子洁白手腕抱着杵上下起落,那就说明是两人各执一杵舂捣的协调行动。这充分说明捣衣是在两个人配合之下,进行的对衣服的一种捶捣,是一件很费体力的事情。

万户捣衣声
何为捣衣诗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捣衣诗是西汉班婕妤的 《捣素赋》。当时的班婕妤已经因为被谗而徙居长信宫,可仍时刻不忘皇帝的恩情,每至秋高天寒,她仍于月夜捣帛,亲手为皇帝缝制衣物。在《捣素赋》中,捣衣这一单调枯燥而又沉重的劳动中触及了班婕妤的心灵,不可避免的带有宫怨的意像。这种意像也启迪了后人的创作。
自南北朝到唐代,无数诗人创作了大量的 “捣衣诗”。虽然南北朝的捣衣诗始终没有脱出 “宫怨”、“闺怨”的窠臼,但 “捣衣”及与之相关的 “砧”、“杵”等作为一种独特的诗歌题材,应用范围相当广泛。
六朝的捣衣诗中所描写的捣衣活动大多出现在秋夜,在直接以“捣衣”命名的诗歌中,“秋”“夜”“风”“”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时节天气意象。伴随着它们的,还有“菊”“槐”“草“树”“虫”“鸟”等动物意像。在这些意像中,“秋夜”和“秋风”给人一种清冷孤寂、凄凉寂寞之感,而“明月”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寄托相思之情的意象,在捣衣诗中更容易烘托了惆怅的气氛。诗歌中出现的秋草、秋虫这些景物以及万物凋零、肃*衰败的秋季、鸣叫的秋虫,都起到了烘托主题,渲染气氛的效果。
六朝的捣衣诗中的人物主要是“佳人:’“、“游人”和“征客”。这些“佳人”佩戴着精致华美的饰品,不辞辛苦地为所思之人舂捣纨素;而“游人” 、“征客”作为思念的对象,或远在天边,或戍守边城,与良人不能在一起,因此这些女子要在秋夜里捣素裁衣,缄封寄远。

捣衣
”捣衣诗“中并没有这些女子的外貌描写,仅以“美人”而提之,给人带去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她们在秋风萧瑟的季节为远方的爱人裁制冬衣,那些男主人公在诗歌中不仅是思念的对象,也起到了扩大诗歌意境的作用。特别是“征客”这一意象使捣衣活动和遥远的边戍联系在一起,增加了诗歌的空间内容,突出秋天悲凉的氛围。
从东魏晋到隋朝统一,中国经历了四百年的分裂。在战争中大量北方人民避乱迁徙,侨居江南,离乡别国之恨萦绕在几代人的心怀。他们借怨妇之口,抒发对故国、家乡的无限眷恋,使东晋南北朝闺怨诗大盛。因此争战不已,很多男丁被迫从军征战,或服劳役、徭役,民间处处征夫怨妇,形成了闺怨诗兴盛的现实社会基础。受其影响,捣衣诗也很快由范围狭隘的 “宫怨”题材过渡、发展为范畴较为宽泛的“闺怨”诗。
南朝谢惠连的 《捣衣》、谢朓的 《秋夜》、柳恽的 《捣衣》、惠侃的 《咏独杵捣衣诗》、王僧孺的 《捣衣》、费昶的 《华观省中夜闻城外捣衣》、萧衍的 《捣衣》、庾信的 《夜听捣衣诗》,都形成了一个“写景—容饰—捣衣—裁衣—缝制—念远—独悲”的闺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