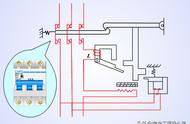(图/《新周刊》)
在这几年,她也经常想生活的意义。如果没有选择“主流生活方式”,没有正常通勤上下班、组建家庭,每天直面自我,与自己的思想相处,需要很高的心理能量,否则很容易感到虚无。但就在这几年,七堇年尝遍了大多数户外运动:徒步、爬山、攀岩、攀冰、洞穴探险、飞滑翔伞、潜水……户外与大自然的亘古与广博,消解了一些她对生活的困惑。
比如飞滑翔伞先得坐面包车上山,然后人再飞下来,一天来回几次。“有时候(觉得这)禁不住细想。从结果来看,上去又下来,多么徒劳啊!但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上去,下来,飞伞,攀岩,滑雪,跳水,哪一样不是如此?运动本身就是一切,它就是你度过这一生的方式。”
往前数的人生里,她经常有竞赛的压力。但这几年的户外生活,给了她极大的安慰。“像我们身后这个无名的小山坡,可能只是给人类世界的精神图景增加了一株小草。写作也是这样,也许不见得被多少人读到,但我用写作去度过我的生命。”

尝试多种户外运动的七堇年。(图/受访者提供)
离开泸州之后,她曾有十多年不再弹琴和画画。在以前,这像是指向妈妈的内在对抗——弹琴和画画,都是妈妈选的;她想要的是写作。但35岁以后,她重新画画、弹琴。
老家的钢琴早已受了潮,音也不准了,可要不是太笨重、太麻烦,她还想将它搬到成都的家里。她重新买了电钢琴,现在早上起床也偶尔会弹弹。那些曾经让她感到痛苦的、枯燥的训练,确实也有滋养她的部分,她如今可以纯粹地享受艺术本身了。
但对她来说,所谓的“和解”,“只是一个叙事上听起来很完美的闭环”。如今七堇年37岁,妈妈已经73岁了。对她来说,“牵妈妈的手,比登山还难”。除了责备,妈妈依然很少表达真正的情感。她们不曾真正地聊天,对话大都是事务性的。直至现在,每个月打的那一通电话,聊天还是只持续1分钟,大多数时候的内容是相互叮嘱注意身体。

(图/《新周刊》)
大学二年级时,七堇年给妈妈写了一封很长的信。那年她20岁上下,每天是易燃易爆炸的状态。看了简媜的《谁在银闪闪的地方,等你》,她第一次意识到,妈妈正在面对孤独与衰老。妈妈生她时36岁,等她进入大学时期,妈妈已经迈向老年了。
“那时我第一次想,也许她也很不容易吧。”在信里,她写了些从没跟妈妈讲过的话:小时候你对我很严格,现在你对我是否满意;她聊了自己身上隐含的自卑情结……洋洋洒洒写了很多,可妈妈没有回信,甚至也没回话。隔了一两个月,她问起时,妈妈才说收到信了。但过去了的事,她似乎不想再提。
情感表达是妈妈不曾学过的功课。后来的这么些年,她们偶尔也会触碰到这个话题,但每回都聊不深,似乎都在回避着,担心再聊下去两个人都会很难过,最后也是徒劳。
不是所有故事都需要以和解为结局。她们各自选择舒适的姿势自处。如今,母女俩分开独自生活。上个月妈妈身体不适,需要在成都做个小手术,却在她家住了几天就回家了。成都那么大,早高峰很嘈杂,路上的人走那么快,妈妈很不习惯。

(图/《新周刊》)
经历过痛苦婚姻的妈妈,也不曾催促女儿进入婚姻。妈妈平时还是住在泸州的职工社区里,和几个认识了几十年的好友维系着一种共居关系:儿女都不在家了,他们互相照料,共同养老。
就连过年,母女俩都是分开过的。去年妈妈就和朋友约定了在海南碰头,73岁的老太太独自开车南下。
妈妈和朋友熟悉的生活是:早上起来浇花、喂鸟,一起打牌、聊天、散步,轮流买菜,请对方吃饭。年轻人想象的社区养老、共享养老,在妈妈生活的大院里,已经实现了一部分。
而七堇年也在构建自己的节奏:早上6点起床,高效地处理工作,写作;下午则看书,运动,偶尔也会骑着共享单车在周边绿道转转,感受风。等大段的工作完毕,她进山,徒步或攀岩,手机离开服务区,离开城市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