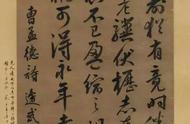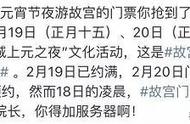《齐物论》是庄子哲学思想的代表作。这篇文章的宗旨在于论述万物齐一和是非相对,既谈到了从无到有的本体论问题,也涉及到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认识论问题。在本体论问题上,主要倾向是主观唯心主义,但也有某些唯物主义因素;在认识论问题上,主要表现是万物齐一和否定是非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但也有较丰富的辩证法内容。
本篇分三个层次:从“南郭子綦”到“怒者其谁邪?”论述了“吾丧我”的精神境界,指出诸家争鸣都是各持己见的结果,要想停止纷争,就得做到“忘我”。第二部分,从“大知闲闲”到“故寓之无竟”,由十个自然段组成,是作者在本文中论述的中心内容。这一部分中,主要论述了各种主观世界的争论纠结,是迷失自我的表现,是主观成见所致使,要想停止争论,就得用“莫若以明”的认识方法,排除成见,开放心灵,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境界。第三部分,用“罔两问景”和“庄周梦胡蝶”两个故事来说明万物融化为一的“物化”过程,得出“物化”的万物齐一的结论。
南郭子聂靠几静坐,仰面朝天,缓漫吐气,形体木然,仿佛精神脱离了身躯。颜成子游立侍在跟前,问说:“怎么这个样子啊?形体安定本来可以使它象枯*树木,而精神岂能可以使它象熄灭的灰烬呢?你现在靠几而坐的情况,不是你过去靠几而坐的情况了。”子綦回答说:“偃,你问的问题,不也是很好的吗!如今我忘掉了功名利禄的我,你知道这一点吗?你听到过人造的萧声,却没听到过地上自然形成的音响,你听到过地上自然形成的音响,却没听到过天空中自然形成的音响吧!”子游说:“请问三籁的道理?”子綦说:“大地发出的气,它的名子叫风。这风不作则已,一发作则上万种不同的孔穴都会怒吼起来。你没有听过长风呼啸的声音吗?山林高大参差不齐的地方,百围大树上的孔穴,有的象鼻孔,有的象嘴,有的象耳朵眼,有的象春臼,有的象深大的洼地。有的象浅小的池塘;长风吹这些孔穴所发出的声音,有的象湍激的流水声,有的象大火燃烧声,有的象呵叱声,有的象抽气声,有的象叫喊声,有的象号哭声,有的声音深沉,有的声音哀切,前面的风声唱着,后面的风声随应着。微风则相和的声音小,疾风则相和的声音大,烈风停止了,则所有的孔穴就都空寂无声了,你难道没看见风吹林木枝叶还在摇摇曳曳地摆动着吗?”子游说:“地籁的声音不过是从众多的孔穴中发出来的罢了,人籁的声音不过是从用多种竹管并起来所制作的乐器中发出来的罢了。请问天空中自然的音响是怎么回事呢?”子綦说:“风吹万窍而声音不同,然而使它们发作或停止的都是它们自己。都是自然状态所致,发动它们的还能是谁呢!”
大知过于广博,小知过于精细。大言盛气凌人,小言喋喋不休。他们睡时也心神交错烦乱,他们醒时也形体不得安宁。与社会接触构合纠葛,整天勾心斗角。有的显得慢不经心,有的却冥恩苦想,有的则小心谨慎。对小的恐惧提心吊胆,对大的恐惧垂头丧气。他们的心计一发就象箭一样疾速,他们的心计探察不发是为了称是避非;他们停止发言犹如盟誓,为了以守取胜;他们衰败好似秋风冬寒的景象,这是说他们一天天在消弱;他们沉溺在所作所为的活动之中,再无法使他们恢复原状;他们隐藏心灵不言不语,说明他们老而枯竭败坏;接近死亡的心灵,再也不能使它恢复生机。高兴、愤怒、悲哀、欢乐,优虑、叹息、变态、恐惧,轻浮、安逸、放荡、娇淫:象乐声从空虚的乐器中产生出来,又象菌类从地上的蒸气中产生出来一样。交互更替在眼前,而不知道它们是怎样萌发出来的。
算了吧,算了吧!一旦懂得了这些情态发生的道理,也就懂得了它们所以发生的根由了!没有客体的彼,就没有主体的我;没有主体的我,客体的彼也就无法体现。这样主体与客体也就近似统一了,然而不知道它受谁支配。好似有个真我,但是却看不见它的迹象。可以从它的行为中得到信息,却看不到它的形体,它是真实可信的,却没有具体的形象。一百个骨节,九个孔穴,六个内脏,都兼备地存在我的身上,我和那个最亲近呢?你都喜欢它们呢,还是有所偏爱呢?如此不是都把它们当成臣妾了吗?它们是臣妾就不能相互支配吗?还是让他们轮流做君臣呢?难道果然另有真君存在吗?即使求得真君的真实情况与否,对它的本真是无所益损的。人一旦享受而形成形体,就认为躯体是常驻不变的而等待最后的耗尽。
和外物相接触,既有相互矛盾之时,也有切中事理之时,他的心行追逐外物象奔驰一样不能止步,这不是很可悲的吗!一辈子劳劳禄禄而看不见他的成功,精神不振,疲于劳役,而不知道他的归宿,这不是很可悲的吗!这样的人生虽然说他不死,又有什么益处呢?他的形体在不断地变成衰老,他的思想又随着形体的变化而消失,这能不叫作最大的悲哀吗?人生在世,本来就是如此的愚昧吗?难道只是我愚昧无知,而别人也有不愚昧无知的吗?若依据自己的成见作为是非标准,那么谁没有一个标准呢?何必了解事物发展变化而有心地的人才有呢?愚昧的人也是有的。如果说没有形成主观成见,便有了是非观念,这就象惠施的“今天到越而昨天就到了”的观点一样。这是把无有看成有。把无有看成为有,就是神明的大禹尚且不能理解,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言论不是吹风,发表言论的人都有所说的内容,但他们的言论又都自以为得当而不能有定论。他们果真有这些言论呢?还是没有过这些言论呢?他们自以为自己的言论不同于刚出蛋壳的小鸟叫声,到底是有分别呢,还是没有分别呢?道是怎么被隐蔽而有真伪的呢?言论是怎样被隐蔽而有是非的呢?道是无真伪的在什么地方不存在呢?言论是无是非的在哪些方面有不可的呢?道的本质隐蔽在片面认识的后面,言论的性质隐蔽在花言巧语之中,因向才有儒墨显学的是非之争,他们都各自肯定对方之所非,而非议对方之所是,如要肯定对方的所非而非议对方的所是,则不如以空明的心境去反映事物的实情。宇宙间的事物没有不是彼的,也没有不是此的,从彼方看不见此方,从此方来看就知道了。所以说,波方是出于此方,此方也依存于彼方。彼此是相互并存的。虽然如此,生中有死的因素而向死转化,死中有生的因素而向生转化,肯定中有否定因素而向否定转化,否定中有肯定因素而向肯定转化;由是而得非,由非而得是,因此,圣人不经由是非之途而只是如实地反映自然,也就是因任自然这条道理。此也是彼,彼也是此。彼有一个是非,此也有一个是非,果真有彼此之分吗,果真无彼此之分吗?彼此都没有它的对立面,这就是物通为一的规律。符合道的规律才能得到它的运转的圆机,以顺应无有穷尽的发展变化。是的发展变化是无穷尽的,非的发展变化也是无穷尽的。所以说不如以空明的心境去反映事物的实情。
用指的概念来说明具体的指不是指,不如用不是指的概念来说明一般的指不是具体的指。用马的概念来说明具体的马不是马,不如用不是马的概念来说明一般的马不是具体的马。其实天地之大就是一指,万物千差万别不过就是一马。肯定自有肯定的道理,否定自有否定的道理。道路是人走出来的,事物的名称是人叫出来的,怎样才算对的?对的就是对的;怎样算是不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怎样算是肯定?肯定就是肯定;怎样算是否定?否定就是否定。万物各有其存在的依据,万物各有其合理性,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对的,没有什么事务是不可肯定的。所以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可举草茎和大柱子小大相同,丑厉和西施丑美一样,千奇百怪一切情态,从道的观点来看,都是齐一无别的。万物总体的分就是众体的成,新事物的成又是旧事物的毁。一切事物没有成与毁的分别,还是把它们看成是齐一的。只有这样,通达的人才会通晓万物齐一的道理。因此,不用成毁的观点看问题,而托付于循环往复的观点看问题,按循环往复的变化行事,就是无用之用,就无所不通,无所不通,就无所不得。达到满意而有所得也就差不多了。听任自然吧,把万物看成齐一而不去了解它的所以然,这就叫做道,耗费自己的聪明才智才了解万物齐一,和了解万物的本来面貌就是一样的,这两者没有什么差别,可以把它叫做“朝三”。什么叫“朝三”呢?养猕猴的老人在分给猕猴橡子时说:“早晨三升而晚上四升。”所有的猴子都非常愤怒。老人又说:“那么就早晨四升而晚上三升吧。”所有的猴子都非常喜悦。其实名义和实际都没有什么亏损,然而却使猴子喜怒不同,这就是顺应猴子的心理作用罢了。所以,圣人调和是非而不去争论,这就是“因是”、“以明”两个轮子缺一不能行走的道理。
古时候的人,他们的认识有最高境界。什么是最高境界?他们认为宇宙未曾形成万物的始初时刻,认识是最高的,尽美尽善的,再不能增加什么认识了。其次,则认为宇宙开始有了万物时,万物之间是没有分别界限的。再次,认为有了分别的界限,但未曾有是非之别。是非观念明显了,道的观念也就因此而亏损了。道的观念之所以亏损,是因偏私观念的形成。果真有所谓成就和亏损呢?果真还是没有成就和亏损呢?有成就和亏损,犹如昭文的弹琴;没有成功和亏损,犹如昭文不弹琴。昭文弹琴,师旷指挥,惠施依靠梧桐树的辩论,这三位先生的认识和才智接近最高峰了,所以载誉于晚年。正因为他们各有所好,而炫异于别人,他们各以所好去让别人领悟,用不是别人所非了解不可的东西而硬让别人去了解,因此以坚白论的糊涂观念而终身。然而昭文的儿子继续昭文的事业,而终生无所成就。如果说这就是所谓成就,那么象我这样的也算有成就了。如果说这不可以称为成就,那么天下的事物和我都不能算是有成就。所以,那些迷乱世人的眩耀的言论,圣人是一定摒弃的。所以圣人不用这种言论,而是把认识寄寓于各物自身的功分上,这就叫做心地如镜地反映事物。
现在姑且在这里发表些议论,不知道这些议论与其他人的议论是同类呢,还是不同类呢?同类也好,不同类也好,既然都是议论,那也就是同类了。那也就与其他人的议论没有什么差别了。既或如此,还是请你允许我说清楚。宇宙有它的开始,有它的未曾开始的开始,更有它的未曾开始的未曾开始的开始。宇宙有它的有,有它的无,更有它的未曾有无的无,更有它的未曾有无未曾有无的无。倾刻间产生了有和无,然而却不知道这个有无果真是有,果真是无。现在我发表了这些议论,然而却不知道果真说了这些话呢,还是果真没说过这些话呢?天下没有比兔毛尖端更大的东西,而泰山是小的;没有比未成年死去的人更长寿的,而活八百岁的彭祖却是短命的早亡者。天地万物都和我们同生于无,都与我同为一体。既然已经说过合为一体了,还能再说什么呢?既然已经说了与万物一体了,又怎能说没有说什么呢?万物一体的存在加上我所说的言论就成为二,二再加上一就成三,从此往下推算,最高明的数学家也不能得出最后的答案,何况一般的人呢?所以从无到有,以至于推出三来,何况从有到有的推演呢?不要再住下推演了,还是因任自然算了。
大道从来是没有界限的,言论从来是没有定准的,因为有了从无到有,才有了差别的界限,请允许我谈一谈它的区别界限,有左,有右,有伦序,有合宜,有分粗,有辨细,有竞弱,有争强,这是界限的八种表现。宇宙以外的事情,圣人只观察而不考核其类属;宇宙以内的事情,圣人只是论说而下加以评议。《春秋》是记载治理社会的编年史,是先王治事的记录。圣人只评议而不争辩。所以说,有有分别的,就有不分别的;有可以争辩的,就有不可以争辩的。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人把“存而不论”、“论而不议”、“议而不争”的观点藏在心中不让别人知道,百家争鸣的众人却争辩不休而相互夸耀以自胜。所以说这样的辩者只能是各执一词,只见己之是,不见已之非的片面性。大道是用不着声扬的,善辩的人是不用言说的,最仁的人是不能偏爱的,最廉洁的人是不去表示谦逊的,最勇敢的人是不伤害人的。道如显示彰明就不是道,言如争辩就有所达不到的,仁有常爱而不周,廉到极清白就不信实,勇到害人逆物就不会取得成功。这五者虽有残缺而接近道的一隅了。所以,明智的人止于他所不知的境地,就是极点了。谁能知道不用语言的辩论,不用声扬的道呢?如果有谁能知道这一点,这就称得上是大自然的仓库了。这种府库,注入多少东西都不会盈满,取出多少东西也不会枯谒,而且不知道它的源流来自何处,这就叫做隐藏起来的光明。
过去帝尧问帝舜说,“我想讨伐宗脍、胥、敖,每当临朝,总是感到心情不安,这是为什么呢?”帝舜说:“这三个小国的国君,犹如生存在蓬蒿艾草中间,你心情不安,这是为什么呢?过去十个太阳一起出来,万物都在阳光下照耀,何况你的德行胜过太阳的光芒呢!”
啮缺问王倪说:“你知道万物有所共同肯定的道理吗?”王倪回答说:“我怎么知道这些呢!”啮缺又问说:“你知道你所不知道的东西吗?”王倪说:“我怎么知道呢!”啮缺再问说:“那么万物就没法知道了吗?”王倪说:“我怎么知道这些呢!虽然如此,还是让我试试谈一谈这个问题。怎么知道我所说的知不是不知道呢?怎么知道我所说的不知并不是知呢?现在姑且让我问你:人在潮湿的地方睡觉就会腰痛而偏瘫,泥鳅是这样吗?人在树上居住就惊恐不安而发抖,猿猴也是这样吗?这三种动物究竟谁最了解真正舒适的处所呢?人吃牛羊猪狗,麋鹿吃蒿草,蟋蟀吃蚁子,鹞鹰和乌鸦爱吃老鼠,这四种动物究竟谁知道真正好吃的美味呢?母猿猴与狗头猿相配为雌雄,麋鹿和鹿相交媾,泥鳅和鱼相追尾。毛嫱、丽姬是世人认为最美的人,然而鱼见到她们就潜入水底,鸟见到她们就飞向高空,麋鹿见到她们就疾速奔跑,这四种动物究竟是谁知道天下真正的美色呢?依我看来,仁与义的端倪,是和非的途径,杂乱无章,我怎么能知道它们之间的区别呢!”啮缺说:“你不知道利害关系,难道至人也不知道利害关系吗?”王倪说:“至人太神妙了!山泽燃烧而不能使他感到热,江河封冻而不能使他感到冷,疾雷辟山、暴风震海而不能使他感到惊恐。象这样的至人,乘着云气,骑着日月,而邀游于四海之外,死生都不能使他自己发生变化,何况利害这样的小事呢!”
瞿鹊子问长梧子说:“我听孔夫子说过:‘圣人不去从事世欲的事情,不贪图利益,不回避危害,不喜欢追求世欲,不拘缘于道欲;没有说话就等于说话了,说了话就等没有说话,而邀游于世俗之外。’孔夫子认为这些都是轻率的言论,而我认为这些正是可以身体力行的妙道。你以为怎样?”长梧子说:“这些话黄帝听了也会感到疑惑不解,而孔丘怎么会了解呢?而且你也太求之过急了,见到鸡蛋便想得到报晓的雄鸡,见到弹丸就想吃到烤鹏鸟肉。我尝试给你随便说说,他也就随便听听吧。何不依傍着日月,挟持着宇宙,与日月宇宙万物合为一体,任凭是非杂乱不齐,把奴仆同样看作是尊贵的人。那些世俗的人们劳苦不休地追求知识,圣人则表现为愚昧无知的样子,浑同历代变异而不为是非所乱。万物都是如此,而互相蕴含于齐一之中。我怎么知道对活着高兴而不迷惑呢?我怎么知道对死亡感到厌恶而不象少年流浪在外不知回家的人呢?丽戎国有个美女,是戎国在艾地戍守边界人的女儿。
当晋国开始得到她的时候,哭得泪水湿透了衣襟;等她到了晋献公的王宫里,和国王睡在一张方正而安适的床上,同吃美味的牛羊猪狗肉时,才后悔当初不该哭泣。我怎能知道死了不后悔当初不该贪生呢?梦中开怀畅饮,醒了之后却要痛哭流涕;梦中痛哭流涕,醒了又去狩猎取乐。当他正在梦中,不知他是在做梦,睡梦中还占卜问他梦中之梦的吉凶,醒了之后才知道是在做梦。只有特别清醒的人才知道人生是一场大梦,而愚昧无知的人,自以为狼清醒,表现出明察一切的样子,觉得他什么都知道。什么君主啊,什么臣子啊,太浅陋了!我看孔丘和你都在做梦,我说你们在做梦,我也在做梦。这些言论可以把它称为怪异的言论,也许万世之后会遇到一位大圣人能了解这个道理,那也是旦暮相遇的偶然现象。即使我与你进行辩论,你胜了我,我没有胜你,你肯定对,我肯定错吗?我胜了你,你没有胜我,我肯定对,你肯定错吗?是我们两个人有一方是对的,有一方是错的呢?还是我们双方都对,或者都错呢?我与你都不知道,别人本来就受到它的蒙蔽而暗淡不明。
我们请谁来评判是非呢?假使请观点和你的观点相同的人来评判,他既然和你的观点相同了,又怎样评判呢?假使请观点和我的观点相同的人来评判,他既然和我的观点相同了,又怎么能评判呢?假使请观点和你我观点都不同的人来怦判,他既然与我和你的观点都不同,又怎么能评判呢?假使请观点和你我都相同的人来评判,他既然与我和你的观点都相同,又怎么能怦判呢?那么,我和你和其他别人都不评定谁是谁非了,还等待谁来评判呢?”“什么叫做混同于自然来调和一切是非呢?”就是说:“有是就有不是,有对就有不对。是的如果真的是是的,那么,是的不同于不是的也就不须分辨了:那些辩论的言词化作声音而相互对立,因为不能相互评判,所以就象没有对立一样,混同于自然之分,顺应着无穷的变化,从而享尽一生。对的果真是对的,那么,对的不同于不对的也就不须分辨了。忘掉生死岁月,忘掉是非仁义,就能畅游于无穷的境界,这样也就把自己寄托在不能穷尽的境域了。”
影子的影子问影子说:“过去你行走,现在你又停下;过去你坐着,现在你又站起来;为什么你不能独立的操持呢?”影子回答说:“我是有依赖条件才这佯的呀!我所依赖的东西又有所依赖才这样的呀!我依赖蛇腹下的鳞皮和蝉的翅膀才这样的吗?我怎能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怎能知道为什么不会是这样的!”
过去庄周梦见自己变为蝴蝶,栩栩如生飞舞自得的蝴蝶,自己为适合心意而感到愉快。竟然忘掉自己是庄周了。倾刻间觉醒了,就惊喜的意识到自己仍然是庄周。不知道是庄周在梦中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在梦中变为庄周呢?庄周和蝴蝶毕竟是有区别的。这种物我的变化就叫做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