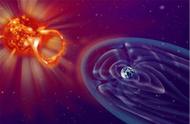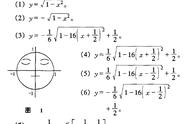关于论语的书名来历,《汉书》中记载为“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
按班固这个说法,论语的论即为论撰之意。又将孔夫子的死轻飘飘的记为“卒”,显然,汉武帝年间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夫子的地位仍然很是边缘化,至少在班固眼中看来,孔子是没有资格入“世家”行列的。
这个解释不久就开始被质疑,东汉刘熙认为论为伦理,意思是“有条理的叙述”。
这个说法太过牵强,莫非夫子有教无类的时候,那些贤弟子们都是一脸懵圈吗?夫子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话,哪里会有三千弟子?
宋人邢呙认为论是个多义词,大概有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等意思。经纶世务则曰纶,圆转无穷故曰轮,蕴含万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集定,故曰撰也。
北宋年间,孔夫子的地位已经变得极为尊崇,邢呙的解释包罗万象,明显太过尊经崇圣了。

宋人陈祥道则认为论为“言理”,面对众多弟子的质疑与诘难,夫子被迫无奈据理力争。辩论的结果自然是夫子胜出,孔夫子每天闲极无聊,就是和一帮学生抬杠逗闷子玩,想想这场景也是醉了。如果老先生穿越到千年后,一定也会象亚圣一样脸红脖子粗的为自己辩解一番:“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解释,“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学者至今则之。”
这样看来,“论”,真的只是编纂的意思,并没有什么神圣特殊的含义。
其实,按“以经解经”的方法来操作的话,《论语》的“论”到底怎么理解,在《论语》中就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只是“述而不作”。还经常在几个得意弟子面前唠叨“吾道一以贯之”这样的话,几个贤弟子听得耳朵里生了茧子,于是在编撰《论语》一书中努力体现夫子思想时,真的将先师定位成了编辑一枚。
而宋代腐儒朱熹,也没有搞明白状况,对夫子的“述而不作”做了如下阐释,“述, 传旧而已。作, 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 而述则贤者可及……孔子删诗、书, 定礼、乐, 赞周易, 修春秋, 皆传先王之旧, 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 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
朱熹认为,在孔子之前,圣人已经将大道理全讲得明明白白了,夫子做的就是个解释与传承。甚至在他眼中看来,孔夫子非但不圣,居然还“不贤”了。
大概是照顾孔圣人后人家的颜面,台湾学者南怀瑾老师在其《论语别裁》中对夫子的“述而不作”解释还算中肯,
南怀瑾老师认为, 研究孔子思想, 首先要知道孔子自己很谦虚, 孔夫子说的述而不作,其实就是承先启后, 继往开来。然而他也认为,夫子做的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只是对传统文化的整理,并没有加以创作。
南老师认为,夫子是编辑,而且是个资深编辑。

司马迁《史记》云,“夫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现代人眼中看来,《春秋》,孔子只能是编著者,而不是作者。
孔夫子对传统文化做的一切努力真的只是“述”,而不是一种再创作吗?
个人以为,这是对孔夫子的一种误解。
与孔夫子大约同一时代,东西方先后出现了几位牛皮哄哄的人物——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
无一例外,他们做的都是传承与弘扬, 自己从不发挥。那些经典并非由他们自己创作,而是完全由门人弟子记载他们的一言一行 , 且体例都是问答式的对话体或者干脆就是记录日常的小段子。如佛家经典中的“如是我闻”,如记载耶稣神迹的《福音》……在现代人眼中看来,他们就是远古文化的集大成者,没有人怀疑他们不是文化的原创者。
还有道家经典《道德经》,明明是函谷关令尹喜笔录记载下来的,没有人知道里面加了私货没有,为何没有一人站出来质疑是老子“述”,而非“作”,怎么轮到孔夫子,就要区别对待了呢?
孔夫子遭遇的这种不公,还得从历史上寻找原因。
孔夫子所处的时代,按夫子自己话来讲就是“礼崩乐坏”。礼崩乐坏不说,各种从前藏于王室,由巫、祝、史、卜等专人保管、秘不示人的诗书也散落民间。孔子感叹“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官失而师儒传之”,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孔子决定开设私立学校,因材施教。
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仁”与“礼”二字, 仁是关键,礼为形式。然而在孔夫子所处的时代太过悲催,按规定,“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
孔夫子做的事情,严格讲来是“越主代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的话,孔夫子曾经亲自曰过,如果自己坚持反其道而行之,岂不是自打耳光?这让每天将“礼”挂在嘴边的夫子如何面对三千弟子?让先生情何以堪?
可以立言者都是天子,而非圣人。天子未必是圣人, 但有立言权, 圣人不是天子, 自然也就没有立言权。
“作”不得,退而求其次“述”,看来孔夫子还擅长打擦边球,绝不是什么不知变通,迂不可及的冬烘先生。
在什么山唱什么山歌,只可惜七十二贤弟子没有换位思考。

众所周知,《史记》作者是司马迁,然而司马迁也公开宣称,《史记》一书,他与夫子一样,属于“述”而不“作”。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史记》)。
敢说“作”,司马迁就是在“作死”,在没了小头后,大头也将不保。
其实,孔夫子从来没有将自己视为圣人,他也曾公开表态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
是后人一厢情愿将孔子捧上圣坛,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