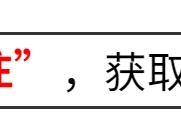又到清明。“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而列夫·托尔斯泰,在童年时代便经历了母亲和奶娘的离世。他把这一情节写进了自传体小说第一部《童年》中,非常真实地描写了自己两度面对死生别离时的心境。
《童年》的最后一节是献给奶娘娜塔利娅·萨维什娜的。这个忠实的女仆出现在小列夫童年记忆的开端,也成为他童年记忆的结束。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处女作中,记下了奶娘的“纯洁、无私的家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张炜非常推崇俄罗斯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因为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温度”,一种“人性的温暖”。张炜说:“没有温度,缺乏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沟通所需要的脉动,结果一切都是扯淡。”
清明时节,我们就阅读一下,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对于至亲的追思与怀念,感受那份浓郁的“人性的温暖”……

托尔斯泰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
托尔斯泰:童年
(节选)
乡间什么在等待着我们
四月十八日,我们在彼得罗夫斯科耶住宅门口下了马车。离开莫斯科时,爸爸心事重重,沃洛佳问他是不是maman(法语:妈妈)病了,爸爸悲伤地望望他,默默地点点头。旅途中他显然平静了些;但是我们离家越近,他的脸色就越来越悲哀,下马车时,他问喘息着跑来的福卡说:“娜塔利娅·萨维什娜(托尔斯泰家的管家,托尔斯泰受其影响颇深)在哪儿?”他的声音颤巍巍的,眼中含着泪水。善良的老福卡偷偷地看了我们一眼,低下头,打开前门,把脸扭到一边,回答说:
“她已经是第六天没有离开卧室了。”
……
这一切使我那由于可怕的预兆而不胜悲哀的、天真的想象感到多么悲痛!
我们走进使女的房间;在过道里我们遇见了傻子阿基姆,他一向好做鬼脸逗我们发笑;但是这时我不仅不觉得他滑稽,而且一见他那冷淡而愚蠢的面孔,我就觉得痛苦得了不得。在使女的房间里,两个正在干活的使女欠起身来向我们行礼,她们那副愁容使我害怕极了。又穿过米米的房间,爸爸打开卧室的门,于是我们都走了进去。门的右首是两扇窗户,窗户被窗帘遮住;一扇窗前坐着娜塔利娅·萨维什娜,她鼻梁上架着眼镜在织袜子。她没有照平时那样吻我们,只是欠起身来,透过眼镜望望我们,就泪如泉涌了。大家本来都十分平静,一看见我们都哭起来,这使我很不喜欢。
门的左边摆着一架屏风,屏风后面是床、一张小桌、一个小药箱和一张大安乐椅,医生正坐在上面打瞌睡。床边站着一个年轻的非常美丽的金发姑娘,她穿着雪白的晨装,袖子卷起一点,正往我当时看不见的maman的头上敷冰。这个姑娘就是妈妈信上说的那个la belle Flamande,后来她在我们全家的生活中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我们一进来,她就把一只手从 maman头上抽回,整理她胸部的衣褶,随后低声说:“昏迷了。”
我当时痛苦万分,但是不由地注意到一切细节。房间里几乎是昏暗的,很热,充满混杂着薄荷、香水、苦菊和霍夫曼药水的气味。这种气味给了我那么深刻的印象,不仅一闻到它,甚至一想到它,我就立刻回想起那间阴森森的、使人窒息的屋子,那可怕时刻的一切细节都立刻再现出来。
maman的眼睛睁着,但是她什么也看不见……噢,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可怕的目光!目光里流露出多么苦痛的神情!……
我们被领走了。
后来我向娜塔利娅·萨维什娜问起妈妈临终的情况,她对我这样讲:
“把你们领走之后,她又折腾了好久,我的亲爱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哽在她这儿;随后她的头从枕头上滑下来,她就像天使一样,平静而安宁地睡着了。我刚走出去看看,为什么没有把她的药水送来,再回来时,她,我的心肝,已经把身边的一切推开,不住地招呼你爸爸到她身边去;你爸爸俯在她身上,但是她分明已经没有力气说出她想说的话:她一开口就又*起来:‘我的上帝!主啊!孩子们!孩子们!’我想跑去找你们,但是伊万·瓦西里奇拦住我说:‘那会使她更加心烦意乱,最好不必。’后来,她刚举起手来,就又放了下去。她这是想表示什么意思,那只有天知道了。我想,她是在暗暗给你们祝福;显然,上帝不让她在临终前看看自己的孩子们。最后,她稍稍抬起身来,我的亲爱的,双手这么动了一下,突然用那么一种我想都不敢想的声调说:‘圣母呀,不要抛弃他们!……’这时她心痛起来;从她的眼神可以看出,这个可怜的人儿痛苦极了。她倒在枕头上,用牙咬住床单;而她的眼泪,我的少爷,就不住地往下滚。”
“嗯,以后呢?”我问。
娜塔利娅·萨维什娜再也说不下去了。她转过身去,痛哭起来。
maman在万分痛苦中逝世了。
悲痛
第二天深夜,我很想再看她一眼。我克制住不由自主的惧怕心情,轻轻地开了门,踮着脚走进大厅。
棺材停在房间当中的一张桌子上,周围是插在高大的银烛台里的残烛;教堂的诵经员坐在房间远远的角落里,用柔和而单调的声音朗诵圣诗。
我停在门口开始张望;但是,我的眼睛哭得那么厉害,神经受了极大的刺激,以至什么都分辨不出;烛光、锦缎、天鹅绒、高烛台、粉红色镶花边的枕头、花环、缀着缎带的帽子,还有一样透明的苍白如蜡的东西,这一切都怪异地融成一片。我站到椅子上想看看她的脸;但是在那里我又看见那浅黄色的、透明的东西。我不能相信这就是她的脸。我更加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它渐渐认出了她那可爱的、熟悉的面貌。当我肯定这就是她的时候,我恐怖得颤抖了;但是,为什么那双闭着的眼睛是那么深陷?为什么这么苍白可怕,一边脸颊的透明皮肤下还有了黑斑呢?她整个的面部表情为什么那么严肃、那么冷冰冰的?为什么嘴唇那么苍白,嘴形那么美好、那么肃穆,露出那么一种非人间所有的宁静,使我凝视着它就毛骨悚然呢?……
我凝视着,感到有一股不可思议的、不可克服的力量把我的目光吸引到那张毫无生气的脸上。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它,但是我的想象却描绘出一幅幅洋溢着生命和幸福的图景。我忘记躺在我面前的这具死尸,忘记我像凝视与我的回忆毫无关系的东西一样凝视着的这具尸体,就是她。我一会儿想象她已经死去,一会儿又想象她还活着,活跃、高兴、含着微笑;随后,我所凝视着的那张苍白面庞上的某种特征突然使我大吃一惊;我想起可怕的现实境界,战栗起来,但是仍旧望着。幻想又代替了现实,现实的意识又破坏了幻想。终于想象疲倦了,它不再欺骗我。现实的意识也消失了,我完全失神了。我不知道我在这种状态下滞留了多久,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境况;我只知道,我一时间失去了自我存在的意识,体验到一种崇高的、难以形容的悲喜交集的快感。
可能在她向极乐世界飞升时,她的善良的灵魂会悲哀地望望她把我们撇下的这个世界;她看到我的悲哀,怜悯起来,于是含着圣洁的怜悯的微笑,爱怜横溢地降到尘世,来安慰我,祝福我。
门吱呀一响,另一个来换班的诵经员走进大厅。这个声音惊醒了我,涌上心头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没有哭,而且以一种根本不会令人感动的姿态站在椅子上,那个诵经员可能认为我是个冷酷无情的孩子,由于怜悯或者好奇才爬上椅子;于是,我画了个十字,行了个礼,就哭起来。
现在回忆我当时的印象,觉得只有那种一刹那间的忘我状态才是真正的悲哀。丧礼前后我不住地哭,十分悲伤,但是我羞于回忆这种悲伤的心情,因为其中总是混杂着一种爱面子的感情:有时是希望显示我比任何人都哀痛,有时考虑我对别人发生的作用,有时是一种无目的的好奇心,使我观察起米米的帽子或者在场人们的脸。我轻视自己,因为我没有体验到一种纯粹是悲哀的心情,于是就极力隐瞒着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因此,我的悲哀是不真诚、不自然的。况且,一想到我自己是不幸的,就感到一阵愉快,极力要唤起不幸的意识,这种自私的情感,比其他的一切更强烈地压制了我心中真正的悲哀。
在极度悲哀之后往往如此,我平静地酣睡了这一夜。当我醒来时,我的眼眶里干涸无泪,神经也十分平静。十点钟叫我们去参加出殡前的祭祷。房间里挤满了家仆和农奴,他们都眼泪汪汪地来向女主人告别。在丧仪中,我大哭了一场,画了十字,深深地行了礼,但心里并不曾祈祷,而且相当冷淡;我只关心他们给我穿的新的小燕尾服腋下很紧,我在盘算跪下时怎样不要把裤子弄得太脏,并且偷偷地打量所有参加仪式的人……所有参加丧礼的外人,我都觉得难以忍受。他们对我父亲所说的安慰话,如“她在天上更美满”“她不是为尘世而生的”等等,都引起我的一种恼怒的心情。
他们有什么权利谈论她和哭她呢?他们有的人提到我们时,管我们叫孤儿。好像他们不提,我们自己就不懂得没有母亲的孩子被人家这样称呼似的!他们好像很喜欢带头这样称呼我们,就像人们通常急着抢先称呼新娘子为madame(法语:夫人)一样。
在大厅远远的角落里,跪着一个屈身弓背、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几乎是躲在餐室敞着的门后。她合着手,举目望天,她没有哭,只是在祈祷。她的心灵飞到上帝身边,请求上帝把她和她在世界上最爱的那个人结合在一起,她确信这一点不久就会实现。
“这才是真正爱她的人!”我心里想,开始问心有愧起来。
追悼会结束了;死者的脸没有盖上,所有参加仪式的人,除了我们,都挨次到棺材前去吻她。
最后的悲痛回忆
maman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是照老样子过下去;我们按照一定的钟点就寝和起床,还住在那些房间里;早点、晚茶、午饭、晚饭,都照往常的时间开;桌椅都摆在原来的地方,家里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没有丝毫变化;只是她不在了……
我觉得,经过这样的不幸,一切都应该有所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是对她的悼念的一种侮辱,它清清楚楚地提醒我她不在了。
出殡的前一天,吃过午饭,我困了,于是到娜塔利娅·萨维什娜的房间里去,打算躺在她那柔软的羽毛床垫上,钻进暖和的绗过的被子。我进去时,娜塔利娅·萨维什娜躺在床上,大概是睡着了;听见我的脚步声,她微微欠起身来,掀开她盖在头上防苍蝇的羊毛披巾,扶正包发帽,坐到床边。
以前我常到她的房里午睡,所以她猜到我的来意,她一面从床边站起来,一面说:
“怎么样,我的宝贝,你大概是来休息的吧?躺下吧!”
“您怎么啦,娜塔利娅·萨维什娜?”我说,拉住她的胳膊,“我根本不是为这个来的……我是来……您自己也很累呀,快躺下吧。”
“不,少爷,我已经睡够了,”她对我说(我知道,她三昼夜没有睡了),“况且,现在也睡不着。”她长叹了一声补充说。
我想跟娜塔利娅·萨维什娜谈谈我们的不幸:我知道她那份真诚和爱,因此同她抱头大哭一场对我会是一种安慰。
“娜塔利娅·萨维什娜,”我说,沉默了一会儿,坐在她的床上,“您料到这事了吗?”
老妇人带着莫名其妙和好奇的神色望了望我,大概不明白我为什么问她这个。
“谁会料到这事呢?”我重复了一句。
“噢,我的少爷,”她说着,投给我一个最温柔的同情的目光,“不但没有料到,就是现在我也不能设想啊!像我这样的老太婆,老早就该让我这把老骨头歇歇了;我何必还活着呢?我的老主人,——你的外祖父,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公爵、他的两个兄弟、他的妹妹安娜,全都逝世了,他们都比我年轻,我的少爷,现在,显然因为我罪孽深重,她也比我先去了。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把她带走,是因为她配得上,上帝那里也需要好人呀。”
这种纯朴的想法给了我很大的慰藉,我更移近娜塔利娅·萨维什娜一些。她把手交叉在胸前,向上望了一眼;她那深陷的潮润的眼睛里流露出深沉而平静的悲哀。她坚信上帝不会使她同她全心全意地爱了多年的人分离多久了。
……
福卡走进屋来;他看见我们这种情景,大概不愿意惊动我们,就停在门口,默默地,怯生生地张望着。
“你有什么事,福卡?”娜塔利娅·萨维什娜问道,用手帕揩着眼泪。
“要一磅半葡萄干,四磅糖,三磅黍米,做八宝供饭。”
“就来,就来,亲爱的。”娜塔利娅·萨维什娜说着,连忙吸了一撮鼻烟,快步走到箱子那边。当她在尽自己认为是十分重要的职责时,由我们的谈话所引起的悲哀连最后一点点痕迹都没有了。
“为什么要四磅?”她唠叨说,拿出糖在天平上称一称,“三磅半就够了。”
于是她从天平上取下几小块。
“昨天我刚给了他们八磅黍米,现在又来要,真不像话!随你的便,福卡·杰米德奇,但是这个万卡就高兴家里现在乱糟糟的,我再也不给黍米了:也许他想这样就可以浑水摸鱼了。不,凡是主人的财产,我都不会马马虎虎。谁见过这样的事啊?要八磅!”
“怎么办呢?他说都用完了。”
“哦,好吧,在这儿,拿去!给他吧!”
她从同我谈话时那样令人感动的样子转变到埋怨唠叨和斤斤计较,当时使我大为吃惊。以后我考虑这一点时,才理解到,不管她心里多么难受,她还有足够的精力去料理自己的事务,习惯的力量使她去完成日常的工作。悲哀对她产生那么强烈的影响,使她不觉得有必要来掩饰她能从事其他事情的事实;她甚至不会理解,怎么有人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虚荣心同真正的悲哀是完全矛盾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在人类天性中是那么根深蒂固,连最沉痛的悲哀都难得把它排除掉。在悲哀的时刻,虚荣心表现为希望显得伤心、不幸,或者坚强;我们并不承认这种卑鄙的愿望,但是它们从来,甚至在最沉痛的悲哀中,也不离开我们,它削弱了悲哀的力量、美德和真诚。但是娜塔利娅·萨维什娜遭到的不幸使她悲痛万分,所以她的心灵中没有剩下半点私心杂念,她只是照习惯行事。
给了福卡所要的粮食,又提醒他要做馅饼来款待神父以后,她就把他打发走,自己拿起编织的袜子,又在我旁边坐下来。
我们又谈起那些事情来,又哭了一阵,又擦眼抹泪。
我同娜塔利娅·萨维什娜的谈话每天都要重复;她那沉静的眼泪和温和而虔诚的言语,使我得到安慰,使我轻松。
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离别了。丧礼后三天,我们全家搬到莫斯科,我注定再也见不到她了。
……
随着妈妈的逝世,我的幸福的童年也就结束了,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少年时期;但是由于我对娜塔利娅·萨维什娜——我再也见不到她,她对我的个性和感情的发展和方向有过那么强有力的好影响——的回忆是属于第一个时期的,关于她和她的逝世我想再说几句。
我们离开以后,后来听留在乡下的人们对我讲,她因为没有事干,感到十分寂寞。虽然所有的箱子还由她掌管,她不断地翻箱倒柜,清理,晾晒,放好;但是她觉得缺少了她从小就习惯的、老爷们的乡间宅邸里的那种喧哗和忙乱。悲伤,生活方式的改变,没有事干,不久就发展成一种在她身上早有苗头的老年病。我母亲死后整整一年,她就得了水肿病,卧床不起了。
我想,娜塔利娅·萨维什娜孤零零地、举目无亲地生活在彼得罗夫斯科耶那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固然很难过,而在那里死去就会更加难过了。家里的人都很敬爱娜塔利娅·萨维什娜,但是她同任何人都没有交情,而且以此自豪。她认为,以她这种管家的地位,享有主人的信任,掌管着那么多装满各种各样物品的箱子,如果同任何人有交情,一定会使她徇私,迁就姑息,为了这个缘故,或者因为她同其他的仆人们毫无共同之处,她避开所有的人,总说她在家里跟谁都不沾亲带故,为了主人的财物她对谁都是铁面无私。
她用热诚的祈祷向上帝述说自己的感情,从中寻求,并且找到了安慰;但是有时,在我们大家都容易遇到的感情脆弱的时刻,生物的眼泪和同情能令人获得最好的慰藉,她就把她的小哈巴狗(它的黄眼睛盯着她,舐她的手)放到床上,跟它说话,一边爱抚它,一边轻轻地哭泣。当那只哈巴狗可怜地吠叫时,她就极力使它平静下来,说:“够了,不用你叫,我也知道我快死了!”
她临死前一个月,从自己的箱子里取出了些白棉布、白纱布和粉红丝带;靠着她的使女的帮助,给自己做了一件白衣服和一顶白帽子,把她丧礼上需要的一切最细小的东西都准备好。她把主人的箱子也都清理好,一丝不苟地照着清单点交给管家的妻子。随后,她拿出以前我外祖母给她的两件绸衣服、一条古色古香的披巾,还有一件我外祖父的绣金军服,也是交给她随意处置的。由于她小心保存,军服上的绣花和金带仍旧是崭新的,呢子也没有被虫蛀。
临死前她表示了这样一个愿望:把这些衣服中的一件,粉红色的那件,给沃洛佳做睡衣或者棉袄;另一件,棕色方格的,给我派作同样用场;披巾给柳博奇卡。我们中间谁先做了军官,她就把那件军服遗赠给哪个。她的其余的东西和金钱,除了四十卢布留作她的丧礼和超度灵魂之用外,她都给了自己的弟弟。她弟弟是个早就被解放了的农奴,住在一个遥远的省份里,生活十分放荡,因此她活着的时候同他一直没有任何来往。
当娜塔利娅·萨维什娜的弟弟来接受遗产时,结果死者的全部财产只值二十五个卢布票,他不相信这点,而且说,一个老太婆在有钱人家待了六十年,而且掌管着一切,省吃俭用了一辈子,连破布烂片都爱惜,居然什么也没有留下,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娜塔利娅·萨维什娜被病魔缠磨了两个月,她以真正基督徒的忍耐精神忍受着痛苦,既不抱怨,也不诉苦,仅仅按照她的习惯,不住地呼唤上帝。在临死前一个钟头,她怀着平静的喜悦心情做了忏悔,领了圣餐,举行了临终涂油礼。
她请求家里所有的人饶恕她可能使他们受到的委屈,请求接受她忏悔的瓦西里神父转告我们大家,说她不知道如何感激我们的恩典,并且说,如果由于她愚昧无知得罪了什么人的话,请求我们饶恕她。“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贼,我敢说,我从来没有偷过我主人一针一线!”这是她最重视的自己身上的美德。
她穿戴上她准备好的衣服和帽子,把胳膊肘支在枕头上,同神父一直谈到最后,当她想到她没有给穷人留下什么的时候,她掏出十个卢布,请求神父在教区分给他们;随后她画了个十字,躺下来,最后又长叹了一声,带着愉快的笑容,呼唤了一声上帝。
她毫无悔恨地离开了人间,她不怕死,把死当作一种天惠。人们常常这么说,但是实际上这么想的却是多么少啊!娜塔利娅·萨维什娜能够不怕死,是因为她是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完成了福音书上的训诫死去的。她一生都怀着纯洁、无私的爱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如果她的信念能够更高尚,她的生命能够献给更远大的目标,结果会怎样呢?难道这个纯洁的灵魂就因此受到较少的敬爱和赞美吗?
她在这一生完成了最美好、最伟大的事业,毫无悔恨、毫无畏惧地死去了。
遵照她的遗愿,她被埋葬在离我母亲坟墓前的小礼拜堂不远的地方。她长眠在一个长满荨麻和荆棘的小土墩下,四周围着黑色栏杆。当我走出小礼拜堂的时候,我从来不忘记走到栏杆跟前,叩个头。
有时我在小礼拜堂和黑栏杆之间默默地站着。沉痛的回忆突然涌上我的心头。我想:难道上天把我同这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就是为了使我终身为她们惋惜吗?……
*因原文较长,本文稍作删减。
图 书 介 绍

自传体小说系列
《阿霞》《初恋》《春潮》,《童年》《少年》《青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分别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三位文学大师在不同时期的成长经历,以文学形式在读者面前展开,宛如一部部青春修炼手册。

自传体小说系列现已开售
扫上方二维码即为购书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