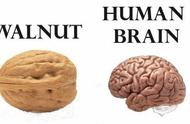William Alexander描绘的中国人吃槟榔的画像
这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一幅描绘中国人吃槟榔的比较写实的画像,是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画师William Alexander画下来的。当时这幅画像是没有写地点的,但是从他的行程来看,最有可能的地方是在澳门。这幅画里有蒌叶,有一个石灰盒子,里边是已经包好的槟榔。这个时候的槟榔就跟台湾看到的包叶槟榔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当时广东是流行这样吃槟榔的。但是大家如果最近去广东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广东人早就已经不这样吃槟榔了,这个习俗对于广东人来讲都是非常陌生的了,因为它已经消失了至少一百年的时间,以至于到民国初年的时候,嚼槟榔的这个问题已经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在其他地方它还会被认为是一种社会问题。
广东人食用槟榔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呢?世界上所有吃槟榔的人,嚼槟榔的习俗的起源都是南岛语系族群。南岛语系族群对于华北或者北方的人来讲可能还是蛮陌生的概念,如果我们了解中国的语言构成通常会说汉藏语系,汉族、彝族这些都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还有一个很典型的语族就是侗台语族,侗族、壮族、傣族都讲侗台语族的语言,是在中南半岛活跃的;还有一个苗瑶语族,有时候也叫它中南语系,这个语系的族群活跃在中南半岛;接下来,中国北方还有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族群是一个很重要的族群,这个族群的起源地,一般来讲学术界广泛地认为是我国的台湾岛。台湾源起以后向整个太平洋群岛和东南亚的岛屿进发,这个族群是遍布在海洋上的,以航海技术作为他们很显著的一个特点。他们还有一些奇怪的民俗,比如中国古籍里面记载的“雕题黑齿”,一般就是指南岛语系族群的后裔。所以,当我们看到中国古籍的时候会发现有个问题,它里面会写到很多对南方民族混淆的称呼,会把瓯越、越裳、骆越都认为是百越,不加以细致的区别,但实际上在中国长江以南的这些原生民族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他们可能是属于不同语系的,比如有些是来自侗台语系的,有些是来自南岛语系的,这些民族都是生活在华南大地上的。随着汉族逐渐地向南拓展,这些民族有一部分融入了汉族,有一部分永远地离开了华南,迁徙到中南半岛上面去了,南岛语系族群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现在在中国大陆已经看不到任何的南岛语系族群了,但是曾经它在大陆沿海有定居地。
南岛语系族群是目前被发现的第一个食用槟榔的族群,最早的遗址是在巴拉望岛上,这个岛上有个都扬洞穴,发现了最早的人类嚼槟榔的痕迹——大概距今五千年前的嚼槟榔的人的牙齿的痕迹,必须是由槟榔和石灰混合以后产生的痕迹。
之后的记录也可以在马来半岛或者菲律宾群岛、越南南部发现这些嚼槟榔的痕迹。但是很遗憾,在华南并没有出土这样的东西。如果按照严格的考古学的判定方法,我们不能印证说嚼槟榔的习俗在汉人到达华南以前就真正存在过,但是文献上能够支持汉人到达华南以后发现槟榔的说法,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得到的证据就是说虽然没有明确的考古学证据,但是我们可以间接地推断出来,华南是存在嚼槟榔的南岛语族的部落的。
嚼槟榔的习俗随着南岛语系族群的扩散,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地方,还影响了它北方的两个邻居,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华。印度受到影响以后,几乎在整个南亚次大陆上都产生了嚼槟榔的习惯,他们把这个作为一个宗教仪式当中的一部分流传下来。所以在印度嚼槟榔是个很普遍的事情,到现在也是。印度人嚼槟榔跟南岛语系族群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印度人嚼槟榔的方法是把槟榔切得非常碎,裹在蒌叶里面,也是会加石灰,但是他们还会加烟草、加糖,会加其他的香料,是非常混合的嚼法。在中国嚼槟榔的习惯,长期以来在岭南是保持着跟南岛语系族群一致的嚼法,就是青叶青裹的状态。
说到中国人对槟榔的记载,第一个记载槟榔的人是杨孚。杨孚本身就是广州人,当然广州这个名称出现既早又晚,它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交州广州这样的说法,但是当时的广州是泛指广东广西的所有地方,现在的广州市是在民国初年重新定义的,所以现在的广州跟以前的广州所指的范围不一样。可以想象一下,当东汉的杨孚详细记录槟榔的时候,你所得到的信息就是杨孚是一个在南越的汉人,他很有可能是汉王朝为了征伐南越而派下的军官的后代——大概是这样一个征服者的地位出现在南越的土地上。他详细地记录了槟榔的食用方法。比他更早的司马相如也记录了槟榔,但是他只有一句话——他在《上林赋》里说“仁频并闾”,仁频就是槟榔,并闾就是棕榈树,所以我们不认为他是实地见过或者能够直接传递信息的。
杨孚是这样记载的:“槟榔,若笋竹生竿,种之精硬,引茎直上,不生枝叶,其状若柱。其颠近上未五六尺间,洪洪肿起,若瘣木焉。因坼裂,出若黍穗,无花而为实,大如桃李”,描述槟榔的样貌。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说“饮啖设为口实”,就是说当时岭南人嚼食的方法,加上解释,把牡蛎灰加入槟榔当中同嚼能让人产生欣快的感觉,俗曰:“槟榔扶留,可以忘忧”。后来《本草纲目》也沿用了这句话。所以,对槟榔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想象就是从这里来的。杨孚特别写成了《异物志》,把岭南的各种物产介绍到中原去,使中原人第一次知道了岭南有如此多的物产,可能会有很重要的药用价值或者食用价值。
槟榔对于华夏文明的影响是很大的,它同样对印度文明也有很重要的影响。槟榔传到印度以后,也在印度文明中产生了一系列的发酵,尤其是它跟婆罗门和佛教的结合,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想象。这里我就不详加解释,主要讲它对西方文字的影响。西方文字当中对于槟榔的说法一直是不太确定的,它有两种说法,一种叫betel-nut,一种叫areca-nut,我书里用的是areca-nut,因为betel-nut这个用法不是很准确。西方人对于槟榔这种树一直有个很朴素的认知,以至于后来产生了很大的误会,我在后面会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误会是怎么产生的,以及为什么我要用这个areca-nut。
槟榔在杨孚把它介绍到华夏文明、中原文明之后,就产生了它的第一个用途。因为槟榔是岭南人经常嚼的东西,而当时的中原人对岭南的印象是多瘴气,所以当时认为岭南人之所以在岭南而不会生疾病,是因为他们嚼了槟榔,槟榔可以祛瘴气。所以从这时候开始槟榔被赋予了“洗瘴丹”的别名,人们认为它可以去除南方的瘴气。瘴气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象,如果现在一个北京人要去广东,大概不会把瘴气作为一个考量的因素——其实不仅是现在不会想,从明朝开始就不太会有人想这个事情了。但是如果你放在两汉或者魏晋时期,当时的人对于发配岭南还是非常恐惧的,认为如果我到了岭南的话一定活不长,一定会中瘴气,一定会死掉。总之,至少是在宋代以前,基本上岭南是一个被人畏惧的地方。但是后来为什么就没有了呢,尤其南宋以后基本上对岭南的瘴气就没有太多的描述了?主要是因为岭南的生活条件变得比较好,大家愿意去了,瘴气其实只是个借口,我要是不想去它就有瘴气,我要想去它就没有什么瘴气。生活条件变好了以后,以至于到了明朝的时候,岭南已经变成了一个商贾云集、沃野千里的地方,那时候是抢着去,那些当官的一想到能够去岭南刮刮地皮还是很开心的,这个时候已经完全不畏惧瘴气了。但是在两汉之际,瘴气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槟榔进入中国人的文化视野,马上就被赋予了洗瘴丹的想象。槟榔也成为了下一切气的首选用药,就是指所有的恶气、呕气、觉得气不顺的情况都可以使用槟榔来调节。槟榔当时在四大南药之中作为首选用药,所以对槟榔的需求量很大。不过也不要认为槟榔是个便宜的东西,药在古代的价格是很高的。

槟榔心切片
槟榔入药的形态一般是这样,槟榔心切片以后的圆柱状态,可以看到它的纹路很漂亮。所以我们有时候说一些木料或者一些东西比较好会说它有槟榔纹就从这里来的,因为它的纹路很好。
对于槟榔入药的记录最早是由张仲景开始的。张仲景当时在他的药方当中就明确写了好几味关于下胃气、下呕气、消食的药用到槟榔。从他开始,葛洪和陶弘景都有描述槟榔的使用。经过魏晋以后,它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普遍的下气的用药,中医药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以至于到了东晋以后,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药品。
前面说过汉人南迁对于槟榔的影响,我们知道在槟榔的发展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就是魏晋南北朝,实际上这个时期的核心就在于统治重心的南移。在两汉时期关于槟榔的记载,一般来讲出现在《异物志》里或者一些医书或者药书里,在两汉之后槟榔开始普遍地出现在中文的文献里面,最核心的要点就在于中国的统治重心从原来的洛阳转向了建康。当把首都搬迁到南京以后——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整个文化和士人集团都向南迁移,它对于槟榔的认知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因为建康离南方近了很多,原来统治的边陲,比如说汉代时把交广二州的首府放在广西梧州和广东封开之间的位置,这里没有什么平地,基本上是西江中游很多山的地方,是非常不适合作为都城或者大的城邑发展的。广州是一个非常适合作为大的城邑发展的地方,都是平地,能够统辖整个珠三角的肥沃平原。在南越国的时候,广州的市区一直都是作为城邑而存在的,但是到汉代的时候这个城邑毁掉了,迁到封开去,意思就是稳定胜于发展。对于汉朝来讲,岭南不重要,所以我需要把你的城邑放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要限制你的发展。那么到了东晋,尤其是在东吴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东吴并不统治北方的已开发地区,所以南方对他来讲很重要,他很重视开发广州。当时的孙吴政权就把原来在封开的交广二州首府搬到广州去了,把广州重新建立了起来。
到了东晋的时候,岭南对东晋来讲也很重要,因为它把北方所有的腹地都丢光了,需要加强对这里的统治,不断地派遣得力的官员,不断地把岭南的物产开发出来,能够为其所用。所以当华夏统治重心南移的时候,槟榔作为文献当中记载的东西就变得特别重要。
大家很正常地会产生这样的想象,比如说在北京,文化资源是很多的,以至于我作为一个广州的文化人都经常想着要搬到北京去住,因为北京实在是聚集了太多的资源,靠近统治重心是文化人天然的属性。建康也是一样的道理,当你的首都在建康的时候,文化人都会跑到建康附近去住,这样对南方物产的记录和描写自然多起来。所以这就造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对槟榔描述最多的一个时代。
大家如果知道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的话,会想到洛阳的白马寺,这是中国第一座佛教寺庙。虽然在东汉的时候佛教就已经传到了中国,但是它真正的兴起是在南北朝,在南北两方都进入大混乱的背景下,佛教就成为了最大的赢家,而且双方统治者都非常需要佛教来巩固他不正统的政权地位。比如说汉代是一个正统性非常高的政权,它对于宗教的依赖是比较弱的,但是南北朝无论是北魏还是萧梁,都属于伪政权,因为自从宋武帝刘裕篡位之后,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了很大的质疑,这个时候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佛教又再一次加强了槟榔的印象。
刚才提到南岛语系族群对印度人的影响,印度人嚼槟榔非常早,在佛教诞生以前印度人就有普遍嚼槟榔的习惯,但中国人没有,主要是因为气候条件所致,印度是适宜种植槟榔的,南亚西大陆的南端都适宜种植槟榔,但是中国不适宜,到现在为止只有海南和台湾是可以出产槟榔的,广东的南部甚至很热的地方都不适合种植槟榔,因为冬天仍然会受到寒潮的影响,槟榔树一旦受到寒潮影响结的籽就非常小,结小籽之后商业价值会大为降低。而在印度,槟榔在佛教诞生以前就深深嵌入了印度文化当中,当佛教诞生以后它已经很自然地成为一种供养品,其中“五树六花”的规定就包括了菩提树、高榕、贝叶棕、槟榔和糖棕。菩提就不用说了,菩提是智慧的化身,高榕一般来讲是一种观赏性很强的植物,贝叶棕的贝叶就是用来写《贝叶经》的,还有藏传的经文也是用贝叶写出来的,它是晒干以后书写经文用的。槟榔则是作为佛教僧侣的香口物和提神物的,一方面是香口,你不可能用你污秽的口气去冲撞佛祖,所以你需要槟榔来香口;另外就是你需要用槟榔来提神,佛教僧侣在打坐和冥想的时候其实是蛮容易睡着的,如果有槟榔就会好一些。糖棕就是用来生产一种褐色糖的东西,也是当时作为寺庙的一种很重要的供养品。
这个规定到了汉传佛教以后没有很好地保留,因为“五树六花”里面全部都是热带作物,汉地不太可能种得活这些东西。菩提和高榕还勉强可以,贝叶棕、槟榔和糖棕是不可能成活的。荷花还能成活,文书兰、黄姜花、鸡蛋花、缅桂花和地涌金莲,这些如果在华北的话应该是种不活的,南方会好一点点,但是也不能完全集齐五树六花。“五树六花”我见到的最齐的是在泰国,泰国的佛教就保持了传统佛教要求的“五树六花”,泰国的僧侣至今也保持嚼槟榔的传统,泰国佛前的供奉就是槟榔。
当佛教在中国的土地上大兴的时候,中国人也突然发现了槟榔。东汉以来,中国人一直把槟榔当成一种药来用,作为一种洗瘴丹来使用,突然发现佛教里面也用到了槟榔,这时候槟榔的地位一下就上来了。所以,槟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作为赏赐品,赏赐给僧人或者寺庙。那个时候,槟榔的价格非常高。
我们后来能够找到的关于汉人使用槟榔作为一种信仰象征的标志,最明确的例证就是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墓,他的墓前是有两盘槟榔的,明确地把槟榔供奉在墓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发现,就是铁证,说明它对于佛教的强烈的信仰。因为张文藻墓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墓葬,使用的是西天荼毗礼的葬法,把人烧成灰以后扎在一个木偶里面埋下去。它后面的经文全部都是佛教经文,里面所有的贡品没有出现肉食。南朝萧嶷的遗嘱里面也是这样强调的,萧嶷嘱咐家人在他死之后不能给他供奉屠宰的三牲。大家知道按照儒家的传统,一个亲王去世的时候至少要用到少牢的规格,是需要屠宰牲畜的,但是在萧嶷的要求当中不允许出现这个,他要求用槟榔和肉干、酒来供奉——在部分佛教概念当中,肉干属于三净肉。所以,在那个时代,槟榔已经被认为是一种佛教的,而且可以用来取代传统儒家的礼仪。

张文藻墓中,最右侧的两个贡碟盛放着槟榔
但是我认为即使在张文藻的墓里面发现了槟榔,也不能认为在辽的时代,北方就有广泛吃槟榔的可能性,因为我始终认为在北方槟榔是作为一种非常昂贵的东西,或者说只跟佛教信仰搭配的东西出现,它可能没有那么广泛的流行,只是少部分的贵族会享用,它毕竟是个高价物。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墓葬里面发现的东西是个常态,但其实是个变态,比如我们考察一些比较重要的遗址会发现青铜器,但是古人吃饭真的是拿青铜器吃的吗?不可能的,古人吃饭是拿陶器吃的,只是那些陶器没有保存下来,它有一个幸存者偏差的问题。
到了南朝以后,(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两种用途——一个是槟榔的药用用途,是从它物体的本身特性来出发的,另外一个是佛教的用途,直接从印度佛教传过来的,被中华文化所借鉴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说的四种对槟榔的想象当中很重要的一种,叫做“调直亭亭,千百若一”的想象。这个想象使得槟榔多次出现在贬谪诗里面,就是当一个中原的文人或者士大夫被贬到南方的时候,他通常都会写到槟榔,而且会一再强调自己的心跟槟榔一样,无限的向往,对朝廷有忠诚度,比如这一段写的“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倾,下不斜,调直亭亭,千百若一”。这其实是体现了槟榔作为一种物被颂扬的状态,它被汉人赋予了一个文化上的想象,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植物。这种想象是汉文化叠加给槟榔的第一次想象。
当然这种想象很快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想象:对伴侣的忠贞不二。因为这种想象一般指的是对皇上的,虽然我被发配到了岭南,我见到了槟榔我就把它写下来,以表达我对朝廷的心是没有变的,我还是心向皇上,心向朝廷的。但是到了民间以后,做官的机会不是人人有,情爱的关系是人人都有的,这种想象就变成了忠贞不二的相生相需,就变成了民间的定情信物。经过中国文人的不断加工以后,槟榔在中国文化的形象被进一步加固了。比如李白的《一斛槟榔》,“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使用了这个典故,还有“泪向槟榔尽,身随鸿雁归”,庾信的《忽见槟榔》“绿房千子熟,紫穗百花开。莫言行万里,曾经相识来”。由于这些文人对槟榔形象的渲染,槟榔在中国文化当中形成了更加强烈的文化印记,使得槟榔变成了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标志物,就好像我们一般说到莲花就会想起《爱莲说》,或者说到芙蓉就会有一系列的文化想象。槟榔的文化想象是从这里开始的,它是比较正面的。但是在陈灭亡以后,由于统治重心的转移,对槟榔的记载就开始减少,所以第一个高潮就过去了。
槟榔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面是一种岭南的风俗,这种民间风俗由于我们对于槟榔的想象,形成了一种很固定的男女情爱的印象。比如苏轼,他写到槟榔的作品大概有七八首,他写槟榔还有一个意思其实是包含了对朝廷、对皇上的尽心尽力,或者说我的心没有变,我随时可以被你召回开封去。包括杨万里的《小泊英洲》也写“人人藤叶嚼槟榔,户户茅檐覆土床。只有春风不寒乞,隔溪吹度柚花香”,杨万里写这种田园诗写得非常优美,他这里写的英洲就是现在广州的英德,产英德红茶的地方。
我们再看看古代人吃槟榔要花多少钱。我们现在如果看到槟榔的话,在北京有20块钱、30块钱、50块钱,还有一种100块钱的,所以槟榔是个很贵的东西。在古代它也是个很贵的东西。根据桂林通判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小而光者为鸡心槟榔,大而扁者为大腹子。中下细民,一日费槟榔钱百余”,这个“钱”是指制钱,制钱百余就是一天要花掉一百多枚制钱来买槟榔。以一百论,千文是一贯,一天要吃掉十分之一贯,当时从八品的知县月俸是15贯,可以想象一下槟榔耗费的钱的数量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比例。
但是宋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大家有没有发现宋代的老百姓生活标准好像特别高,尤其在南宋的时候,除了粮食收入以外,还有很多的货币收入。实际上,南宋时期的人民生活水平是远比明清时期要高的。那个时代的人如果日费槟榔钱百余是可以承受的,放到明清以后基本上没有这样的记载了,因为明清以后老百姓已经吃不起槟榔了,所以后来槟榔的衰弱跟老百姓吃不起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看一个东西的传承其实民间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东西在老百姓当中有很大的市场大概率能够传下去,如果它只是贵族食用,当这个贵族或者这个朝廷被推翻的时候它就会完全的消失,不能传下去。
在广府的历史当中有大量的关于槟榔的记载还有实物的留存,包括槟榔用具,这些都在广东省博物馆可以看到。大家知道故宫里也会展出槟榔荷包这样的东西,清代的内府经常会出现槟榔包,所以实际上各个地方主要是社会的上层都有嚼槟榔的习惯,因为你会看到这些槟榔器都是用银做的,槟榔习惯在其他地方的消失也跟这些上层有很大的关系。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槟榔荷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