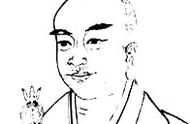阿底峡
《玛尼宝卷》的编订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宗教背景。首先,我们知道,按照西藏传统的说法,在九到十世纪,西藏经历了“朗达玛灭佛”,佛教已经毁灭殆尽,西藏历史进入了一个“黑暗期”。现在很多人质疑“朗达玛灭佛”的真实性,说朗达玛死后,吐蕃进入了政治上的分裂期,强人四起、纷争不断,后来连藏王墓也被盗掘了,经济也经受了灾难性的衰退,因此他难以逃脱末代君主常常会被污名化的命运。我们知道赤祖德赞(806-841)时候颁布了“一人出家,七户供养”的政令,佛教活动需要消耗国家大量的粮食、财力、物力,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对佛教的支持,佛教事业是难以为继的,故自然就会走向衰落。后弘期伊始,当佛教再次传入西藏的时候,藏人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像松赞干布这样的转轮圣王,他不光是能够在政治和军事上统一西藏,还可以从教法上重新振兴佛教。宁玛派,或旧译密续派(gsang sngags rnying ma),是吐蕃最古老的佛教传统,他们的黄金时代正是在吐蕃前弘期,尤其是三圣王统治时期。到了后弘期,自十二到十三世纪,宁玛派面临着萨玛派(gsar ma)即新译密续派(gsang sngags gsar ma)的挑战,以卓弥译师释迦也失(’Brog mi Shākya Ye shes,992-1072)为代表的藏地新译密续派的译师们从北部印度地区大量翻译无上瑜珈部(Anuttarayoga Tantra,Bla na med pa’i rgyud)的密续,诸如《密集金刚本续》(Guhyasamājavajra Tantra)、《喜金刚本续》和《胜乐金刚本续》(Cakrasaṃvaravajra Tantra)等。新译密续派的译师们历经万难远赴印度求学,学成之后回到藏地,说着印度典雅的语言,念诵着印度悠扬的咒语,推崇着印度时髦的新神,谈着当时最深奥的佛理,迅速俘获了藏人的心,冲击着作为旧派的宁玛派在藏地的宗教地位和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宁玛派重新将目光转向了前弘期,转向了观音菩萨化身的圣王松赞干布,他们使用《玛尼宝卷》这种伏藏文本重新建立起宁玛派与吐蕃黄金时代的联系,渴望昨日再现,辉煌重来。这显然有点一厢情愿,自吐蕃灭亡以后,西藏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政权。即使松赞干布在位时,它也不是西藏历史上最强大的时候,后者出现在赤松德赞统治时期,是他建立起了一个仅次于唐朝的大帝国,从西安一路向西,到今天新疆和田,和田再向西的中亚地方也都是它的统治范围,但在朗达玛遇刺之后,这样的一个大帝国便永远地消失了。

卓弥译师释迦也失
在西藏历史上,后弘期早期的一些上师也曾被认为是观音菩萨的转世,如阿底峡的大弟子仲敦巴,但这只是个别的现象,噶当派的活佛转世并没有形成体系。宁玛派对于观音崇拜在藏地的兴起和传播有巨大的贡献,但最早建立活佛转世系统的不是宁玛派,而是新译密续派的噶玛噶举派,它是从三世噶玛巴让迥多吉(1281-1339)开始的。三世噶玛巴在十四世纪的时候就引用过《玛尼宝卷》,可见作为一部宁玛派的伏藏文本,《玛尼宝卷》也曾被新译密续派全盘接受,其原因主要就是观音菩萨崇拜已成为当时西藏普遍的信仰。甚至在尼泊尔和东印度地区,当时也流行观音崇拜,例如十二至十三世纪来到藏地传法的印度瑜伽士米得兰左吉(Mitrayogin)就以擅长观音修法而著称。他传播的多种观音修法仪轨不仅被译成藏文,后来在西夏蒙元时期也被译成了汉文,这些文本一直保留至今。《玛尼宝卷》能被新旧密续派普遍接受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里面收集的多种观音求修仪轨没有明显的宗派属性,是新旧密续派都能接受的修法和仪轨。《玛尼宝卷》不仅被视为松赞干布的遗训,而且还被视为他的灵魂(rgyal po’i bla)的延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玛尼宝卷》的出现就意味着松赞干布的再现和观音菩萨的转世。早年我曾用心研究过一世达赖喇嘛的生平和他对于格鲁派活佛转世系统形成的历史贡献,当时看达赖喇嘛的多种传记,就发现它们一开始都要讲述观音菩萨的故事,强调传主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他来到人间的使命就是为了救度雪域的有情众生。

印度瑜伽士米得兰左吉
今天我们习惯于将西藏的转世活佛都称为仁波切,这其实是很不恰当的。或者说,将西藏的转世喇嘛称为活佛本身就是不恰当的,佛不生不灭,本来就没有活和不活的区分,更重要的是,活佛不是佛,他们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如果我们对西藏的历史有比较多的了解的话,我们知道西藏历史上被称为仁波切(Rin po che)的上师并不多。而且这几位最著名的仁波切都是佛,他们是不会转世回来的,如上师仁波切(Guru rin po che)莲花生,觉沃仁波切(Jo bo rin po che)阿底峡和杰仁波切(rJe rin po che)宗喀巴,他们都被称为“第二佛陀”,住在佛土,不再转世回来。回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的转世活佛都是观音菩萨,其中最早的化身是三世噶玛巴让迥多吉。噶玛巴上师的藏文称号之一是chos rje rin po che,后来明代永乐皇帝赐封五世噶玛巴上师为“大宝法王”,授予如来大宝法王龙钮白玉印。后人对噶玛巴上师所享用的“大宝法王”称号十分推崇,赋予它十分崇高的政治和宗教地位,其实所谓“大宝法王”无非就是chos rje rin po che的汉文意译。大宝法王在元、明西藏地方政治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力,但是越到后来他们在西藏宗教的影响便越来越大,远远超过了他的世俗影响力,所以,到后来大宝法王就变成了西藏宗教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明代中原的官僚体系里面,并没有法王或者上师的具体位置,明代分封了很多法王、国师和西天佛子等等,他们虽然声望显赫,但都不归属于明代的官僚体系,不像在元朝帝师是从一品的高官,地位很重要,而到了明代和明以后的西藏社会,法王、国师、上师和仁波切们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超越了传统的地方权贵、家族的影响力。

永乐皇帝颁给得银协巴的大宝法王印,西藏文化博物馆藏。
以往有学者提出,活佛转世系统的建立是为了解决藏传佛教寺院领袖的继承问题,它是选拔寺院和教派继承人的一种善巧的手段。例如,格鲁派和噶玛噶举派都是用活佛转世系统来解决教派继承人问题的。在整个藏传佛教体系里面,宁玛派和萨迦派早期都没有建立活佛转世制度,因为他们的教法传承都以家族为中心,通过父子(yab sras)、叔侄(khu dbon)相续的方式代代相传。十七世纪之后,转世活佛在藏传佛教各个教派中都出现了。现如今,活佛越来越多,以致网络传言朝阳区就有三十万仁波切。以前索甲仁波切写《西藏生死书》时专门提到,现在的世界越来越富裕,但受苦受难的人却越来越多,如华尔街的人就最需要救度,因为他们是饿鬼转世。很多人经济上富裕了,但脑袋越来越有问题,越来越需要得到菩萨的救度,所以,随着世界上需要被救度的众生越来越多,菩萨的重要性就越来越大,以致今天社会上仁波切再多也依然供不应求。但是,我想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一个理念依然还是世人对观音菩萨的信仰和崇拜。
藏地从后弘期开始所传的观音法门便与汉地观音菩萨信仰呈现了明显不同的形态。印度佛教从六世纪之后,受到印度教教派中的湿婆派、毗湿奴派和性力派的影响,开始向秘密宗教方向发展,而观音修法体系亦不例外,也开始向密教化、仪轨化转变。观音崇拜在后弘期再次传入藏地当在十世纪之后,藏地当时更多地受到了观音崇拜的密教化传统的影响,比如《玛尼宝卷》第二部分就是以观音菩萨为本尊的成就法,主要是修本尊禅定,所以很多本尊禅定主修观音菩萨,出现了不少观音菩萨密教化的形象。元人盛熙明《補陀洛迦山传》中说:
藏教密乘经中所载,观自在菩萨为莲华部主,现诸神变,忿怒则称马首明王,救度则圣多罗尊,满诸愿则大准提尊,及如意轮王、不空羂索,乃至师子吼,并毘俱胝、一髻、青项,白衣、叶衣,千首千臂,皆有仪轨、真言,略举其名,若西天未译番本,师传本续,真言要门,未易悉究。
我们现在知道藏传佛教中的观音菩萨求修仪轨多种多样,名目繁多,它们早在西夏时期就已经被翻译成西夏文、汉文传世。在九至十四世纪的西夏和蒙元时期的西夏文佛教经典中,同时出现了观音的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即源自藏文的“观自在”和源自汉文的“观世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安海燕老师写过一本《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研究》。她最早对在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明代汉译藏传佛教的观音修行法本做过细致的研究。当时,我曾和安海燕一起花了很大的力气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复印出来《观世音菩萨修习》和《观音密集玄文》两套观音修法文本,其中包含了二十多种不同的观音修法。我相信还有更多的观音修法仪轨等待我们去发现,因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观世音菩萨修习》仅仅是这套观音修法集成中的第九卷的内容,前面至少有八卷内容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也不知道这第九卷后面还有多少卷轶失了,总之这部文集中原来所收集的观音修法的数量应该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这些。只是今天我们在汉文文献里面见到的观音菩萨修习的文本已经足够的多,而且我们在藏文文献里面可以找到大量的与这些汉译观音菩萨修行文本相应的藏文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