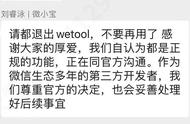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生在杭州,死在柳州、穿在苏州,食在广州”,足见广州的饮食早就蜚声全国。羊城的诸多美食,“天下所有之食货,粤东几尽有之;粤东所有之食货,天下未必尽有也”,其中颇有些令外人瞠目的食材,蛇肉称得上就是其中之一……
古人食蛇
岭南多蛇。这是因为蛇类属于冷血动物,喜暖畏寒;而岭南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冬暖夏长,气温高,温润多雨,利虫蛇类生长。淮南王刘安谏汉武帝远征南越就说,“南方暑湿,近夏瘴热,暴露水居,蝮蛇蠢生……”偏偏以普通人的观感而论,蛇类状貌奇特,天生给人一种恐怖与厌恶感。唐代李德裕在《谪岭南道中作》中写,“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石避燕泥”。区区两句就写出了作者在谪贬途中处处提心吊胆的感受。《广东新语》也提到岭南“蛇之类甚众……蛇种类绝多……予不欲言,宁言猛虎,不欲言毒蛇也。”这种恐惧感反映在汉字上,就是连带着产蛇的地方也跟着倒霉,比如汉代的《说文解字》就明确声称,“南蛮,蛇种”、“闽,东南越,蛇种,从虫门声”……

“闽”的字形演变
但这也并不是说,古人就因此彻底对蛇类敬而远之了。对于早期人类而言,蛇类与其他野生动物一样,是一个寻常的食物来源。《山海经》里就有食蛇的记载,譬如 “……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齿,食稻啖蛇”,“又有朱卷之国,食象。又有黑人,虎首鸟足,两手持蛇,方啖之。”
如果说,《山海经》尚且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的话,另一些古籍则确凿无疑地显示,岭南的一些古代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食用蛇肉。北魏的《水经注校》里说,“(交趾)山多大蛇,名曰蚺蛇,长十丈,围七八尺……山夷始见蛇不动时,以以大竹籖籖蛇头至尾,*而食之以为珍异。”南宋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也提及:“深广及溪峒人,不问鸟兽蛇虫,无不食之……至于遇蛇必捕不问短长……悉取而燎食之。”同时代的《桂海虞衡志》也留下了土人捕蛇的珍贵记录:“寨兵善捕之数辈满头插花趋赴蛇,蛇喜花,必驻视,渐近竞拊其首,大呼红娘子,蛇头益俛不动。壮士大刀断其首……数十人儿之一村饱其肉。”晚至清代,根据《粤西丛载》的记载,对于当时岭南的“俚民”而言,蛇就是他们普通人家的平常食物,烹制蛇类食品的本领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技能,就像以面食为主的北方人必须会擀面、做馒头一样。故而他们用“若修治水蛇黄鳝,即一条必胜一条矣”而不是“裁袍补”来夸耀姑娘的能干。

蚺蛇
此类嗜蛇的情况,大概是与早期岭南地区生产条件落后,民间生活条件艰苦,平时“至难得肉”有关。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边徼荒凉之地海南岛。“天涯海角”的肉食匮乏给这位发明了东坡肉的美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闻子由瘦》写道,“土人顿顿食诸芋,存以熏鼠烧蝙蝠。”诗末自注云:“澹耳至难得肉”。由此不难想象,食蛇同样应是早期岭南先民弥补蛋白质严重不足的一个重要途径。

北宋时期的海南岛
另一方面,在进入了文明时代之后,一个民族或地区的人们吃什么的选择,却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们的文化风俗。例如动物的内脏,在中国“吃什么补什么”的传统观念下,受到人们普遍喜爱,售价很高。可是在西方,动物的内脏是低贱的,其地位与其在中国的地位就刚好相反。大约因为“龙崇拜”是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龙的形象则出于大蛇——这从古代服饰文化中也可见端倪:帝王着龙袍,王公大臣则穿蟒服,帝与臣,龙与蟒,仅有大小而无类属的区别——由此食蛇也就成了禁忌话题。西汉武帝时期成书的《淮南子》里总结,“越人得蚺蛇以为上肴,中国得而弃之,无用”。这就说明在食蛇方面,中原与岭南在很早就分道扬镳了。
殊途同归
至迟到宋代,中原汉人不吃蛇的传统已经为周边民族所知晓。《宋史》就记载了黎桓(越南前黎朝君主)接待宋朝使节时的一次带有挑衅意味的举动,“令数十人扛大蛇长数丈馈于使馆,且曰:‘若能食此,当治之为馔以献焉’”,一个“若”字就表明他心里其实很清楚宋使是不会吃的。
耐人寻味的是,秦朝统一岭南后,随着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入这片先秦时期的蛮荒之地,岭南开始走向汉化;随着“独尊儒术”政策在汉帝国的普遍推行,岭南又进入进一步儒化的时代;到了明清之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更是论证“粤人”“大抵皆中国种”,是中原移民的后代,与傜、僮等原住民明确区分开来;但岭南食蛇的食俗却并未因为此地的族群替换而消逝,而是顽强地延续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