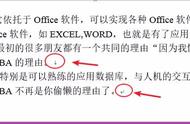烙馍(luo mo),这个词在馍都西安方言里很常见,现实市面上却没有烙馍这个馍。
在馍都甚至馍省,烙馍都只是个动词,它只是做蒸馍、锅盔馍、坨坨馍、白吉馍、石头馍,等一系列馍的过程和动作。
譬如这段对话:
弄啥呢?烙馍呢!烙地啥馍?烙坨坨!
烙馍在这里的用途一清二白,作动词用。
烙馍作为一种馍被叫响是在江苏徐州一带,距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相传楚汉时期的徐州,刘邦的部队在打仗时把烙馍当军粮用,能当军粮用的馍肯定都有的共性就是耐放、耐饥、耐摔、耐压。
徐州的烙馍之所以说它是潜伏在馍都的烙馍,这跟西安的外来人口比例有关,西安人淳朴善良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西安的外地人很多,这些外地人祖祖辈辈在西安扎根繁衍演变为土生土长的外二代外三代甚至外四代,从显性看这些外地人中河南人居多,因为他们好像说的都是“河南话”,但细分起来这里面苏北的的调调还是占不小的成分,具体说就是江苏徐州一代的人还是不少的。
烙馍经过上千年的繁衍传播在河南地界也广泛流传着,据我所知在西安的很多河南人里也有吃烙馍的印记,还有好几个河南朋友经常跟我争抢烙馍发源地是他们老家的。
这一批人在纬度上跟西安一致在吃饭口味上与西安人比较接近,在吃食上很容易和此地人融合,加之西安馍的丰富多彩和方便,烙馍相对来说因其制作过程及工艺的局限性就一直没有在西安推广,而以徐州为中心的一大批烙馍群族对家乡味道的情节却是顽强的,烙馍成为了许多家族的保留传承项目代代相传,默默潜伏流传在西安的深巷之中。
我就是徐州来的外二代,我的父母在解放初期来到西安,随之带来了三大宝:红木箱子、大圆子、铁鏊子。

红木箱子是徐州闺女出嫁时娘家妈必须送的嫁妆,寓意闺女出嫁到婆家永远吃香;大圆子是柳条编的大篮子,很实用能装很多东西,结实耐用储物搬运都很方便;铁鏊子是做烙馍的专用锅,铸铁的,一尺见方的圆,中间微凸周边带三个支脚。
历经七十多年的岁月,父母早已驾鹤西去,他们带到西安的宝贝红木箱子只剩下了一对铜锁扣,大圆子保存完好成为了文物摆设,唯有铁鏊子不见了踪影,是烂了还是扔了问了哥哥姐姐们没人知道。
人啊,很奇怪,年轻的时候打打**一个劲地想挣脱原生家庭的束缚,老了老了倒越发地回想起小时候家的味道。
铁鏊子丢了,想家的味道却越来越强烈了,有时候也会用电饼铛凑和着做几张烙馍解解馋,但电饼铛的味道怎能替代铁鏊子呢。
据查烙馍在徐州已经申遗成功,徐州烙馍在西安却一直潜伏着,至今没有一家像样的烙馍专卖店,早几年隐隐呼呼听大哥说北郊有一家烙馍店再问具体位置和经营状况又都说不清。
想想我八九岁就跟父母言传身教学下的正宗烙馍童子功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馍都,心里确实不甘,今借「贞观」广而告之把潜伏在馍都的烙馍宣传一下,铆不定哪天我还真开一家以烙馍为主打的馍店,让徐州烙馍给馍都再锦上添一枝花。
烙馍的原材料很简单普通粉、高筋粉都行,制作手法要求技术性比较高,首先面要和得不硬不软,要醒到柔到,制作好的面胚搓成手腕粗的长条左右手配合把面分成满把抓大小的剂子,把剂子揉搓成馒头状,一大把干面粉堆到面剂子上用手掌按成饼,用尺把长的擀箸子(徐州方言小擀面杖,中间粗两头细的那种)开擀,几十秒约一毫米厚薄均匀脸盆大小的正圆薄面皮子就擀好了,把擀好的生面皮如衣服一样搭在擀箸子上,移铺到架在旺火炉子上的铁鏊子上,用半米长两指宽打磨的光滑圆润的薄竹坯子正反折叠地把生面皮子在滚烫的铁鏊子上翻腾三五下,一张鼓着小黄泡泡柔软筋道的烙馍就完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