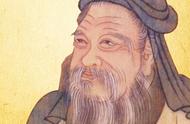梳理茶花以免影响茶树生长
乌岽村的牌坊是2015年左右才修建的,也算是乌岽村的标志性建筑。由于天气晴好,视野非常开阔,站在牌坊处,有点群峰竞秀、万壑争流的感觉。脚下的茶园一直延伸到山脚,与其他山头上的茶园遥相呼应;沟壑间的梯田连绵起伏,规整而有韵律,极富节奏感……据说,凤凰山是畲族的发祥地,境内的第一高峰凤鸟髻和第二高峰乌岽山终年云雾缭绕,很难得窥全貌。偶然的一次造访,竟得老天如此眷顾,我们情绪也随之高亢起来。
不过,随后的品茶经历却让人心生晦涩,给刚刚才点燃的情绪泼上了一盆凉水。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没有永远的高潮,也不可能永远处于低潮,沉浮动静皆人生,起起落落乃常态。只不过,我们不能因为个人的情绪和好恶,而影响曾经接待过我们的茶农,不管他(她)当时是真情,还是假意。因而,在此后的行文中,把初制所的名字和茶农的姓氏都隐去了。

乌岽与其他因茶而富的村庄一样正在野蛮生长
进入村庄,采花大姐介绍的茶农A果然在门口等着我们。热情招呼落座以后,问道:“你们平常喜欢喝什么茶?准备寻点什么茶?”
由于有了多年跑茶山的经验,小菜也没有客气,直接提出了要求:“正宗乌岽山的,年份老一点的,焙火起码三次的。”
茶农A满口应承下来,在旁边一堆茶叶里摸索出一泡茶泡上:“这是鸭屎香,目前最受欢迎的香型。”
我端起茶杯,一口茶汤入口,眉头立即皱了起来,偷眼看小菜,她正用一种怪异的眼神望着我。显然,这泡茶没有任何一点符合她刚才提出的要求,而且,口感极差。
“好吧,就当是对我们的试探和考验吧。”我想。其实,寻茶的过程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轻松惬意和风花雪月,沿途的艰辛自不必说了,就说与茶农的沟通,就是一个考验技术和心理素质的过程。一般来说,茶农不愿将好茶卖给不懂茶的人,或者说,更愿意将垃圾茶卖出一个好茶的价格(两者的价差太大了,难免让人浮想联翩),于是,不管是朋友介绍的,还是陌生拜访的,第一次见面,茶农一般都会试一试来者的真实水平。如果技术过关,顺利通过考核,那此后的交流,茶农或许(注意,是或许)会坦诚相待;如果被茶农瞧出了破绽,那大概率会花高价买到垃圾茶。

站在乌岽村牌坊处有群峰竞秀的感觉
我不露声色,组织了一下语言,再次提出要求,“能不能试一泡品质好一点的茶,我们重庆的朋友,喝茶还是比较讲究的。”
茶农A满口答应,又开始在一大堆茶叶里摸索。一边找茶叶,一边还不忘给我们洗脑:“凤凰单丛属于乌龙茶,最大的特点是香,有‘能喝的香水’的说法。凤凰单丛还有一个特点是一丛一味、一树一香,单株采摘、单株制作,香韵个性各不相同。”
“那么,凤凰单丛究竟有多少香型呢?”我们问道。
“最出名的就是黄枝香、芝兰香、玉兰香、蜜兰香、杏仁香、姜花香、肉桂香、桂花香、夜来香、茉莉香等十大香型,”茶农A略一迟疑,“由于命名香型的标准不统一,很多香型其实说的是同一种茶,总数完全没法统计。”
“先不管同一种茶是否有多个名字,就目前出现的香型大概有多少呢?”我们继续追问。
茶农A犹豫片刻,还是给出了她心目中的答案,“大概有两百多种吧!”
说话间,茶农A又泡上一泡茶,指了指我们面前的杯子:“姜花香。”
再次端起茶杯,一口茶汤下肚,顿时五味杂陈。“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试探,而是赤裸裸的蔑视和欺骗了。”我想。抬头看向小菜,她眼神里竟然有几分怒气。
“能不能……拿一泡真正好一点的茶……尝尝。”我嗫嚅道。
“走吧。”小菜站起身径直朝门外走去。

凤凰山从唐代就开始产茶
茶季过后的乌岽村显得很安静,整个村庄里,大多人家都关门闭户,街道上也少有人走动。汽车在村子里唯一的公路上来回走了一圈,终于看到一家开着门的人家,主人正坐在茶台边喝茶。
停车,走进去,自我介绍。茶农B热情招呼,同样问道:“你们平常喜欢喝什么茶?准备寻点什么样的茶?”
对于寻茶,小菜一直要求颇高,有自己独特的标准,按照她的话说:“自己这一关都过不了的茶,怎么好意思推荐给朋友们呢?!”于是又提出要求:“正宗乌岽山的,年份老一点的,焙火至少三次的。”
茶农B转身便开始在靠墙的货架上逐个寻找。边找茶边找话题:“天池你们去了吗?”
“不去了。我们是专程来寻茶的。”我们随意答道。其实,就在刚才,我们才从天池景区大门口返回。
“没去过的话,还是值得一去的。”或许,茶农的这种看似无用的闲谈,同样是一种试探,考察你对茶的态度,辨别你究竟是来寻茶的还是来旅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