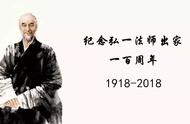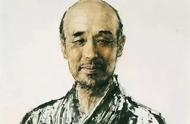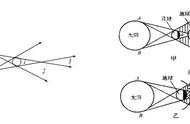邓子美 江南大学宗教社会学研究所教授
开智慧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是神秀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另一个就是惠能的一条途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尘”佛教的说法是有习染,我们从小的生活习惯、生活环境已经形成了“尘埃”。另外也有通过学习而产生不同观念带来的“尘埃”,也叫“分别心”等。神秀的办法是天天去擦拭、剿灭,结果剿来剿去,剿不掉。所以最后的办法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出埃”。第二步就是要遍计所执性,只要我们把念头转过来,这些烦恼随自然就没有了,当然这要到一定境界。但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佛的能力,都能够通过一个小的感悟来转变我们的观念,解除我们的烦恼。
主持人何欢欢:谢谢邓老师!邓老师非常深刻地从禅宗的角度解释了什么是烦恼。禅宗其实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烦恼有,一种是烦恼无。释迦牟尼甚至可以说更早的印度哲学的源头就有这样的“有无之争”。我主要从事中观学方面的研究,从“缘起性空”或者“空性”的角度看,讲“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可以把烦恼直接否定掉。那么,不存在所谓烦恼需要我们去消除吗?还是说烦恼本身就是我们所幻想出来的一种观念,是我们被外界所牵引导致观念产生烦恼?下面我想有请张总教授来谈谈您的看法。
张总:烦恼和智慧,这和佛教的根本有很大关系,因为从佛教创始,本身针对的就是有情众生的烦恼。众生有*与新*,得不到满足,就会带来烦恼,所以佛教根本就有为解决烦恼而建立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本身最重要的修行就是达到阿罗汉果位,阿罗汉的意思就是破除烦恼。然后再下一步就是智慧,智慧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佛教里的智慧是一种特有——般若波罗蜜。佛教对世界有一个透彻的看法,有八正道,有修行戒定慧三学,再发展到大乘六度,就含有了般若智慧。在现代社会中,烦恼和智慧也是时时刻刻都会有很强的体现,有些是科技带来的,一些新的科学技术发展既带来方便,也带来新的烦恼。比如病毒与细菌和抗生素的关系,我们生产出各种抗生素,病菌和病毒就会产生耐药性,现在知道生产抗生素的速度赶不上细菌产生耐药性的速度。所以,新冠疫情等等,甚至有可能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这种大的烦恼,也是某种程度上科技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张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所研究员,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客座教授
中国佛教本身有重要的特点,就是佛教的中国化。佛教中国化在义理方面一个重要的特点,就体现在如来藏思想上,就是说佛性、真如就在烦恼之中,烦恼即菩提。我们要联系地藏正法门来谈,佛教里有八万四千法门。现在中国佛教本身主要就是大乘佛教,其中菩萨道就是一个最主要特色。我们弘扬地藏法门,地藏法门首先是大愿,“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发大愿就是要成佛,要救众生,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大愿,有了宏愿,其他的一些小的方面很自然就解决了。地藏菩萨的大愿又和孝道文化有非常深刻的关系。地藏菩萨、佛教是讲大孝,我们自己对亲人对父母,然后再扩及有情众生,值得我们好好的弘扬和发展。
主持人何欢欢:谢谢张老师!首先我要感谢张老师提出来,我们在台上的五位都是门外汉,应该由法师来讲述佛门里面的真正的智慧。刚才张老师主要从智慧的角度谈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也正好引入了第二个讨论层次:佛教里到底有哪些智慧,不管是比较深奥玄妙的大智慧,还是一些可以切切实实落地的方便法门小智慧,这两类智慧可以分别用来对治哪一些烦恼,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佛教提供给我们的智慧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在把话筒传递给各位专家之前,我想谈一点点自己的看法,刚才张老师举了抗生素和细菌的例子,我觉得特别好,烦恼有点像细菌,智慧能不能比喻为抗生素?如果可以的话,烦恼多了,智慧也能变多?还是智慧越多,烦恼就会越多?佛教讲“所知障”,我有时候会感觉到,懂得越多可能烦恼越多,什么也不懂,可能就是一种本然,可能烦恼就少了。我们可以从智慧的角度来讨论一下,佛教讲的四圣谛、八正道到三十七道品,再到六度这样的大智慧,和小的或者说具体的方便法门,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代生活,特别是世俗的在家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还是从成老师开始。
成建华:佛教讲“信、愿、行”,首先,人要有信念,要有信仰和追求,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信仰观;其次,要发愿,发四弘誓愿,要发矢志成佛、普度众生的大愿;最后是行,就是归结到具体的实践与行动的层面,也就是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即是佛教“信愿行”三资粮的基本思想所在。那么,佛教为什么又说“烦恼即菩提”呢?所谓烦恼即菩提,是从佛教证悟者的角度来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众生本具的智慧、菩提,由于妄念、执着,以及无明和无始以来业的遮覆,障碍了菩提智慧的现前,因此产生了种种烦恼。众生只要一念觉悟,放下烦恼,菩提智慧就会显现出来。所以,烦恼与菩提,在觉悟与迷惑的一念之间。菩提要在烦恼中修,没有烦恼,就没有菩提,所以烦恼与菩提是相即不二的,是一种辩证逻辑关系。修证菩提,成就佛果,需要有由烦恼转化而成的智慧。智慧究竟从何而来?这就要学修“戒定慧”三无漏学。首先要持戒,由戒生定,由定生慧。也就是通过一种修行办法或禅定的功夫,来使我们本来具有的智慧显现出来,这就是开悟。众生是未觉悟的佛,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执迷不悟,不断被烦恼羁绊,需要凭智慧来排解和消除烦恼。所以我们要善于将无尽烦恼转变成无上智慧,做一个有理想,有信念,有智慧,大愿践行,人格完善的智者和觉者。

论坛现场
主持人何欢欢:谢谢成老师!成老师刚才又强调了一下“烦恼即菩提”,我对这句话也特别有感受。菩提虽然不完全等于智慧,因为菩提可以说是智慧的果。“烦恼即菩提”让我想到了《中论》里说的“不依世俗谛,则不得第一义”。所以,如果没有烦恼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有成佛的智慧,更不可能成佛。刚才我就在想,地藏菩萨那么伟大,“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要到地狱中去拯救众生,他把自己的大愿建立在拯救众生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可以从“烦恼即菩提”或者说世俗和胜义相依相成的关系上去理解。这样一来,对我们来说,烦恼本身就不再是一种负担,就像对地藏菩萨来说,拯救众生并不是一种压力,而是实现自我的方式,这种方式或途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不二法门。下面我想请孙教授再来就智慧谈一谈您的看法。
孙亦平:每一个的人生经历都不一样,但每个人生都是烦恼相伴,如影随形,所以才要有智慧,才要学习、体悟和运用智慧。儒佛道三教思想都曾在智慧层面来探讨如何解除烦恼,各家的智慧表达是有所不同的,大乘佛教,特别是地藏菩萨的智慧有其独到性。我在到九华山参加会议之前,为撰写会议论文,专门读了《地藏菩萨本愿经》,还看了《宋高僧传》中的金乔觉传记,最大的感受是,金乔觉是从一个普通的新罗王子慢慢成长起来的。他一生都在跟各种各样的烦恼、困难,跟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伤害在做斗争,最后提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他对自己人生的一种大愿,一种崇高理想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大乘菩萨精神的高度体现,这种概况和总结从某种意义上面讲,就是他在对治烦恼之后所形成的一种人生态度——烦恼不可怕,困难不可怕,关键是要找到对治烦恼的智慧与方法。所以一个人既要树立伟大的理想,同时也要从当下每一个小事做起。正如人间佛教所讲的“做好人,说好话,做好事”,从当下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是对治烦恼的最重要的方法。
主持人何欢欢:谢谢孙教授给我们非常生动地刻画了地藏菩萨如何成为地上菩萨的过程。让我们先从好人做起,我们做好人了,我们以后也能成为菩萨,谢谢孙老师。下面有请邓教授来发表您的高见。
邓子美:论文集里印刚法师那篇论文,他除了强调发愿还愿之外,更重要强调的行愿。换句话说行愿即是:我们的许多习染、习惯,还有外来的那些污染等,通过我们的修行来改变的过程。地藏精神或者是地藏菩萨实际上是从最苦的境地来教我们,最苦的地方会激发出最大的智慧。“愿”跟我们的“行”相应,这样生死都不成问题,其他烦恼就更不成问题。抛开名相的话,我们可以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到我们的地藏法门都贯通起来。最后我祝愿大家都能够转识成智,把我们拥有的知识都转成我们自己的智慧。

论坛现场
主持人何欢欢:谢谢邓老师的美好祝福,看到已经有法师在鼓掌了。确实不管是发心发愿,还是我们大谈特谈什么是烦恼、什么是菩提、什么是智慧,最后的落脚点一定要归结到“行”上去。那么,如何行愿?就要向地藏菩萨学习真正地落到“地狱”里去,在烦恼中修行,在烦恼中增长智慧。这让我想起了《心经》开头的一句话“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里有一个“行”字,我们经常把“般若波罗蜜多”简称“般若”,其实我们往往把“行”字给忽视掉了,甚至轻视掉了,没有这个“行”是出不来般若智慧的。所以“波罗蜜多”事实上就是一种修行法门,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对话的副标题——“地藏正法门”,把佛法智慧落实到“行”上就是“正”。下面请张总来给我们做最后总结发言。
张总:今天在座的多是佛门中人,我们在此而谈,真是班门弄斧。我们首先要有大智慧,有正念。碰到解决各种不同的问题的时候,再用不同的方法手段,从佛教或者其他方面,比如说有病也得去医院、看医生等去解决这些烦恼。第二就是我又想到地藏金乔觉,想到我们中国佛教,就是中国民众信仰力量的支撑。为什么地藏信仰在我们中国发展,而且形成了四大名山、四大道场,形成了地藏菩萨道场。中国的民众自古以来有这个信仰的力量,凡遇到烦恼,要通过佛门也是有智慧的去解决问题,由信仰的力量,才形成九华山这样的名山,这样的道场。另外,从外在的角度,从技术层面或者现代社会发展的角度,与时俱进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社会通讯这么发达,我们现在这种论坛也是弘扬地藏信仰的一种形式,通过媒体、网络把地藏精神传播出去,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努力的方向与要做的事情。
主持人何欢欢:谢谢张老师!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再请其他几位老师发表他们的观点了。我特别喜欢《地藏十轮经》中里面说地藏菩萨是:“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秘藏。”“安忍”其实是玄奘大师的一种特殊翻译,他把前人翻译的“忍辱波罗蜜”都翻译成“安忍波罗蜜”,我觉得玄奘大师用“安忍”一词有着非常深刻的意蕴。九华山的地藏菩萨精神,其实可以从佛教的方方面面来阐述,不仅是“大愿大孝”,还可以从“六波罗蜜”的每一个角度来进行深入探讨与挖掘,我想这可能也是举办这么大型学术论坛的一个目的。我希望我们学界也能配合教界做一些相应的工作,更好地阐发地藏菩萨精神,使这么伟大的地藏精神能和我们当代社会更好地相适应,也能更加深入人心,对社会起到更积极的引领作用。我们第二场对话就到此圆满,谢谢各位老师,也谢谢各位法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