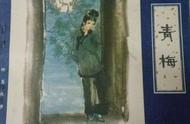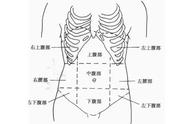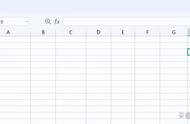这样的对应存在于很多层面之上,有清晰的,也有含蓄的:
两位女主角对情人都很热情,对父亲都很关爱,都有用戒指摩擦自己下睫毛的习惯。
她们都是左撇子,戴红手套,都会注意到身边步履蹒跚的老奶奶。
两人身边都出现了一些物件:润唇膏、能反光的玻璃球、一段绳结...
波兰花拧着音乐夹上的一段绳子直到它断开,法国维洛尼卡收到的包裹里有根鞋带,她把鞋带放在自己的心电图报告边上,绷紧的直线暗示着死亡,和在波兰花棺材上方摇晃着的绳子前后呼应。两人都有着脆弱的心脏、漂亮的歌喉和对范登布登迈耶尔作品的偏好。法国花梦见波兰花的父亲画的那片风景。
她们是同一个人物的东欧版本和西欧版本,一个从波兰农村来到克拉科夫,一个从克莱蒙费朗来到巴黎。

甚至,亚历山大的作品里也需要把同一个人物刻成两个木偶。
在他家,薇洛妮卡发现他正按照自己的样子在做木偶。
“为什么是两个?”她问他。
“因为表演时我反复地碰触它,只准备一个的话有可能会弄坏。”他回答。
他的木偶戏也是和这种对应关系相关的:芭蕾舞演员想要跳舞,似乎突然死去,化身为蝴蝶再次出现。法国花能够飞起来,是否正是因为波兰花跌倒了?
一个波兰女孩的死亡,是否是为让她的法国对应者停止歌唱而发出的警告?在亚历山大第一次给薇洛妮卡打电话后,影片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画面:
她似乎看见波兰维洛尼卡在舞台上歌唱,然后在红色的背景中忽然跌倒。

影片的核心问题似乎来得十分猛烈:
如果说人世正是上帝表演木偶戏的舞台,如果说其中也包含了“反复碰触,可能弄坏”的情况,这世上是否可能存在着一个为我们幸存下去而准备着的替身?抑或我们中的某些人才是这样的替身,为的是让别人能更聪明地活下去?
这也正是我们观后所思考的。

接着法国花侧起了她的脑袋:她在阁楼里午睡,被透过窗户射进屋子的金色光芒弄醒。她起身寻找光线的源头。
她注意到对面大楼里玩镜子的小男孩,和她一样,我们于是也以为是小男孩在用镜子反光玩。但在,就在她关上窗户,回身之后,金色的光线继续出现在她房里,光芒与配乐声一样美丽,并且让人无法解释。
影片的配乐一开始来自剧情范围之内,我们可以从故事中、人物身上找到它的源头:伴随片头字幕出现的歌声是大雨滂沱中的波兰花唱出来的。但随后的音乐声变得越来越玄,它贯穿全片,如同一条魔术般的声音线索,将两个女孩联系在一起,召唤着某种无法看见的神秘力量来产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