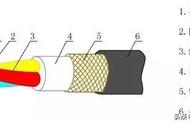如果银娣是一个充满浪漫主义幻想的女孩子,她会坚定地选择站在朦胧的爱情一边,甚至偏颇一点说,银娣仅仅是家境好一些,她也有很大可能站在爱情一边。可这样的假设是无意义的,因为银娣手握那个年代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一人出嫁,鸡犬升天!
这是一个真正的机会,是一个真正的“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机会,更何况银娣本就不是一个甘心永远穷苦的人,她是一个容貌佼佼的女人,更是一个充满野心和希望的穷苦女人,加上她的未来夫君身子孱弱,一重难堪下掩饰的是一重自由,至此,她要披胆孤勇进豪门了。
文章里写到:
“越美丽,到了这时候越悲哀,不但她自己,就连旁边看着的人,往往都有种说不出来的惋惜。漂亮的女孩子不论出身高低,总是前途不可限量,或者应当深不可测,她本身具有命运的神秘性。一旦结了婚,就死了个皇后,或是死了个名妓,谁也不知道是哪个。”
她穷怕了,没有钱的苦楚她受够了,于是她成了姚二奶奶。
姚家的大门一进,便再没有回头路了。

家大业大、人员众多,一眼就看穿了她是从小家来的,没几个人睁眼瞅她,人精似的家仆们打量打量就很明白银娣的地位。
回到房里也没什么温暖的,丈夫的缺陷让柴银娣开始陷入狂热的*之中:对身体的*、对金钱的*、对爱情的*。
终于,她跟家里的浪荡子姚三爷突破了禁忌。

姚三爷成为了爱情、身体与性的替代品,她害怕事情败露,但一边享受着这样的暧昧,一边又担心姚三爷把这件事情戳出去,可这样的刺激何尝不是另一种欢愉?

终于,二爷死了,接下来自由的号角吹响——家里的老太太也死了。
姚家要分家了,她带着二爷的孩子孤儿寡母地分到了不怎么沾光的财产,不过也总算是苦熬了这么久的回报,她独出去过生活了。
她紧紧地攥着手中的钱,极其抠搜,她不能不这样,眼看着家里以后就是只出不进的情形了,可是她心里有个地方还是不安分,就是姚三爷。
就算是这点不安分也在一次会面之后被完全击碎。
他不跟她开口,也不说走。有时候半天不说话,她也不找话说,故意给他机会告辞。
但是在半黑暗中的沉默,并不觉得僵,反而很有滋味。实在应当站起来开灯,如果有个佣人走过看见他们黑黝黝对坐着,成什么话?但是她坐着不动,怕搅断了他们中间一丝半缕的关系。黑暗一点点增加,一点点淹上身来,像蜜糖一样慢,渐渐坐到一种新的原素里,比空气浓厚,是十几年前半冻结的时间。
他也留恋过去,从他的声音里可以听出来。
在黑暗中他们的声音里有一种会心的微笑。
这样暧昧的环境下似乎他们都回忆起了往事,但在这时,外面追债的人让她知道了他此行的真正目的——借钱!
银娣升腾起一种耻辱感,给了他一个巴掌,两人从此断了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