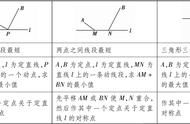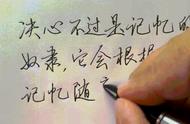“历史学者的责任,我能谈的只有自我期许。我最近正在进行的,是重新理解人类社群、相关历史记忆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我想要揭露它们之间的真正面貌。这多少算是与堂吉诃德所为一样的impossible dream。我认为,历史学者应该检讨自己,反思我们相信的伟大经典。这是对历史经典如何成为经典的反思,也是对经典历史记忆所支持的文明与人类社群的反思。”
——王明珂,历史人类学家
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山间村落中,过去流传一种“毒药猫”传说。毒药猫指的是能变成动物害人或施毒的妖人,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其中还分两种,一种是法力较强能变成动物来害人的毒药猫,一是年老而只能从指甲放毒害人的毒药猫。每当村寨中发生灾害或疾疫,都有一两名妇女被闲言闲语为“毒药猫”。
上世纪90年代,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在川西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田野考察中,听闻了流传于不同村寨中的“毒药猫”传说。虽然这些故事大都夹杂着虚构、真实与想象,但在王明珂看来,它们都共同折射了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实:在许多社会中,女人、弱势群体与社会边缘人常被视为有毒的、污染的、潜在的叛徒或破坏者。在社会动荡*乱之时,他们常成为代罪羔羊。

王明珂在羌族考察期间。受访者供图。
随后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中,“毒药猫”传说不断刺激着王明珂的研究工作。2015年,有感于世界日益增长的群体暴力,王明珂决定搁下其他研究写作,着手将“毒药猫”传说发展为剖析人类集体恐惧与暴力的一般性理论。为此,他将多点田野扩大到近代初期的欧洲及美国等地,考察近代西方的女巫传说与猎女巫行动,重审当下各类宗教与社群暴力现象,理解人类社会中普适性的社群认同与暴力表征。
2020年,在王明珂完成“毒药猫”理论初稿之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疫情与因而导致的各类制度性困顿不仅加剧了全球各人群间的紧张敌对气氛,也引发从日常生活到社会层面的不同形式的猜疑、仇恨与暴力。在《猎巫危机:对新冠肺炎的人文省思》一文中,王明珂一再强调,相比医学病毒,社会性“病毒”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而在新书《毒药猫理论》中,他将自己对于疫情及相关政治、社会、文化情势的思考纳入进来,并就此指出,对于病毒源头、病毒传播途径,以及谁应负责,人们经常脱离流行病学与防疫科学的讨论,而卷入国家、民族等族群认同下的集体恐惧、猜疑与暴力——这仍是施暴于毒药猫或女巫的抗疫手段。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各种“替罪羊”或“毒药猫”暴力事件证明,无论人类文明与理性如何进步,在某些方面我们仍然原始野蛮。

2019年王明珂在一席演讲。受访者供图。
这也牵引出王明珂近年来思考的另一个问题:人类原初社群。在他看来,哪怕到了今天,原初社群的原初性认同仍然具有强烈的情感驱力。“这种深植于全球各种社会文化中的人群结群特质,即情感与现实利益结合,表现在亲属血缘与领域空间并重的认同上,以各种伪装面貌(近代国族建构是其中之一)不绝如缕地存在各历史时期人类社会中。它所蕴含的沉睡在人类遥远记忆中恐惧、猜疑与暴力,在每个时代与世界角落都经常被唤醒,化身为人们意识中的女巫、魔怪、狼人与其他‘恐怖分子’,及至今日。”他在书中写道。
今年5月,我们借由专题《何以为“家”》采访了身在北京的王明珂。在三个小时的专访中,我们从“毒药猫”理论出发,聊到其中的关键概念及与此相关的诸多现实议题。我们也聊到近年来他对于人类文明、族群认同的新认识。
最后,面对灾难频发的当下,王明珂谈及身为历史学者在今天的责任。他指出,在今天,历史学者应该检讨自己,反思我们相信的伟大经典。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对王明珂的专访。

王明珂,著名历史人类学家,台湾“中研院”第30届人文社会科学组院士,曾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长期从事于结合华夏与华夏边缘,以及结合人类学田野与历史文献的中国民族研究,其多点、移动的田野考察遍及青藏高原东缘羌、藏、彝族地区。主要著作有《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择》《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毒药猫理论》,以及《寻羌》《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等田野杂记及随笔集。
“替罪羊”vs“毒药猫”:想象的敌人或许会成为真的敌人
新京报:你最早是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羌族田野考察时听闻的“毒药猫”传说。而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你也花了一定篇幅论及“毒药猫”传说及这一隐喻的普遍性。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想要将它发展成为一套理论,而不是仅仅作为族群研究中的一个田野资料和例证?
王明珂:我在羌族地区采取的是一种多点田野考察方法,也就是从多个田野地点之间的差异里面去了解当地的一些社会现实。相对于我观察到与听到的各地差异,每个地方所讲述的“毒药猫”传说却都差不多,那么,我认为这样的共同社会表征之后应是一种更基本的社会现象。
如果我们将“毒药猫”传说的故事结构抽取出来,还会发现它与西方女巫传说有很大的相似性。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毒药猫”故事反映的这种人类社会性就不仅存在于羌族地区,而更可能是世界性的,因而也就想要更深入探究这一主题。
近年来让我着力于这项研究,也就是将它发展为一关于人类集体恐惧与暴力的一般性理论的动机是,这世界日益增长的各社群间以及社群内的暴力,各种被称之为恐攻与反恐的暴力。然而虽然我在《羌在汉藏之间》这本书里已经论及“毒药猫”传说的意义和它可能具有的重要性,但以我在羌族所得田野资料来讲,还没办法将其发展成为一般性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