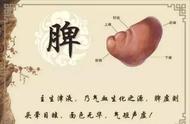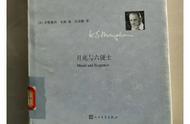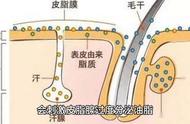肖克在妻子姚妮的建议下,去参加了亲子教养研习班,当时他们的儿子肖亮快两岁了。肖克告诉我,他和妻子原本商量好不要孩子的,不过姚妮四十岁的时候改变了想法。经过一年尝试自然受孕,又做了一年的试管婴儿后,她终于*了。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有了这个孩子,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对生活中多了一个孩子会变成什么样子一无所知。我想我是受电视的影响太深了,我以为婴儿都像电视里演的一样,乖乖地在婴儿床里睡觉,几乎不哭不闹,全家一片和谐美好的景象。

肖亮出生后,我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随性地做事情,有了孩子后的生活缺乏色彩,育儿的过程既单调又乏味,我们俩总是有一个人没黑天没白天地照顾孩子。这种种变化让我的情绪时而愤怒时而沮丧,有时甚至是既愤怒又沮丧。
两年过去了,我依然不能享受正常的生活。姚妮和我之间的话题也只有孩子,即使我想聊点别的,不到一分钟,话题又会回到孩子身上。
我知道我很自私,性格也太暴躁。坦白说,我觉得我和她们母子俩一起生活的日子应该撑不了多久了。我请肖克描述一下他的童年,但他说,他没什么兴趣跟我一起探讨他的童年,因为他的童年很正常。当时我把他所谓的“没什么兴趣”解读成他想跟童年保持距离。我猜想,为人父母可能触发了他想逃离的感觉。

我问肖克,他说的“正常”是什么意思。他说,父亲在他三岁时就离开了他,在他之后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探望越来越少。马克说得没错,这是“正常”的童年,大部分孩子的童年,父亲都是缺位的。然而,这不表示父亲的消失对他来说无关紧要。
我问肖克,他对父亲的遗弃有何感想,他说已经不记得了。我试探着问,也许是因为太痛苦才记不起来吧。也许他像他父亲那样离开姚妮和孩子会感到轻松,因为这样,他就不必打开内心那个积满复杂情绪的盒子了。我告诉他,把那个盒子打开很重要,否则他无法察觉儿子的需要,也会把自己从父亲那里接收到的情绪传给孩子。从他的反应,我无法判断他是否听进了我说的话。

六个月后,我在再次见到肖克。他告诉我,他一直很抑郁,但他没有忽视这个状况,决定开始接受治疗。令他惊讶的是,他竟然在治疗师的房间里哭诉父亲离开他的事情。
心理治疗帮我把情绪摆在适切的地方,也就是说,摆在父亲的遗弃上,而不是下结论说我只是不适合这段关系,或不适合做父亲。
我仍会感觉到无聊,心中也还有怨恨,但我知道这种怨恨是过去造成的,跟孩子无关。
现在我已经明白把所有关注放在孩子身上的意义了,那是为了让他感觉良好,不仅是现在,他未来也会因此而感觉良好。
我和妻子正以我们的爱来填满他,希望他长大以后,会有满满的爱可以付出,并因此觉得自己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