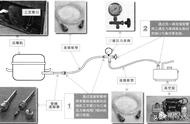潮汕地区的婚嫁习俗之复杂应该在全国都出了名,但外人有所不知的是:具体到每个区和每个村,习俗都有所不同。
随着时代的改变,大家慢慢都在提倡从简,但即便是从简了的仪式,身处其中的我们依旧疲惫不堪,以至于冲淡了真实感。
而回顾我整个嫁人仪式中最舒服的时刻,可能便是冲洗五天没碰水还涂满发胶的长发那一刻吧。

出嫁前的一个重要仪式是“冠笄”。
是看了时辰的,所以我早上不能赖床,怕过了吉时。
但这么一个听上去郑重其事的仪式,其实就是洗头。
“就跟平时一样洗吗?”
我跟我妈妈确认,“听说有的姐姐是可以去发廊洗的喔,还有我同事她是要洗花水(加了各种植物的水)的……”
“我问过啦,就跟平时一样洗就好了,到时候洗澡才需要花水。”
我妈为了增强她指示的说服力,又跟我说她是请教了已经嫁过女儿的谁谁谁。
“那我去洗啦?就跟我平时一样站在莲蓬头下冲喔?”“对呐对呐。”习惯了洗头和洗澡一起进行的我,开始了别扭而认真的“冠笄”。
我站在淋浴莲蓬头的左下方,弯腰让水冲过我的头发,又尽量不要弄湿我的衣裤,袖子和裤腿都已经被我尽可能地往上卷起,领口也垫了毛巾,可是只要稍稍姿势不对,水依然会顺势而下,跑赢我调整角度的速度,弄湿了某一小块衣服,贴着皮肤,凉飕飕的。
这个洗头的姿势,我觉得非常不痛快。
却在眼睛的余光瞟到水珠下落的时候,走了神,任水流直下,告诉自己,要不洗久一点,显得更有仪式感一些。
洗完头,我直到出嫁都不能出门了,迫不得已非要出门也得戴帽子,头发不能再见天。
而我更担心的是,尽管我已经用了干爽去屑的洗发水还不敢加护发素,可是我这头发,接下来要三四天不能洗,真的好吗?

“担衫”
第二天上午,陈先生要来“担衫”,按我老家的习俗是下午来,不过陈家那边是上午,所以我八点就被妈妈叫起来了。
“担衫”,顾名思义就是拿衣服,旧时应该是用担子担着走的。
准备两个红色行李箱,装满衣服和陪嫁的首饰,衣服多是新衣服,总件数要成双。
有的地方讲究新婚四个月内不能买衣服,还好我家没听说有这个习俗。
一起送过去的还有一对对浴巾毛巾组合,还有一盆传统物件,是很复古的搪瓷盆,里面装的除了成对的拖鞋牙膏牙刷漱口杯镜子梳子,还有很多我觉得很可爱的东西,比如一对红竹筒(大人叫对笙),一对红尺,一把红剪刀,一对烛台,还有传统油灯。
即使都属于潮汕,不同村子的人婚嫁准备的物件也略有不同,有特别需要的,比如男女双方同岁需要准备的对笙,这些我们的妈妈都提前沟通过了。
两个红色的行李箱是我爸妈一起收的——我不能自己收,只好拿着相机咔咔拍下这个仪式。
我没有请摄影记录,但又很想记下这些一生一次的时刻,只能亲自“操刀”。

距离过门倒计时半天,心情平静。
晚上八点,妈妈开始张罗十二色花水给我洗澡,那感觉便是我真的要过门了。
加入十二种植物的洗澡水,好像童话里的某种魔法液体。
但真正的魔法师是帮我化过门妆的化妆师。
两个小时的漫长化妆过程,我变成了新娘的模样,镜子里是一张略显陌生的脸。
快十一点半的时候,按习俗,妈妈要来我的床上和我睡一会,这是唯一让我觉得比较温情的部分,可是为了保持我的发型,我躺着一动也不敢动,半个小时的时间脖子酸到哭。
妈妈似乎没什么想跟我说的,也可能是她太累了,很快睡着,而一心只惦记着妆发的我,也没有太多多愁善感的情绪。
快凌晨一点的时候,妈妈唤我吃饭,“米饭在饭锅里,要吃多少随便舀。我们不限制。”
按习俗,出嫁前的这一顿,女儿这碗饭只能吃一半,菜也都不能吃完,意思是不能把娘家的东西都带走。
饭桌上摆着四个“公鸡碗”:咸菜炒猪肚,韭菜炒猪肚,厚合炒猪粉,青蒜炒猪肝,每道菜都有寓意,每一样都要吃到。
按照传统,吃饭时该有“青娘”(指潮汕传统婚俗中,主持新娘出阁前拜别双亲直至到男家引新娘进洞房、为新娘牵被角等一系列仪式的角色)相伴念四句。
但现在即使在老家村镇里,也很少人请青娘了。
没有被计划什么传统仪式的我,就这样在一个奇怪的时间点,一个人背对着客厅,吃着奇怪的饭菜。
离愁别绪没有吃出来,只觉得咸菜猪肚挺好吃的。
“好了,可以过去了。”
爸妈和妹妹带着陈先生走进来,我站起来的时候还不忘让妹妹抓拍一张全身照。
我不知道这个第一面有没有让他惊喜。
甚至没有好好看他捧来的那束花,我就要出门了。
我一只手提着装了一把扇子、一株春草、一包种子的红色手提袋,掌心还捏着四颗“朱糖”(指剪成小小粒的“潮汕明糖”,寓意甜甜蜜蜜)一只手被爸爸牵着,他的动作很僵硬,提得很高,妈妈在身后喊,你们俩手放下来呀!我忍不住把我爸的手往下拽,“不要提这么高,不舒服”。
“我感觉你这鞋高,会走不稳啊。”爸爸挺委屈的。
我不屑地说这鞋一点也不高啊,但很快意识到,他可能很少看到我穿高跟鞋,以往都是在各式各样的场合穿,但自己如何优雅自信,来自爸妈的培育,却从未邀请他们验收。
走出大楼,爸爸要给我撑红色的伞,他老人家好像不太用得惯,也可能是紧张,折腾了好一会才撑开。
爸爸、一辆婚车、一位司机和陈先生,一个安静的交接仪式。
我上车后,眼睛扫到大门旁边的小区名,突然想起被叮嘱过不能辞别,不能回头看,刚想转动的脑袋不得不老实地面向前方。
一路静默,我隐隐感觉到,自己将被带入另一种全新的生活中去了。
这个念头让我有点难过——可惜我嫁得太近了,才十多分钟的路,情绪才刚起了涟漪,我们就到了。

从大门到客厅装扮了很多喜字和气球,径直走向婚房,坐在提前准备好的椅子上,和陈先生分吃了我捏了一路的朱糖后,他出去端姜薯甜汤,和我妈习惯用白砂糖不同的是:陈家是用红糖煮的。
我环视了一圈婚房,红到眩晕:红的气球,红的床单被单,床头点着红的灯,床位架子上也点着红的灯,床头柜上有两个红色搪瓷大脸盆,床中间放着刷了大红喜字的竹筛,里面又摆着一些我没有兴趣去搞清楚的红红的东西,无非是象征着百年好合和早日添丁的寓意吧。
吃完甜汤,我们坐了会儿,马上就要回门了,传统要三天甚至十二天完成的仪式,我们用一个时辰完成,真是刺激。
回门只有我和陈先生开车,气氛倒是轻松了不少。
提着一喜袋东西回娘家,又喝了碗甜汤,我便下楼了。
陈先生带着对耳环上楼去二回门,赶着吉时过之前回到婚房。
三天回门十二天回门的习俗,我们用最快的方式完成,新方式夹杂旧仪式,很多环节我都觉得挺滑稽,但实践起来还是虔诚而小心的。
忙碌一天直到凌晨一点,过门正日已过一个钟,我和陈先生躺在床上,他在打“吃鸡”,我在写每日书。
如果不是房间里到处都是大红的结婚物件,我真的恍惚这不过是一次日常的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