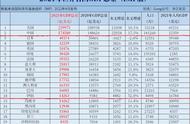北宋 王希孟 《千里江山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笃信道教的徽宗素来迷信天人感应之说,喜欢向群臣展示他表现祥瑞之兆的花鸟画,他借画作传递治国理念、震慑群臣的意图也不难理解。
南宋邓椿在《画继》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政和五年(1115),宋徽宗向赴宴群臣展示自己绘制的《龙翔池鸂鶒图》,群臣“皆起立环视,无不仰圣文,睹奎画,赞叹乎天下之至神至精也”。

宋徽宗
但宋徽宗没有想到,在《雪江归棹图》创作仅17年后,他自己以及大宋的半壁江山便全部陷落在金人手中。也正因此,后人在看此画时不免感慨。明代文坛领袖王世贞便在题跋中写道:“而帝以雪时避狄幸江南,虽黄麾紫仗斐亹于璚浪瑶岛中,而白羽旁舞,更有羡于一披蓑之渔翁,而不可得。又二年而北窜五国,大雪没驰足,缩身穹庐,与食毡子卿伍。”
此作既然是徽宗教导下所作,与他的审美追求必然有着巨大的联系,徽宗作为历史上有着极高造诣的文人画家,也崇信道教, 他通过王诜等受到此前北宋文人圈对书画创作的影响,以及“诗画同体”、 “无心” 的审美态度以及 “淡而无为” 的文艺观等, 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宋徽宗对欲进入翰林图画院的应试者有命题作画的习惯,尤其是爱出隐逸风格的诗句考学生的画意,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等,反映了他对文人隐逸生活的向往。
余辉先生曾称《千里江山图》或是描绘庐山大境,还包括长江口和部分鄱阳湖,与《千里江山图》卷画意最接近的是唐代孟浩然的五言山水诗《彭蠡湖中望庐山》,所谓“大湖中见高山,真成活画”,而诗中的“久欲追尚子,况兹怀远公”正表现的是一种隐逸与漫游的矛盾,“寄言岩栖者,毕趣当来同”则说出了归隐到底是最终目的所在。
作为帝王,徽宗又认为艺术的最终价值是为了弘道 、 育人 ,他对此有过不少论述,曾说 : “ 道虽不可以言传 , 然道非音声可求, 得之不离音声, 圣人不得已而 言者 , 以物固有所然 , 非言无自而显 , 必因言以 求理, 则各然于然矣。”而在《千里江山图》蔡京的一段题跋也验证了这样的观点。
蔡京题有:“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由画及人,通过对王希孟的培养成功,感慨天下之士也在于培养而方可作事成事,并未涉及此画的评价。

《千里江山图》卷末蔡京跋文
虽然此作符合徽宗的部分审美理念,但就宋代以来对于中国文人画的赏鉴最高标准而言,仍有不少差距。可以说,与徽宗的审美与艺术标准也是有较大差距的。
就文献而言,对于《千里江山图卷》,不仅蔡京主编、收录画作六千多轴的《宣和画谱》中未有记载,甚至连邓椿的《画继》中也未见相关记载,从蔡京的跋中也只是“上嘉之”,“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蔡京对这一画作自己未加评语,宋徽宗对此作也未像对于少年新进的画月季者“喜赐绯,褒锡甚宠”,蔡京所记的意思很清楚,徽宗虽然“嘉之”,但并未真正重视,既未题签,亦未命名,更未收藏宫中,而是顺手把此画赐于宠臣。
除了元代溥光在题跋中有赞语,从宋到清代之前,并无其他人加以夸赞。如果不考虑此作的真赝争议,或可说明此画只是部分符合了宋徽宗对绘画的要求,距离北宋绘画的高格或曰最高标准仍有较大差距。
同样是画作长卷,宋徽宗对于其后创作的《清明上河图》的满意显然溢于言表,定为“神品”,以瘦金书题签“清明上河图”并钤“双龙”藏印。相比《千里江山图》的待遇——只是“嘉之”,几乎是象征性的鼓励一下而已。
《清明上河图》与《千里江山图》,两幅宋代长卷画的待遇,宋徽宗的态度可谓天壤之别。

《清明上河图》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