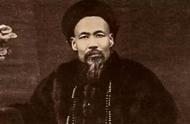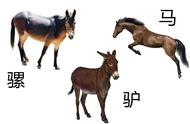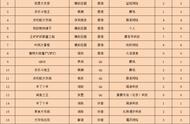图一二 战国秦汉时期中原出现的骆驼形象
1. 望山楚墓出土人骑骆驼铜灯 2. 东汉画像石中的骆驼
汉武帝大力开发西域以后,中原对骆驼就已经比较了解了。《盐铁论·本议》称:“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60]西域取代北方草原成为中原骆驼的主要输入地,但这一时期仍是依赖于进贡、征调、赏赐等官方的流通。如长沙杨家山304号汉墓出土一件漆器上有骆驼纹样的金箔贴花,年代约在西汉后期[61]。
骆驼作为装饰动物纹样出现在了高等级贵族所用器物上。骆驼还成为汉代官印纽制所用形象之一。据《汉官旧仪》载,诸侯王、御史大夫以及匈奴单于的官印以橐驼为印纽。在实际考古发现中也有不少驼纽官印的实例,多为汉朝对少数民族首领的颁赐印[62]。私印亦有用驼纽,如新和县玉奇喀特乡出土驼钮铜制“常宜之印” [63]。
到了东汉时期,中央对于西域的控制力有所衰弱,并最终于公元175年从西域撤军,史书中有“三通三绝”之称,彻底断绝了政治联系。然而,民间与西域却并未完全隔绝。中原普通民众对于骆驼的形象已越来越熟悉。东汉画像石中有大量的骆驼图像,常与胡人、大象伴生出现,均为西域远方的代表[64]。
(图一二,2)尼雅95MN1M3号墓葬出土女尸袍面所用人物禽兽纹锦,纹样有十几种动物和羽人形象,其中包括骆驼。同墓地M4出土两块残锦,装饰有骑马射猎双峰驼的场景。(图一三)这两件织锦都是典型的汉地舶来品,出现骆驼图像一方面可能是专为输入西域而专门设计,另一方面也说明骆驼已是织锦的习见纹样。

图一三 尼雅出土织锦上的骆驼纹饰
魏晋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活动逐渐兴盛起来,普通民众对于骆驼在沙漠交通中的独特地位有了比较准确的认识。《周书·异域传》载:“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风之欲至,唯老驼知之,即鸣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即将氈拥蔽鼻口。其风迅驶,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至危毙。”[65]
商旅的加入,使得诸绿洲之间的人员往来密度和频率进一步增加,对骆驼的需求量也随之加大。养殖骆驼在西域畜牧业中所占比例更重,这在尼雅出土的佉卢文书中有明确的体现:皇室有专门的驼队,配有专职看守人,还配备卫兵;各级政府机构均有专人负责骆驼事务;骆驼还可充当税收、作为交换货币以及供祭、礼物[66]。骆驼的养殖水平也相当发达,牡牝有严格区别,据推测早在西汉时期就采用了阉割技术[67]。
河西地区也是重要的骆驼养殖区,为汉武帝的历次用兵提供了大批骆驼。到魏晋时期,大量中原汉人迁入河西,成为丝绸之路继续延伸和发展的主力。他们与西域之间的交往,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骆驼。如《魏书·吕光传》载,前秦吕光讨伐西域返回时,“光以驼二千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
交通运输的需要极大推动了养驼业的发展,并体现在了这一时期河西的壁画墓中。如甘肃嘉峪关5号墓前室西壁第63号画像砖上出现了一大一小两峰骆驼吃树叶的场景,6号墓前室西壁第37号画像砖也表现了一名男子一手持长杆、一手牵骆驼的形象[68]。(图一四)高台骆驼城出土画像砖中也有放牧骆驼的图像。

图一四 河西魏晋壁画墓所见骆驼图像
值得注意的是,楼兰LE古城西北壁画墓的后室西壁,表现了一幅双驼互搏的场景,二驼两侧还各有一人手持长杆,试图将它们分开。(图一五)该墓葬前室发现有佉卢文题记,墓主人应是一位侨居楼兰的贵霜大月氏人,年代约在魏晋时期[69]。前述交河沟北的小月氏酋长墓曾出土骆驼纹金饰片,显示了月氏人对骆驼的喜爱。
西迁中亚的大月氏人还将骆驼铸在了自己发行的钱币上,特别是贵霜前三代王的钱币,骆驼是其背面最主要的装饰形象之一。(图一六,1)于阗模仿贵霜钱币铸造的汉佉二体钱,也直接照搬了这一形式[70]。(图一六,2)

图十五 楼兰壁画墓双驼互搏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