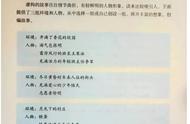【青春荟】
作者:森糖(北京大学艺术学院2020级本科生)
闹钟响起的时候天仍暗沉,玻璃上结了霜。隔壁的小男孩在喊:“妈妈,快看,下雪了!”
我用校服的袖子抹掉一片霜雾,便看到仍沉睡着的街道上的雪景。公交站牌旁的枯树一片素白,枝丫交错间露出路灯淡金色的光晕,金银交错。
我并不喜欢城市里的雪。
小时候,冬天经常下雪,远处烧锅炉的工厂还没有拆,烟囱里终日冒着烟。那时候的寒假还有大段大段的留白来给我挥霍,还没有做不完的题和令人忙乱的课外班。我总是在下雪的日子坐在楼外面的一截楼梯上,托着下巴看雪看烟。雪花轻盈地降临人世,青烟逐渐在长空里隐去身影——它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呢?那时候我隐约看到了这世界的玄妙。
有一天我在小雪中坐了一个下午,暗色开始从远处晕染过来,我在角落里堆了一个很小的雪人——城市里的雪太稀松零散了,团不起太大的雪球。我低着头看它,对它说:“我是一个人,你也是一个人。”我在它脸上画下笑脸的那一刻,眼泪莫名其妙地滑落进围巾,脸颊被风刮得生疼。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那种心脏空洞的感觉叫作孤独,就像暮色四合时角落里歪歪扭扭的小雪人。
第二天,雪已经化得干干净净,满地都是冰水混合物组成的黄褐色污泥,汽车轮胎的痕迹错综复杂地蔓延在地面上。我堆雪人的那个角落里什么也没有,除了一片泥印。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堆过雪人,因为我亲眼见证了我创造的雪人的死亡。那时候,在我眼中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所以我坚信雪人化掉的时候会很疼。我花了一个下午来哀悼我的雪人。
我不喜欢城市里的雪,因为它们在拥有短暂的美丽后总是化作污泥。我宁可轻盈洁白的精灵在落地的那一刻就消逝了,这也许是它们的幸运。
我仍是喜爱雪的。在雪山,我们住在木屋里,地板潮湿,放眼望向屋外,皆是起伏的纯白,洁净得让人自惭形秽。驻足远望,那纯净的色彩随着冷风一起洗净灵魂,过滤掉一切杂乱的心绪,正如雪地吸走所有的噪音。树木露出零星的褐色和深绿,每走一步都陷进一片温柔无声的松软。夜晚,我听着屋外雪融化的滴水声,整个人落入一片静谧空灵,我梦见精灵踏雪而来,清凉的星光落在发梢。那里的雪终年不化,它们让美好永生。那是仙境的雪。每每想起,我还能在记忆中的那一片寂静里回味屏住了呼吸的敬畏和惊叹……
雪可以是美好的,它可以存活,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也许雪的生命只有在安静的地方才得以存在吧,城市对它而言,太嘈杂、太忙碌了,人们过于夸张地迎接它的到来,又毫不在意地毁灭它。
擦开的霜雾已经重新聚拢了,隐约透着路灯浅金色的几团光晕。第二遍闹铃已经在响,我叼起面包的同时,把一沓厚重的书本塞进拉杆书包。
走到路口时我回头看,拉杆书包的轮子在雪地上留下了两条轨迹,看起来就像一个去往远方的旅人留下的痕迹。我想,等到高考完,去趟北欧吧,去看看那些被银白色覆盖的街头,走进那些挂着花环的咖啡厅,让咖啡杯上腾起的雾气与落地窗上的白霜重叠,我可以用手指画出自己的名字。
天已大亮,路灯倏地灭掉了,训练过似的,整齐划一。我拉起行李箱一样的书包,继续踩过这片雪地。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29日1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