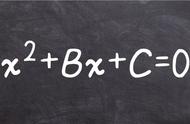后排左起:林云普,宋曼萍,黄江华前排左起:高娟英,徐文仙
回 家
作者:林云普
大概是从我下乡的第三个年头起,大学开始招生,企业开始招工。村里的下乡青年、回乡青年有的被招生上了大学,有的进城当上了吃商品粮的国家职工。尽管名额很少,但这已足以动摇绝大部分知青“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的信心。
与此同时,上海针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也悄悄开始松动。有病的可以办病退;老人身边无子女的允许一个子女回家;父母退休可以顶替工作;主动报名支援三线建设或者到上海郊区新建企业工作的职工,作为放弃上海市户口的代偿,允许一名下乡的子女招工同往。
政策一松动,家长们便开动脑筋,使尽千方百计把子女往南方挪动。符合政策的自不必说,用上海话讲叫“硬档”,不符合政策的则另辟蹊径。“路道”粗的托亲戚朋友把孩子调回南方某城落脚谋生,“路道”差一些的把孩子调回老家农村,希冀得到亲眷的照应。实在不行的,就在南方某地托人找个对象,把孩子嫁过去。总之,只想让子女不再在遥远的边疆“面朝土地背朝天”,只想子女离上海近一点,再近一点……

看着一起下乡的同学一个一个悄悄地离开,心里长草自不必说,夜半醒来满脑子胡思乱想。咱一不符合接班顶替政策,因为早在我下乡前父母就已退休;二不符合身边无子女条件,爹妈有姐照顾;三不符合病退,本人体格“杠杠”的,一般小病小灾撂不倒,还在女社员中评得大寨式工分最高分——八分,诸如铲地、割地的这些大田活计不输给男人;四不符合当兵条件,咱近视眼,再说,部队也没到俺们队上来招兵;五轮不到招工,在我离开农村之前,还没有上海知青被招工;六没有投亲门路,祖辈生活在苏州城里,没有乡下亲戚……想啊想,想到鸡鸣五更心烦意乱,就开始羡慕嫉妒恨。羡慕人家爹妈有本事,羡慕人家的父母年轻,怨恨自己“生不逢时”,甚至希望自己能得点什么病。越想越绝望,于是和小高同学相约,如果离不开农村,那咱也绝不在当地结婚嫁人。假如同学们都走光了,知青点撤了,我们就自己盖一座小土房,在那里相互照顾了此一生。
现在想起当时那绝望中的梦想不禁觉得好笑。其实,过着集体生活的知青,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我们不懂春耕、夏锄、秋收、冬藏的农活,没有东北农家扒炕、抹墙、挖窖、储菜等基本生活技能。两个女孩想要在那苦寒之地独立生活,简直是痴人说梦!说来也怪,在离开农村很多年以后,当时臆想中的那个小土房却常常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一个人的旅程
1972年末,大多数同学都回上海探亲了。我因为要给社员分红,再加上组织上要发展我入党,为接受考验,我留在了青年点。春节将临,家里突然来电报称“父亲病危”。亲情大于一切,于是我舍弃“进步”,踏上了回家路。
先坐马车到松树沟,再搭西岗子开过来的客车到黑河。老队长蒋维新为了让我尽快坐上火车,打电话给在黑河一粮店工作的亲戚,安排我在她家落脚,并托她给我找车去北安。晚饭,大婶给我烙了饼,还有炒土豆丝。夜里,我睡在她闺女的房间里。半夜,大婶叫醒了睡梦中的我,把我送上了一辆到北安拉货的卡车。

雪夜,提心吊胆地坐在颠簸的驾驶室里。不知司机何人,不敢搭话,人家问一句我答一句。司机觉得没趣,于是不再作声。半路,又有人送上来一个操着山东口音的男孩,司机让男孩坐在中间。男孩上来,驾驶室里多了个人,但大家还是没话。司机默默地开着车。那个山东男孩上来后,我的紧张心情似乎放松了些。车窗外,天空黑漆漆,大地白茫茫,分不清哪是道路哪是大地,车顺着车辙往前开。耳边只有轰鸣的马达声和汽车轮子碾压雪地的嘎嘎声。途中不知是何地,距公路不远的一处房子着火了,熊熊的大火映红了天空,映红了雪地……
第二天清早,车到达北安的一个货运处。我背着行李跳出驾驶室,着忙中把水壶拉在了车上,师傅拎起水壶带把水壶扔到了我脚下,我弯腰捡起水壶,谢过师傅,奔向火车站。那个山东男孩跟着我到售票处排队买票,我对男孩说:“你看行李,我去买票?”男孩摇头。我又说:“那我把钱给你,你去买票,我看行李?”男孩还是摇头。嗨!都说我有戒心,那男孩的戒心比我还强!我心想,你那破行李白给我都不要!有啥好防的?不过,俗话说“跑腿子行李,大姑娘腰——碰不得”。算了,也许人家的行李里装着钱呢。那就背着行李一起排队吧。当天我们上了火车,六七个小时后到达哈尔滨。那男孩还是不说话,于是大家各走各的。晚上,哈尔滨火车站候车室早就没有空座,我蜷缩着坐在行李上过夜,瞌睡中的大脑不断被睡熟得东倒西歪的身体惊醒。第二天凌晨排队签58次直快,座票已经没有只有站票,票价一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