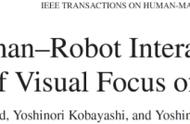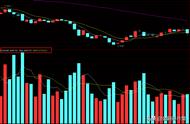基于本节考察,我们得到以下两点认识:第一,“娶”这个字是西汉末才开始行用起来的,此前记录{娶}时是不用“娶”的。第二,“娶”字甫一行用,后面就是不带直接宾语的。目前所见早期出土文献用例,都是如此。这为我们重新认识早期“娶”和“取”的字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参看下文第5节。
4►
出土文献中的“取(取妻)”
本节讨论出土文献中“取(取妻)”的分布情况和使用特点。“取妻”之“取”殷商卜辞已见行用。根据于省吾(1996:652),“取”字“卜辞之用法有三:一为凡取得之义,……;一为‘娶’,如‘乎取奠女子’(合二七六合集五三六);‘乎取女’(乙三一八六合集九七四一正),实则‘娶’为后起孳乳字,典籍亦用取为娶。卜辞‘取女’与‘取牛’‘取马’本无区分;一为祭名”。我们全面检查了目力所及的汉代及以前的出土文献,发现在记录{娶}时,西汉末期以前一直是“取”字一统天下,并不用“娶”[15]。下面作具体分析。
战国秦汉出土简帛文献中“取(取妻)”的使用和分布情况,如下表1所示。
与表1相同,上表区分N1(N范畴)、N2(N区别)、N3(N所自)三类名词性成分。取转 = 取转指,取者转 = 取者转指,代表“取”由动词转指娶妻之人。“所取”也是转指用法,即所取之人。括号内数字为有括号内字的格式的例数,括号外数字为无括号内字的格式的例数。如“取(以)为N1范畴”之下的张家山汉简“(4)”代表“取以为N1范畴”格式出现4例,“3”代表“取为N1范畴”格式出现3例。

表2:战国秦汉出土简帛文献“取(取妻)”的分布情况
上表统计数据显示:
第一,战国到秦汉的出土文献中,“取(取妻)”带直接宾语包括以下四类格式:“取N1范畴”“取N2区别”“取N1范畴(于)N3所自”“取N2区别(以)为N1范畴”。这四类格式的例数占总数的95%强(249/262)。据此可知,这期间“取(取妻)”表现出强烈的带对象宾语的倾向。
“取N1范畴”类用例甚多,占总数的84%(219/262)。也就是说,即便是像“妻”“女”“妇”这类范畴性语义的对象也不能省略,而一定要通过直接宾语表达出来。
“取N2区别”,9例。例如:
(26) 王或


(27)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简3背壹/164)
“取N1范畴(于)N3所自”之N3所自代表“取”之所自或所在,7例。例如: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