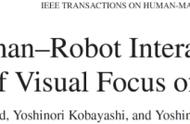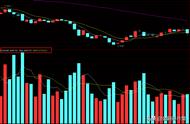(29) 家不居咸阳而取妻咸阳,及前取妻它县而后为吏焉,不用此令。(岳麓秦简四 336/0353)
“取N2区别(以)为N1范畴”,14例。例如:
(30)城父蘩阳士五(伍)枯取贾人子为妻。(里耶秦简 8-466)
(31)赏(倘)取婢及免婢以为妻。(肩水金关汉简一《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简73EJT1:2)
第二,“取(取妻)”后不带对象宾语(N1范畴或N2区别)的用例仅占总数的5%(13/262),可分以下两种情况。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情况均不改变“取(取妻)”的及物性。
1),“取(以)为N1范畴”,“取”后省略N2区别,但N2区别一定是前文出现过的信息,属于承前省略。例如:
(32)司马子反与


(33)阑曰:来送南而取为妻,非来诱也。(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简20)
例(32)对象宾语承前文“少”而省略。例(33)对象宾语承前文“南”而省略。
2),“取”发生名词化,转指娶妻之人,或用于“所取”等结构。例如:
(34)取人妻及亡人以为妻、及为亡人妻,取及所取,为谋(媒)者,智(知)其请(情),皆黥以为城旦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简168)
(35)夫生而自嫁、及取者,皆黥为城旦舂。夫死而妻自嫁、取者毋罪。(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简192)
综上,从出土文献来看,西汉末期以前,“取(取妻)”后一直是倾向于带对象宾语的,是典型的及物动词;不带宾语的情况都是有条件的,并不改变动词“取(取妻)”的及物性。
5►
讨论
5.1 重估上古汉语{娶}的及物性与综合性
承前所述,对于上古汉语{娶}的特点,前贤已经多有抉发。关于及物性,李佐丰(2004:103–104)指出,上古汉语有些“具有不及物动词某些特点”的及物动词,即准他动词,其中第三类是“不带宾语和带直接宾语都很常见,甚至不带宾语更常见。这样的动词常用的有:娶”等。关于综合性,胡敕瑞(2005:8–9)指出,上古汉语{娶}的对象是隐含在动作中表达的。蒋绍愚(2021:3)指出,“在《左传》中还有一类动词,不完全是综合性动词,但经常表现出综合性的特点”,最常见的有{娶}等;其综合性表现在,“动作对象经常是不出现的,但它们作为语义构成要素包含在动词之中”;更甚者,“在‘娶(取)于 地名’的句子中(《左传》共14例[18]),‘妻’一定不出现”。“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上古汉语的动词有综合性的特点”。
根据本文的考察,以上论断需作进一步深化。从传世文献看,上古{娶}写作“取”时是典型的及物动词或分析性动词,几乎没有不及物或综合性动词的用例;写作“娶”时,不及物或综合性用法集中体现在“娶 于N3所自”这一种格式上,其他格式中罕见。从出土文献看,在殷商至西汉末很长一段时期里,{娶}(只写作“取”)的动作对象一直是倾向于通过直接宾语专门表达的,并未隐含或综合在动词之中。由表2数据可知,不只是概念相对具体、承担区别功能的对象N区别(褒人之女、织女、它国人),概念相对概括、没有区别功能的对象N范畴(妻、女、妇)也要通过直接宾语单独表达。只有少量不带宾语的例子,但基本上都是可以解释的。由此可见,这期间“取(取妻)”一直是典型的及物动词或分析性动词,不应列入准他动词或综合性动词。而且,在要求带宾语这一点上,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的“取”是高度一致的。“娶”则晚至西汉末期才开始出现,而且一出现就是不带宾语的,最早的9个例子均是如此。因此,出土文献中,不及物或综合性动词用法主要体现在西汉末始见行用的“娶”上。
5.2 及物性与综合性的关联
及物性与综合性可以说是从各有侧重又紧密关联的两个角度对{娶}进行的观察。前者侧重句法行为,后者侧重概念或语义表达。那么,二者之间的关联体现在哪里呢?根据本文的分析,正是体现在N1范畴作被娶者这种情况上。作为及物动词的{娶},所带宾语既包括N区别(如褒人之女),也包括N范畴(如妻);而其不及物动词的用法(写作“娶”),基本都是N范畴作对象宾语但不出现的情况。例如,传世文献“娶 于N3所自”格式(及其他零星用例)和早期出土文献的9例“娶”,都是N范畴作对象宾语没有出现的情况。当N区别作对象宾语时,仍要实现为及物动词(写作“取”)。动词{娶}的综合性用法(写作“娶”),综合(或隐含)到动词中表达的对象基本也都是N范畴。当涉及的是具有区别功能的动作对象时,仍要通过N区别专门表达。
上古汉语有一批“对象自足”的综合性动词,根据本文的分析,其实质跟“娶”相似,都是将属于范畴义的动作对象综合到动词的词汇语义之中,如“盥、沬、聚、牧、沐、洗、引”等。其所表示的意义,汉代以后逐渐倾向于通过动宾结构表达,如“洗手、洗面/脸、聚众、牧牛/羊/马、洗头/沐发、洗足/脚、开弓”。(王力,1941/2005:391;蒋绍愚,1989/2005:229;杨荣祥,2005:53)
5.3 “娶”与“取(取妻)”的字际关系
胡敕瑞(2005:8–9)指出,“如果把偏旁表意也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呈现’,那么像‘娶妻’……可以说经历了二度‘呈现’,第一次是从‘取’到‘娶’,……第二次是从‘娶’到‘娶妻’。”即是说,上古对象隐含在动词“取”中,后来对象逐次呈现,第一次是通过文字构造上添加意符“女”呈现([VP 取]→[VP 娶]),第二次是通过句法上添加“妻”呈现([VP 娶]→[VP 娶妻])。传世文献历经多次钞刻,我们无从确知原貌。出土文献可以弥补这一缺憾,而从出土文献来看,该论断是缺乏根据的。因为如前所述,在西汉末以前的很长时期内,记录{娶}这个词的字只用“取”,不用“娶”,而且,其动作对象通常是通过直接宾语专门表达的,即便是在传世早期文献中,用“取”记录{娶}时,也是如此;反倒是“娶”字,自西汉末期一出现就是不带对象宾语的。据此,“娶”的“二度呈现”就不成立了。
对出土文献的考察显示,“娶”应该是西汉末出现、专门用来记录“{娶} N范畴”的一个字,其词汇语义中包含了动作和关涉的对象N范畴两部分信息,以与其他一般“取得”义的“取”相区别。这样看来,《说文》用“取妇”来训释“娶”,是相当准确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传世上古典籍中“取”“娶”共现的情形,极有可能是西汉末期以后不断“当代化”的结果,即是说,其中的“娶”很可能是后人改动使然。[19]因此,我们在利用《左传》《论语》等传世文献语料时,需作审慎处理。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经典多叚取为娶。”于省吾(1996:652)说:“‘娶’为后起孳乳字,典籍亦用取为娶。”就产生先后而论,先有“取”后有“娶”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娶”和“取(取妻)”在其所记录的词的层面,是不是等同的?从出土文献来看,答案是否定的。词是特定语音、语义、语法乃至语篇语用等信息的交汇,从句法上的及物性和词义上的综合性来说,“娶”和“取(取妻)”是有着显著区别的。“取(取妻)”是典型的及物或分析性动词,而“娶”自西汉末期一出现就是不带宾语的,是不及物或综合性动词(就N范畴而言)。因此,我们在考察以往所说的孳乳字、古今字等字际关系时,不应只是关注基本词义,还应将词的语法等层面信息纳入考察视野。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从语言的层面全面立体地展示字际关系。
6►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在以下三方面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第一,结合出土文献的考察,深化了对上古汉语动词{娶}的及物性与综合性的认识。结合出土文献来看,在殷商至西汉末很长一段时期里,{娶}只写作“取”,且一直是典型的及物动词,并非准他动词或综合性动词;写作“娶”则是晚至西汉末才开始出现的,并且一出现就作不及物动词。第二,区分了N范畴和N区别这两类名词性成分。这一区分不仅有助于准确揭示{娶}的及物性与综合性之间的关联,对于准确刻画以往所说的对象自足动词,也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从及物性的角度辨析了“娶”和“取(取妻)”的字际关系,强调在考察以往所说的孳乳字、古今字等字际关系时,不应只是关注基本词义,还应将词的语法等层面信息纳入考察视野。
最后对{娶}的读音问题稍作讨论。在《经典释文》中,“娶/取(取妻)”大多专门出注,标为去声(七住反、七喻反、取注反),以与读上声、“取得”义的“取”相区别。孙玉文(2015:394–397)等对此有专论。这一读音上的区别何时产生?“娶”与“取(取妻)”除综合性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语义之别?这些问题是重要的,但与本文主旨关系不甚密切,故暂不讨论。
向上滑动查阅注释
[1] “娶”在传世早期文献中又写作“取”。古代学者已对此有所揭明,《白虎通义·嫁娶》“娶者,取也”,[清]陈立疏证:“古多假取为娶。”(陈立,1994:491)《说文解字》“娶”,[清]段玉裁注:“经典多叚取为娶。”为了避免称述上字与词的混淆,行文以“{娶}”代表“娶妻”之“娶”这个词,“娶”代表以“娶”记录{娶}这个词,“取(取妻)”代表以“取”记录{娶}这个词。
[2] 姜雯洁(2013:192)列出的唯一1例不带宾语的“取”出自《论语·述而》“君取于吴”。据李方(1998:272),伯二六九九号、伯三一九四号、伯三七〇五号、伯二五一〇号郑本、郑卯本、伯三七八三号白文、篁墩本、皇本皆作“娶”。伯三五三四号、邢本“娶”作“取”。《释文》出“娶”,云:“本今作‘取’。”
[3] 例如,姜文将“季文子聘于陈,且娶焉。”(《左传·文公六年》)和“不可娶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等同视为“‘娶’后接助词位于句尾”的情况,显然是不准确的。
[4] 李佐丰(2003:79)认为,上古汉语“取妇”都是娶儿媳妇。但从本文调查的出土文献来看,“妇”不限于儿媳妇,“取妻”也可以称“取妇”。
[5] 关于范畴性语义和区别性语义的区分,参看史文磊(2021:18–19)。
[6] 历代不同版本“娶/取”的写法或有出入。“娶”或作“取”3例:《僖公五年》“娶焉”,《经典释文》作“取”,曰:“本又作娶。”《哀公十二年》“昭公娶于吴”,《经典释文》作“取”,曰:“本亦作娶。”《襄公二十六年》“椒举娶于申公子牟”,《经典释文》作“娶”,曰:“本又作取。”“取”或作“娶”2例:《昭公二十八年》“不敢取”,《经典释文汇校》:“写本取作娶。”《襄公二十五年》“使偃取之”,《经典释文》作“取”,曰:“注本或作娶字。”总体而言,这几条异文不影响“娶”“取”分布的整体格局。
[7] 《国语·越语上》:“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这是“娶”见于非“娶于N3所自”且不带宾语的例子。传世上古文献所见不多,且是被娶者为N范畴的情况。参看下文第5.2节。
[8] 不同版本存在少许异文,参看黄焯(2006)、袁梅(2013)、李方(1998)等。总体情况与《左传》相似,这些异文并不影响“娶”“取”分布的整体格局。
[9] 甲骨学者均明知此点,只是处理方式上略有差异。有的为方便计,姑且作为《说文》“娶”字的对应字形,如刘钊(2014:688);有的特意隶定作“娵”,以与后世的“娶”相别,如李宗焜(2012:167);当然,其与后世的“娵”也仅是同形字关系而已。殷商卜辞仅此一见。出土战国文献未见“娶”字(曾宪通、陈伟武,2019)。
[10] 《慧琳音义》卷九十八“孟娵”注引王逸注《楚辞》曰:“娵,美也。”《慧琳音义》卷八十六“孟娵”注引《考声》曰:“娵,美女也。”(《故训汇纂》“娵”引)
[11] 参看刘大雄、何玉龙(2020)的综述。
[12] 《汉语大字典》“娵”字未列作为“娶”的异体字用法,可补。
[13] 根据张德芳(2016:439)“今按”,“该简册属于应书,是甲渠候官在接到上级转发的朝廷有关禁止嫁娶逾制、反对铺张浪费的诏书后,自查本部具体情况后所作的汇报文书”。
[14] 其中“取直为妇”(EPT59:306)这一例,图版字形很模糊,所以没有列出,但可肯定不作“娶”。
[15]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西汉末期以后,“取(取妻)”也一直在用。东汉的五一广场汉简(壹、贰)即用“取”不用“娶”(“娉取缣为妻”),甚至敦煌变文写本中仍有不少写作“取”的(姜雯洁,2013)。本文重点考察上古汉语的情况,这个问题暂不涉及。
[16] 清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至七册);上博=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楚帛=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包山=包山楚简;九店=九店楚简;睡虎=睡虎地秦简牍;里耶=里耶秦简;岳麓=岳麓秦简(第一至四册);周家=周家台秦简;王家=王家台秦简;放马=放马滩秦简;居新=居延新简;张家=张家山汉简;马王=马王堆汉简;孔家=孔家坡汉简;银雀=银雀山汉简;肩水=肩水金关汉简;武威=武威汉简;尹湾=尹湾汉简;阜阳=阜阳汉简(周易);东牌=长沙东牌楼汉简;五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一、二)。
[17] 个别释文有不同意见,但对本文所论没有影响,故仍据整理本。
[18] 根据笔者的统计结果,《左传》中“娶(取)于 地名”格式有18例。
[19] 这一段论述吸收了匿审专家的意见。谨致谢忱!

上下拉动翻看引用书目和参考文献
引用书目:
[唐]陆德明(撰),黄焯(汇校),黄延祖(重辑)《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2006年版;[清]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编)《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一、二)》,中西书局2018年版;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四)》,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武汉大学出版2016年版;陈伟等(著)《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一)》,中西书局2011年版;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武威汉简》,中华书局2005年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上)》,中华书局1994年版;湖北省文物考古所、随州市考古队(编)《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一〕》,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至七)》,中西书局2010年至2017年版;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至2012年版;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一、二)》,文物出版社1985年、2010年版;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一至三)》,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至2013年版。
参考文献:
白于蓝 2017 《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福建人民出版社。
陈 伟(主编) 2012 《里耶秦简牍校释》,武汉大学出版社。
高 亨(纂著) 董治安(整理) 1989 《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
韩自强 2004 《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侯瑞华 2020 《论〈离*〉的“女嬃”与清华简的“有嬃女”》,《古籍研究》(第71卷),凤凰出版社。
胡敕瑞 2005 《从隐含到呈现(上)》,《语言学论丛》(第31辑),商务印书馆。
湖南省博物馆等 1973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
姜雯洁 2013 《汉语动词“娶”、“取(娶)”关涉对象隐现情况的历时考察》,《励耘学刊(语言卷)》第1期。
蒋绍愚 1989 《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05年增订本。
蒋绍愚 2021 《再谈“从综合到分析”》,《语文研究》第1期。
李 方 1998 《敦煌〈论语集解〉校证》,江苏古籍出版社。
李 零 2017 《子弹库帛书》,文物出版社。
李宗焜 2012 《甲骨文字编》,中华书局。
李佐丰 2003 《试谈汉语历史词义的系统分析法》,《语言学论丛》(第28辑),商务印书馆。
李佐丰 2004 《古代汉语语法学》,商务印书馆。
刘大雄、何玉龙 2020 《武威汉简〈仪礼〉年代问题补说——甲本的抄写年代及相关问题研究》,《简帛》第2期。
刘信芳 2011 《楚简帛通假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
刘 钊(主编) 2014 《新甲骨文编(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
毛远明 2014 《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中华书局。
裘锡圭(主编) 2014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华书局。
史文磊 2021 《汉语历史语法》,中西书局。
孙玉文 2015 《汉语变调构词考辨》,商务印书馆。
唐 兰 1980 《长沙马王堆汉轪侯妻辛追墓出土随葬遣策考释》,《文史》(第10辑),中华书局。
王 辉 2008 《古文字通假字典》,中华书局。
王 力 1941 《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国文月刊》第4期,1941年7月。收入《王力全集》第19卷《龙虫并雕斋文集(一)》,中华书局2015年,第390–395页。
王立军 2020 《汉碑文字通释》,中华书局。
谢维维 2021 《〈经典释文〉“取”字音义关系考辨》,《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徐玉立 2006 《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
徐中舒(主编) 1989 《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
杨伯峻 1981 《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三版。
杨荣祥 2005 《语义特征分析在语法史研究中的作用——“V1 V2 O”向“V C O”演变再探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于省吾(编) 1996 《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
袁 梅 2013 《诗经异文汇考辨证》,齐鲁书社。
曾宪通、陈伟武(主编) 2019 《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中华书局。
张德芳(主编) 孙占宇(著) 2013 《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
张德芳(主编) 2016 《居延新简集释》(全七册),甘肃文化出版社。
周 宇 2002 《从〈甲渠言部吏毋嫁聚过令者〉文书看汉代社会中的婚俗奢靡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
Hopper, Paul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Language, Vol.56 (2): 251–299.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