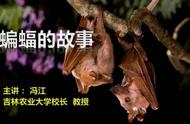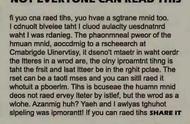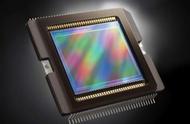预警雷达(图片来源网络)
或许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人类的雷达研发历史不足百年,而和雷达相似原理的回声定位却被蝙蝠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改善并使用了约6500万年。
当我们绞尽脑汁尝试着提高自己雷达的探测距离、追踪精度的时候,又纠结于如何避免自己的装备被对方的雷达系统探测到。这样的军事装备竞赛自雷达的研发开始持续如今。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军事装备竞赛却与蝙蝠和猎物的“捕食与反捕食”装备竞赛出奇的相似:作为狩猎者的蝙蝠,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不停地完善着其回声定位系统的性能;作为猎物的昆虫,同样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不停地提升着其反捕食的技能。这也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军方每年都会资助蝙蝠的生物学研究。

蝙蝠和雷达感受器(图片来自网络)
七、蝙蝠是破解人类语言脑机制的哺乳动物模型
语言是人类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在促进人类进化与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语言如何演化而来?语言控制和学习的脑机制是什么?这些重大问题仍不清楚。
多年来,鸣禽(songbird)是研究语言最主要的动物模型,但缺少与人类亲缘关系更近的哺乳动物模型。而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蝙蝠有望成为科学家研究脑机制的哺乳动物模型之一。
众所周知,人类的语言是后天学习而来的,这种能力称为发声学习。然而,发声学习能力在哺乳动物中却是十分罕见的。目前被证实的具有发声学习能力的哺乳动物仅仅包括蝙蝠、大象以及海豚等少数哺乳动物。
显而易见,由于体型、物种多样性和个体数量等方面的限制,相对于大象和海豚而言,蝙蝠是更为理想的实验动物。蝙蝠物种多样性高,许多蝙蝠种类高度群居,具有复杂的社会结构,而高度的社会性是促进语言进化的关键因素之一。
此外,与绝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同的是,回声定位蝙蝠具有极高的发声活跃性(每秒的发声数量从几个到上百个不等),为研究发声控制的脑机制提供了便利的行为模式。或许正是由于蝙蝠在研究声音通讯和导航方面的独特优势,蝙蝠发声控制和学习的研究是动物声音通讯研究的主要模式物种之一,也成为破解人类语言脑机制的希望。

蝙蝠的发声控制和学习(图片来自罗金红)
八、蝙蝠帮助揭开人和动物大脑方位感知和空间导航的秘密
当我们走出家门,到附近的公园或者商场逛逛后,总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回家的路。在这个大家习以为常的过程中,我们的大脑提供了大量极其精确的导航信息。比如,从商场门口需要前行多少距离达到下一个路口,然后再左转或者右行等等。
那么,我们的大脑如何知道这些位置、距离以及方向信息的呢?针对这些问题,英国的O’Keefe教授和他的博士后学生Moser夫妇等科学家做出了一些列出色的工作。他们发现,在大鼠大脑的海马体及其邻近的邻脑区——内嗅皮质发现了处理位置信息的“位置细胞”、处理距离信息的“网格细胞”以及处理方向信息的“头朝向细胞”等导航细胞,形成了大脑中的“GPS”。O’Keefe教授和Moser夫妇也因此共享了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然而,这些发现都是在二维(2D)空间中获得,在更为真实的3D环境下情况又是如何呢?这时,就无法再以常规的动物模型小鼠或大鼠作为实验对象了。科学家们想到了生活在3D空间中,唯一能够飞行的哺乳动物——蝙蝠,并以蝙蝠为实验对象,做出了大量出色的工作。
研究发现,在3D空间中,蝙蝠海马体中的位置细胞处理垂直和水平方向信息表现出各向同性;前海马回的细胞能够对其头朝向的3个欧拉角(水平方位角、俯仰角和翻滚角)连续表征,实现3D空间的方向信息的精确获取。
当从一个环境中来到另一个环境中,我们大脑中的“GPS”需要进行重置,以适应新环境下的导航需求。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是,我们大脑中“GPS”多久能够重置1次呢?先前研究显示这个时间尺度大概在1分钟左右。
然而,利用蝙蝠回声定位高时间精度的特点,研究人员发现“GPS”重置的时间在300毫秒左右,大大刷新了人们的认识。部分种类的蝙蝠兼有视觉和回声定位的能力,研究人员利用这一特点,比较了视觉线索和听觉线索下位置细胞处理位置信息的能力。结果显示,视觉线索下,位置细胞的空间分辨率更高。
此外,研究还发现,蝙蝠海马体中存在识别其它蝙蝠位置的“社交位置细胞”。虽然大脑导航的机制已经逐渐清晰,但仍有大量空间导航的问题仍待回答。例如,上述导航细胞所在的脑区之间如何相互协作完成导航任务?
目前的研究都是在实验室环境,空间极其有限,那么在真实自然环境中、大空间尺度下的导航有何不同?等等。不难想象,利用蝙蝠众多物种特异性的迷人特征,大脑在3D空间中的导航秘密将不断被破解!

蝙蝠的三维空间导航(图片来自网络)
八、蝙蝠是维持生态系统健康不可缺少的动物类群
长期以来,蝙蝠在害虫控制、种子传播、植物授粉以及森林演替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不同的蝙蝠物种表现出食虫、食果、食蜜、食鱼、食肉甚至食血等多种多样的食性,但超过三分之二的蝙蝠专性或兼性地以昆虫为食。
在生态系统中,蝙蝠是夜行性昆虫的主要控制者,每晚可以捕食大量的昆虫。据估计,圈养的蝙蝠每天消耗的昆虫约占其体重的四分之一;但在野外条件和哺乳期等高能耗时期,这个数字可高达70%,有时甚至能超过100%。
蝙蝠经常出没于农田,通常在农田里伺机捕食许多潜在的农业害虫。研究表明,巴西犬吻蝠(Tadarida brasiliensis)会伺机捕食多种与农业相关的害虫。此外,由于多种主要的农业害虫具有迁徙行为,因此蝙蝠赋予农业的价值可能会扩展到数百公里以外的其它农业区域,而不仅仅局限于蝙蝠在当地的觅食区域。
研究表明,蝙蝠在农田中的捕食行为极为出色。Cleveland等人的研究评估了巴西犬吻蝠为德克萨斯州中南部棉花生产提供的害虫抑制服务的经济价值,结果表明,每年蝙蝠通过捕食害虫而避免棉花受损以及避免使用*虫剂的价值为74万美元,占棉花最终产量价值的15%。
仅在北美地区,蝙蝠通过减少作物损害和避免使用*虫剂的价值约为229亿美元/年。在泰国,蝙蝠每年在稻田中通过捕食害虫可防止稻米损失近2900吨,产生的经济价值超过120万美元,意味着泰国的蝙蝠每年能够为近3万人提供口粮。
此外,研究人员通过对玉米田的大规模围网实验,发现蝙蝠对作物害虫施加了足够的压力,在抑制玉米害虫的幼虫密度和危害的同时,能够降低玉米中与虫害相关的真菌生长和真菌毒素,保守估计在全球范围内,仅在玉米种植中,食虫蝙蝠通过对害虫的抑制产生的价值超过10亿美元,而蝙蝠可通过间接抑制与虫害相关的真菌生长和玉米上的有毒化合物而进一步造福人类。
很多情况下,许多农业害虫的幼虫能对作物造成损害,而蝙蝠能够对害虫的成虫进行捕食,从而阻止了成虫的产卵,进而减少幼虫的发育。因此,蝙蝠对害虫的捕食可能会对农业生态系统产生级联效应。
传统研究蝙蝠食性的方法是,对蝙蝠粪便中食物残渣进行形态学分析;该方法存在较大的局限性,阻碍了对蝙蝠食性的研究。随着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如DNA条形码(DNA metabarcoding)和环境DNA(environmental DNA, e-DNA)分析,使我们对蝙蝠捕食害虫的生态服务有了新的认识。
Aizpurua等人(2018)通过e-DNA分析法,对全欧洲范围内普通长翼蝠(Miniopterus schreibersii)的食性进行研究,发现普通长翼蝠能捕食超过200种节肢动物,其中包括44种农业害虫,这些害虫可以危害欧洲大陆的许多作物,且普通长翼蝠可根据当地农田中可利用食物资源调整食性,重塑其食性生态位。由此可见,长期以来,蝙蝠对农业害虫的抑制作用严重被低估。
此外,蝙蝠还可以通过授粉和传播多种植物种子,提供关键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关于榴莲的传粉生态研究表明,虽然大蜜蜂(Apis dorsata)是榴莲最频繁的访花动物,但果蝠,尤其是长舌果蝠(Eonycteris spelaea)是榴莲的主要传粉者,以每晚平均26次的频率访花。
在热带地区,由于狐蝠体积大、流动性强,故而成为高效的传粉者和种子传播者,许多狐蝠每晚从栖息地到觅食地的飞行距离超过60公里。蝙蝠塑造了森林群落的多样性和物理结构,从而使得森林中许多动植物得以生存。
自然界中,多种植物不同程度的依赖于蝙蝠进行繁殖,其中包括多种经济作物,如香蕉、芒果和番石榴等。在岛屿上,进化的偶然性和人为导致的当地其它种子传播者的灭绝,意味着狐蝠成为授粉或传播种子的唯一媒介。因此,狐蝠是当地或岛屿特有的维持植物生存能力的关键物种。岛屿上狐蝠的灭绝可能会引发连锁灭绝,从而导致不可挽回的生态和经济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