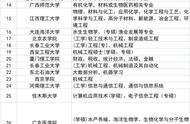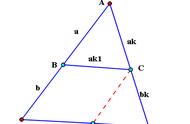悬泉置遗址,这是一处风蚀严重的垃圾堆积,这种松散的人为堆积一般无水平层位可言,加上自然营力扰动严重,极有可能把不同时代的东西混在一起
功能与社会背景
研究纸史一定要给纸赋以一种功能的定义,即一些原始的类纸物,如果不是专门用于书写,则不应该从造纸术的发明来考虑。其他包装物和人工加工的纸状物,如果不是用于书写目的,也不能从书写载体的发明和创造来考虑。从世界上大部分发明创造来看,20世纪以前多为个人努力的成果。只是到了20世纪工业化的充分发展,才使政府和商业机构成为一些重大发明的主要支持者和赞助人。
对于纸张的发明,根据文献线索,它是因东汉统治者深感“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于是作为宦官的蔡伦为了迎合上层贵族的喜好而发明了造纸术。《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第六十八蔡伦本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行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因此,蔡伦尝试造纸的发明行为可以看作是政府支持下的一种创新工程。
发明与发现不同,后者常有一定的偶然性,而前者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需要,而且往往与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发展的复杂程度密切相关。最早公开宣布西汉有纸的科技史学者自己既非考古学家,也非造纸专家。他在根据灞桥汉墓的发掘简报,提出西汉有纸的观点时,将造纸术的发明归功于西汉的劳动人民,有意贬低蔡伦,其动机和目的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从社会与科学技术发展的相互关系来看,对纸需求的主要阶层恐怕不是普通的下层百姓,而是政府部门和知识界,所以纸取代简帛的主要社会动力应当来自于上层建筑。对于这点,后世文献也有探讨,比如清代何绍基在《东洲草堂文钞》卷十九《纸赋》里提及:“岂云智者创而巧述之,无如上有好而下甚焉”。认为正是朝廷对书写材料有所好,才推动了蔡伦发明纸张以满足贵族阶层的需求。这和过去大力宣传造纸术是西汉劳动人民的发明有明显的抵牾:广大劳动人民可能连字都不识,哪会有发明纸张的动机和念头?
从史前期以及历史时期的重大科技发明来看,一种新发明从诞生到普及应用之间往往有一个漫长的滞留阶段,而且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关系密切。最明显的例子是火药,它在中国发明后的漫长岁月中主要被用来制造烟火,但是它在传到欧洲后却被用来生产枪炮。这是因为在传统和常规的生产基础上补充一种新技术与建立一种全新的工艺技术,在经济和生产结构上完全不同。它不但涉及到原料的开采和供应、劳力投资、设备、市场需求和贸易规模等社会机能的完善,而且还涉及到工匠的充分培训和能动性提高。所以,有些重大发明在我们现代人眼里看来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经济潜力,但是在原始条件下,它的采纳和普及可能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从而常常窒息和延缓了它的采纳和普及。
造纸术与简帛生产属于完全不同的生产工艺,所以造纸术在发明初期所需投入的代价未必一定比生产简帛便宜。这一发明初期所显示出来的优点,可能主要体现在它质地上的潜力。对于造纸术这种需要相当资金和劳力投入的发明,一般来说也只有那些具有一定地位、经济实力和劳力调遣能力的上层人物才可能予以尝试。而且在没有任何成效可以预见的情况下,要使为糊口而操劳的普通百姓自发从事这种尝试,可能是一种相当不现实的推断。蔡伦身处统治阶层,对纸的作用和意义应比一般人有更深刻的认识与体会,更何况发明造纸术在一定程度上是秉承了皇帝旨意所进行的一项创新工程。
当时,蔡伦的官职已经做到了尚方令,这是一个主管皇宫制造业的机构,主管监督制造宫中用的各种器物。他管辖当时的皇宫作坊,集中了天下的能工巧匠,代表那个时代制造业最高水准。这就为蔡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他的个性、爱好以及他在工程技术方面的过人天资,使得造纸术成为他在这个岗位上的集中展现。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向汉和帝献纸,蔡伦将造纸的方法写成奏折,连同纸张呈献皇帝,得到皇帝的赞赏,便诏令天下朝廷内外使用并推广,朝廷各官署、全国各地都视作奇迹。九年后,蔡伦被封为“龙亭侯”,表明朝廷对蔡伦重大发明和杰出贡献的肯定和嘉奖。。
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下造纸术的应用和普及问题。纸张这种用品的需求主要是政府机构和知识界,最初使用的应当是相当有限的一小部分人如当时的统治阶层。可以想象,在纸张发明的初期,它应是一种颇为珍稀之物。只有当造纸技术改进,使纸张能成批生产,并且成本大大下降之后,才有可能被普及到基层供一般老百姓使用。目前主要的所谓“西汉纸”多出土于边疆地区或下层人物的墓葬,这是一个颇令人怀疑的现象:为什么当时在朝廷或统治阶层尚未使用的东西会在人烟稀少的边疆地区和下层百姓使用?如果在甘肃悬泉置这样的边陲,纸张在西汉已作为平时公文用品却不见于首都和朝廷,似乎不合情理。
小 结
像造纸术这种重大的发明事件如果真的发生于西汉,史藉应不会不予以记载。蔡伦的造纸术受到当时皇帝和朝廷的高度评价,被誉为“蔡侯纸”,就是官方的正式肯定。如果西汉已经能够造纸,而且已被广泛使用,朝廷未必会对蔡伦有如此高的评价和嘉奖。
造纸术的发明是一桩划时代的变革,它的应用必然会影响到当时社会上层建筑的各个层面。从某种程度上说,纸的发明最大的得益者不是劳动人民,而是统治阶层和知识界。所以,对于这样重要的事件,西汉的官方记载和知识分子在文字记载上不留一点笔墨是难以令人置信的,特别是当他们日常使用的简帛被纸张所取代时,不会不留下一些述评和感想。所以,像造纸术发明这样的问题,从历史考古学的角度来说,可以认为历史记载要比一些可疑的考古现象更为可信。换言之,就目前对“西汉纸”所做的科技鉴定结果表明,这些发现不足以动摇史籍记载的可靠性。有些学者坚持这类颇为可疑的考古发现来修改历史,否定蔡伦的地位是不可取的。“需要是发明之母”,从需要来说,古代劳动人民可能识字的不多,基本生计的操劳使他们对书写物品的需求和关切也不会很大。即使有些平民有这样的想法和愿望,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很难使这样的愿望变成现实。造纸术的诞生应被视为当时政治、经济 和文化发展推动下的产物。社会的发展促使具有一定地位的上层人物意识到书写材料变革的意义,并正好允许蔡伦能运用他的智慧、地位和权力来从事这样的尝试,并投入相当大的财力和人力,经过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才获得成功。
在造纸术发明后的相当长时间里,纸仍是一种难以推广和普及的用品。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具体事实来看,简帛向纸张的过渡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地方文书到汉末乃至三国两晋仍为简牍,如《后汉书》《儒林列传》第六十九记载“及董卓移都之际...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王所允面西者,载七十余乘”,说明东汉皇室藏书主要以帛书为主。而长沙走马楼出土十万枚东吴账册简牍表明,三国时期的普通书写材料仍然是竹简。到蔡伦发明纸张后约三百年的东晋,书写载体的新旧交替才以官方禁令取缔方式而告终结。这就是北宋李昉等辑《太平御览》卷六百五著录《桓玄伪事》提及的:“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由此可见,纸取代简帛的过程取决于造纸术的改进,只有当造纸工艺改善到一定阶段,使得纸张成本大为下降而可以成批生产之后,才能成为最普通的书写用品。从目前几处出土的所谓西汉纸遗址的整体背景判断,特别是从它们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阶层来看,应当说尚不具备使用纸张书写的条件和资格。换言之,如果像灞桥汉墓、放马滩汉墓和悬泉置这样层次较低的人士和帝国边陲的哨所或驿站在西汉已能用纸作为日常的书写载体,那么纸在当时应早已成为朝野比较普及的用品了,然而这岂不与三国时期仍大量用简的事实相矛盾?
最后,从考古学发展的现状来说,科技考古已经成为当下具体实践的常规操作。非技术专业出身的考古学家对特定出土文物的质地分析,必须请相关科技专家作鉴定,以了解原料产地和生产工艺的信息。过去那种单凭田野工作者个人直觉和经验判断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早年发现所作的草率判断和结论,今天仍然对社会产生着负面的影响,“西汉纸”就是其中的一例。造纸专家抱怨,有的博物馆甚至知道展品经鉴定后不是西汉纸的情况下,仍然执意按过去的不实说明展出。表明在某种利益驱动下,有关部门无视真相,不愿纠错的复杂心态。
在科技考古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不仅能够深入分析各种出土文物的材质和工艺,而且也可以对过去所下的结论进行重新的检验,20世纪中叶,考古学者和科技史学者在下西汉有纸的结论时并未首先请专家鉴定,过于草率、很不严谨。造纸专家在《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一书中对西汉纸状物的各种标本提供了权威鉴定,应该对西汉有纸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以后任何讨论有关西汉有纸的问题,应该首先认真和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如果有新的发现,也应该首先将出土材料供专家分析鉴定,在得到他们的分析结果之后才能对外正式发表和报道。
本文相关照片由造纸专家王菊华工程师提供,李玉华工程师在具体细节的说明上也给予了大量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1]王菊华、李玉华:考古发现西汉纸状物的分析研究。见:路甬祥主编《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
[2]王菊华、李玉华、齐晓东、王玉、王松: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历史定论不能动摇——对“放马滩纸地图”残片的再观察。载:《纸史和手工纸研讨会论文集》,中国造纸出版社,2019年。
信息转自:理寓物内 artifactsandide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