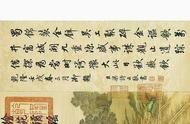《没头脑和不高兴》1958年11月第一版封面
当时《少年文艺》编辑急等稿件上版面,只给任溶溶两小时。那时,上班前总要拐到咖啡馆喝杯咖啡的他,利用喝咖啡的时间提笔疾书,一篇5000字的经典童话作品诞生了。这篇发表于1956年的童话,给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带去了快乐。其中最好玩的一句话是:“你不高兴跟他玩,他可是不高兴你不高兴跟他玩。”
任溶溶在回忆《没头脑和不高兴》作品创作之初时谈道:“角色都从生活中来,我自己就是那个‘没头脑’,常常糊里糊涂的。‘不高兴’嘛,我的孩子有点儿倔脾气,叫他做什么,他就会说:‘不高兴!不高兴!’有一次,我和孩子们一起在少年宫,这个故事突然自己就跑出来了。”1962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将《没头脑和不高兴》拍为美术电影,成为中国童话幽默夸张最成功的典范之一,更成为几代中国少年的集体记忆。

动画《没头脑和不高兴》
在这之后,任溶溶又创作了《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同样获得成功,与《没头脑和不高兴》堪称姐妹篇。虽然只是试水创作,但这两篇作品在风格和技巧上都已成熟,并“与世界儿童文学接轨”,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
相比之下,儿童诗是任溶溶最钟爱的文体,也为之投入最大。从1962年起,任溶溶创作了《我的哥哥聪明透顶》《爸爸的老师》《弟弟看电影》《强强穿衣裳》《我给小鸡起名字》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儿童诗。在他看来,创作儿童诗要从“诗人本位”向“儿童本位”转换,使用尽量清浅、好读的语言,教训意味不能过重,应该“不能只写要儿童做什么,同时也要写儿童要做什么”。
近十来年,任溶溶又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了散文的写作之中。他的散文辨识度很高,简洁、干净、明快,不拖泥带水,不冗长啰嗦,不矫情,不无病*,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性情宕开,适时打住,自然天成。强调作品让人看得懂,看得明白,看后又不觉乏味,并为之着迷,这是任溶溶一以贯之的追求。
“虽然我的头发开始白了,但我也是看任老的书长大的。”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魏育青曾回忆说,自己出生于1956年,正是任老写下《没头脑和不高兴》的那一年。“刚来到世界上,就有一个人为你写了这么多让你在几十年后读起来仍然觉得很有意思的书……非常感谢任老为我们的童年带来了那么多快乐,他的翻译著作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岁月匆匆,转眼间,那个带给孩子们快乐的任溶溶到了百岁高龄。任溶溶曾说过:“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对此,他的解释是:“人的一生总会碰到各种各样机缘,这是不是像一个童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