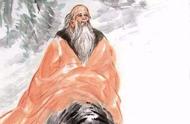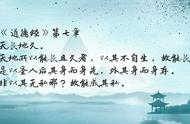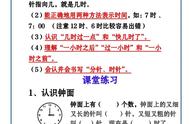老子和庄子都被认为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以“道”作为他们的哲学思想的根本范畴,即是说,老庄的哲学理论都是建立在关于“道”的规定性上面的,这也是他们的学说都属于“道家”的重要理由,可是,老子和庄子是有区别的,而且这区别还不小,老子是一个哲学家,然而,他又是一个谋略大师,他的权谋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他冷静而机智,很有韬略,可以说是古代权谋理论的鼻祖。与老子相比,庄子虽然也是哲学家,但庄子更像是一位艺术家,他的哲学理论是通过他的如诗性散文和寓言故事来阐述的,庄子有艺术家的天真气质,充满奇妙的想象力,故事讲得十分精彩,他真情、浪漫、潇洒、超脱。庄子梦到了蝴蝶醒过来时竟搞不清楚是蝴蝶梦到了庄子还是庄子梦到了蝴蝶,这不是非常天真可爱吗?与庄子的天真可爱相比,老子老谋深算、深谋远略,算是很有权谋,甚至可说是很狡猾的政治谋略家。
老子的理论与兵家有密切关系,他继承了早期兵略的思想,而后来的兵家也继承了老子的谋略理论,在道家谋略中,老子是理论奠基者和思想大师,所谓的“人君南面之术”,即政治哲学范畴内的帝王学、统御天下之术或治国之道,其理论基本点是由老子开始的。

《道德经》
一部《道德经》与其说是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不如说是中国古代的谋略典籍,仔细读进入,便不难发现,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讲的权谋理论,比讲哲学的还多一些,当然,二者很难完全分开,老子的哲学思想是他的谋略理论的哲理根据,而他的谋略思想是其哲学在政治理论领域的体现。《道德经》包含着非常丰富的谋略智慧。
下面,以《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作为典例,来分析老子的政治谋略思想,看看老子是怎样阐述道家的治国谋略的。
这一章的原文是: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这一章所讲的是道家政治谋略的精髓,老子在这一章中阐述了道家是怎样理解治国之道的。
第一,开头三句讲的是道家关于治国的三个基本原则,即关于“治国”“用兵”和“取天下”的基本道理。首先,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那么,关于"以正治国"这一句,说的是什么呢?句中的“正”字是关键,这“正”字即是指“政道”,也是指“正道”,治国必以正,此"正"者,乃“政道”也,即管理国家的政治措施、治理策略等;此外,此“正”者,乃“正道”也,治国之道,必须体现大中至正之道。
在先秦各家学说中,将治政理解为遵循“正道”,这几乎成了政治共识,只是,各家对“正”的解释不同。比如,儒家创始人孔子也说:"政者,正也。"《论语·颜渊》这主要强调以尊仁守礼为正;管子说:“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管子·立政》)主张走正道,反对走歪门邪道;法家强大以法治国,而他们认为守法为正,商鞅说:“ 法令者, 民之命也, 为治之本也”, “ 法任而国治矣。” (《商君书·慎法》)坚持执法,国家走的才是“正道”。
而老子所讲的“以正治国”与儒家不一样,不是指尊仁守礼之“正”,而是指遵循“道”的运行规律来治理国家,即顺其自然,不干预,不偏离,不过头,不回避,顺“道”而行,法自然方是“正”。
其次,老子讲"以奇用兵",这"奇"字是什么意思呢?“奇”与"正"对应,其意相反,即指"不正"。先秦时期,关于“奇正”的说法不少,特别是在兵学中,有代表性的兵家基本上都论到了用兵的“奇正之道”,最具代表性的是《孙子兵法》,孙子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战争要以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国家实力做基础,实力是“正”,是从正面的、公开地应对地方的,但光有实力还不够,战争需要用兵方面的出“奇”制胜,即凭借战略战术的变化,攻敌于不备,以奇克敌。取得时间、空间上的相对优势,实力是基础,而战略战术的合理运用则是发挥实力、夺取胜利的关键。“奇”还包括使用谋略和计策,即使用诡计。孙子曰:“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用诡计来欺瞒敌人,也是出奇制胜的策略之一。
学者称《道德经》通兵法,这是很有道理的,老子所讲的“以奇用兵”与《孙子兵法》里论用兵的“奇正之道”以及论“轨道”的兵学理论是相通的,所强调的是以“正”为基础,以“奇”为智策,需考虑与敌的实力对比,但不与敌死拼实力,而是要出奇制胜,“兵者,诡道也”,不晓得以“奇”来克敌的,必定不是杰出的掌兵统帅。
再次,老子讲"以无事取天下",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无事“是指无事可做,不需要做什么事,即无所事事。这其实说的就是道家一贯主张的"无为"。
其实,“以无事取天下”讲的就是“无为而治”的治国道理。治国之道,最忌讳的是管理者事无巨细,事事要管,处处要管,时时要管,管得太宽,太细,太勤了。上层的管理者事无巨细都要管,最终是丢了大事,只管住小事;而且,使得下面的人无法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变成无所事事,最后,忙坏了高层管理者,闲慌了下面的管理人员,成不了大事。而在道家看来,“无为而治”远不止是指与此相反的,而是指治理国家,要顺其自然,不横加干涉;只有顺其自然,才能使民众休养生息;反之,如果过多政策够多干涉,过多管理措施,那便是积极“有为”,而这是多余的,因为这样做便不是顺其自然,不是“无为”,这是违背“道”的运行法则的,是不利于治理国家的。所以,根据道家的治国之道,无论是儒家推崇“内仁外礼”,还是法家强调“以法为本”,都破坏了顺其自然的原则,都是错误的,都不是“无为”,不是“以无事取天下”,因而,都不是正确有效的治国之道。

老子画像
第二,为何说"以无事取天下"是对的呢?老子在接下去的分析中,对"吾何以知其然哉"做了详细的回答。首先,老子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所谓的"忌讳",从政治管理的角度看,是指各种禁忌、禁令,包括各种法令、法规、宣称理念等。在老子看来,禁忌、禁令如果过多了,民众动不动被处罚,被训斥,被责怪,自然就缺乏言论和行为的自由,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因而造成民众不敢说,不敢做,不能说,不能做,久而久之,便会使整个社会缺乏主动性、创造性,对于财富的创造就失去了活动的支撑,因而也将变得越来越贫困。简要说,老子是认为,社会财富的创造是要以民众的言行自由作为前提的,而禁忌、禁令太多了,抑制自由创造,不穷才怪了。
其次,老子说:"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所谓的"利器",主要是指利己之器,即为己获利的工具。王弼说∶"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强则国家弱。"这说得很明确。河上公注曰∶"利器者,权也。"孙子说:“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孙子·计篇》)可见,这是指权衡利益而手段。而高享先生认为"利器"就是"武器"。如此说来,老子的这一句话有两种解释,一是指民间利己之器多了,国家就会产生混乱,变得黑暗;二是指如若民间多藏武器,拥有兵革之利,则国家就愈加混乱、昏暗。而不管是哪一种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民间利己的手段、工具多了,国家就会混乱、黑暗。
再次,老子说:"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所谓的"伎巧",就是指技巧,意指投机取巧的方法、手段,技巧多了,新奇事物就会增加,人就会有更多的投机的心智,因而也就会逐渐失去敦厚朴实的心性,想投机取巧,自然离“道”也越来越远了。这与上一句所强调的其含义基本一致。说的就是“弄巧成拙”,聪明反被聪明误,丧失了顺其自然的观念。
此外,老子还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谓的"法令",比较容易明白,指国家法规和官方的命令,而“滋彰”是指名目繁多、条目清晰。原本国家制定法规,官方发布命令是为了防止狡诈奸伪的盗贼的,但“法令"太多,规定太苛严,结果,不但没有能制止偷盗行为,反而使盗贼更多了。这就叫做适得其反。闽南俗语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形象,叫”严官府出厚贼“,意思是说,越是采用严酷处罚的官府,其属地将出现越厉害的盗贼。

老子画像
最后,老子提出了道家的管理策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所谓的"我",这是统治者的代称,老子以第一人称说话,比较有力量。而几句话中的"无为""好静""无事""无欲",是对应于上面分析的"多忌讳""多利器""多伎巧""多法令"所说的,皆是强调道家治理时的“无为而治”“顺其自然”的主要方略。而"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则是统治者实行“无为而治”所能够带来的效果、成果。如果说上述分析批评的是“有为”,是“妄作”,那么,这后面所推崇的则是"无为",因而能获得"无不为"的效果。简言之,老子借圣人的话说:“我无所作为,民众便能自行发展;我爱好清静,民众便能自己变得更正派;我无所事事,民众便能更富足富裕;我没有*,民众便能变得更淳朴。”这说的就是“无为而治”的主要方法和效果。

老子画像
总之,在老子看来,道家治国之道主要包括三个原则:“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其中,第一个原则是强调治国理政要依顺“正道”,而这“正道”指的是道家的顺其自然的原则,对管理对象不作过多干预;第二个原则是强调用兵不能仅仅满足于实力,还要能“出奇制胜”,要深谙“兵者,轨道也”的用兵智谋;第三个原则最关键,所强调的是想夺取天下,想治理好天下,必须坚持“无为而治”(即“无事”)的管理妙策。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老子是想回到以前的社会形态,他的想法才侧重于“无为而治”方面,而进入了战国时期,老子的这一套就不一定适用了,如果坚持治国顺其自然,无所作为,那么,如何做到富国强兵呢?也不可能有军事实力(孙子讲的“以正御敌”),而没有军事实力做基础,也就不可能做到第二点,即“以奇用兵”,以奇取胜。战国时,秦国通过变化富国强兵,证明了光是老子所讲的以“正道”(顺其自然)治国是不够的,也是难以奏效的。至于第三点,即“以无事取天”,只是采用“无为而治”的方法,只有在由“乱”转“治”的过程中才是有效的,就像在汉初,楚汉战争已经结束,刘邦建立了汉朝,采用“无为之治”才有效,才会有“文景之治”,若是在楚汉战争最激烈时,刘邦、韩信不用谋略、兵法,只采用“无为”之策,刘邦怕是要将汉军输光了。
可见,就古代的政治哲学而言,治国之道,不能仅用道家之策,还要将法家、兵家、儒家等的管理方法作为互补,将儒、道、法、兵、墨各家的管理精华,融为一体,才是最好的治国的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