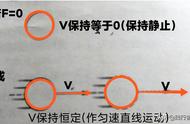(1)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命,也是我所想要的;道义,也是我所想要的。两者不能同时都得到,(我)会放弃生命而选取道义。
(2)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生命也是我所想要的,但所想要的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就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情;死亡也是我所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还有比死亡更坏的事,所以有祸患(我)就不躲避了。
(3)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
按照这种方法(可以活下来的方法)就可以活着,却有人不采用,按照这种方法(可以避患的方法)就可以躲避祸患,却有人不去做。
(4)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
因为有比生命更想要的东西(即义),有比死亡更令人厌恶的东西(即非义)。
(5)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不只是贤人有这种思想,人人都有这种思想,只不过贤人能够坚守这种思想不至于丧失罢了。
(6)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如果)无礼地吆喝着给人(吃),就是过路的饥饿的人都不会接受;用脚踢着给人家,即使是乞丐也因遭轻视而不屑接受。
(7)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丰厚的俸禄,如果不辨别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了,那么这种厚禄对我有什么益处!
(8)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这种行为不可以停止吗?(如果不停止,)这就是所说的丧失了人本来的天性。
②
唐雎不辱使命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说。安陵君因使唐雎使于秦。
秦王谓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唐雎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
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注:选自《战国策·魏策四》,题目是后人加的。《战国策》是西汉刘向根据战国时期史料整理编辑的。

(1)安陵君其许寡人!
安陵君一定要答应我!
(2)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
现在我用比安陵大十倍的土地,请安陵君扩大自己的领土,但是他违背我的意愿,(是)看不起我吗?
(3)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
安陵君从先王那里继承了封地继而守护它,即使(是)方圆千里的土地(也)不敢交换,更何况只是这仅仅五百里的土地呢?
(4)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天子发怒(的时候),倒下的尸体有近百万,鲜血流淌数千里。
(5)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
百姓发怒(的时候),也不过就是脱掉帽子,光着脚,把头往地上撞罢了。
(6)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
这是平庸无能的人发怒,不是有胆识才能的士人发怒。
(7)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
这三个人,都是平民中有胆识才能的人,心里的愤怒还没发作出来,上天就降示了吉凶的征兆,(现在)加上我将是四个人了(我将成为第四个这样的人)。
(8)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
假若这个士人(我)一定发怒了,倒下的尸体两个,五步之内淌满鲜血,天下百姓(将要)穿丧服,现在就是这个时候。
(9)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安陵却凭借方圆五十里的地方幸存下来,只因为有先生在啊。
③
送东阳马生序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 ,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
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撰长书以为贽,辞甚畅达。与之论辩,言和而色夷。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予者哉!
注:选自《宋濂全集》。宋濂,字景濂,号潜溪,元末明初文学家。此篇需背诵前两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