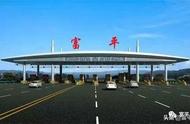图源黄有维水彩
提起四合院,我这年龄的人即便是从小就住在北京,也没有几个能真正说出点什么。毕竟都在楼房中长大,很难对只在书本上见过的东西产生深厚感情。
我在同龄人中要算是幸运的了,可以在四合院中住上十几年。本来普通的东西,成为记忆的时候,或许永远是最美好的。现在回想起两年前搬出的院子,就像在心灵深处放一部胶片发黄的老电影——
这座坐北朝南的四合院坐落在老城区的汪芝麻胡同内,胡同口隔一条街就是著名的东四那十几条胡同。汪芝麻虽不及那些胡同又长又深,但我家的院子里却总能找到某种与世隔绝的清静意味,根本感觉不到街上喧嚣的一点痕迹。
我只知道这座院子属于祖父,不过连祖父也不知道这座院子真正的年纪、经历过怎样的沧桑。

图源黄有维水彩
祖父和祖母有五个孩子,原来院子里住着各家,后来几个姑姑或搬走或出国,祖父去世,祖母因病住院,最后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和一个小阿姨、一个当年祖父家的老保姆。搬走前的一年,那个老保姆,一位因为住在厨房旁的房间里而被我唤做“厨房奶奶”的勤劳老人,也终于以九十九岁的高龄辞世。
从胡同中走过,我家院子并不容易被忽视。朱红木门,两个乌黑的门环,顶上灰瓦,周墙青砖,再加上门前两方花纹模糊的抱石鼓,是四合院标准的如意门。院子三进,进了大门,左边是门房,面前是一面影壁,影壁前面的空地种着一株银杏。从这里往西一拐,下几级台阶就是前院。
前院中,西面上一段台阶是一个改成车库的厢房,原用两扇巨大的木门和胡同相接,后来装修时把木门拆掉,换了店铺常用的金属卷帘门。我们家没有车,所以车房一直被当做堆放杂物的地方,我五岁前睡的小床后来就一直放在那里。前院东面是厨房,北面一个样式标准的垂花门连着中院。在垂花门旁边有一个后来用砖砌出的小小耳房,用来存放菜,那是童年我和来家里做客的小伙伴捉迷藏时最佳的藏身地。
中院最大。北面是正房,祖父和祖母的起居室。小时候每天放学回来都要先到这儿向他们问好才回自己屋子。中院的东厢两间房是饭厅和保姆的卧室,东厢前的花池中种着棵很大的梨树。在饭厅内有一扇门与前院的厨房相连,夏天和伙伴打水仗,经常利用这道门从前院绕开垂花门溜进中院来。东厢和正房间有道现在已经少见的圆形月亮门,直通后院。后院除了两个树池外只有北面一排四间屋子,从西数起第二间就是我的房间。两个树池中,大的种着棵极高的柿子树,小的是葡萄,这都是我小时候观察昆虫和植物的“实验所”。

图源黄有维水彩
国人盖房子总喜欢把家围在一个院子里,无数专家学者也有各种解释和观点,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或许是这青砖白墙,朱门灰瓦为我营造了一个自由的、可以最大限度上不受人干扰的私密空间。我在这里玩耍嬉戏,舞刀弄棒,下接地气,上顶苍穹,从小就在一种接近自然、不受空间拘束的环境下成长。
楼房中长大的同学常问我为什么跑步和协调能力不经训练就这么好,其实这都应归功于从小在院子中长大。母亲曾笑着说起我刚学会走路时经常一个人大黑天从后院跑到院门口,一路有那么多石阶沟坎,竟然从来没被绊倒过。
院子为儿时的我提供了一个足够小男孩疯玩的空间,同时它自身具有的深厚文化积淀,也让我从小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兴趣,不但学习了国画书法,还和祖父练习太极拳剑,而且喜欢上了听京剧。在这样的院子住着,身心都受到了潜移默化的熏陶。初中语文老师对我有一句评语,说我“看上去就是一个‘中国文人’”——她不知道,这也是我家院子的功劳。
春赏百花秋望月,夏日听雨冬观雪——四季的交换让我家院子变化着不同的风姿。
春天是新绿的季节,年年开春,沉寂一冬的花草开始松动骨节,陆续用稀疏的绿色装点起院子,让灰瓦白墙们迅速从冬天的沉闷中苏醒过来,梨花、樱花一夜之间坠满枝头,丁香的紫花、牡丹的团簇,都早早显示着生机的蓄势待发。这个时候的我也正嗅着春天的气息,脱去厚重的衣物,让自己在万象更新中,迎来新的一次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