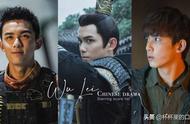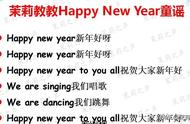▲ 图1:宾阳洞前壁浮雕全图。 制图/Paprika;图2:来自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北魏大型浮雕《维摩变》中的维摩诘居士像片段。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历经周折转运至美国,浮雕从岩壁上盗凿到漂洋过海,受到了极大的损坏。博物馆非常努力的给予了最大程度的修复,才能使我们有幸一睹一千五百年前的这尊大型浮雕的一个局部片段。 图/网络

唐高宗、武则天、中宗、玄宗执政的盛唐时代,龙门造像活动达到巅峰。因天下相对太平,社会财富增长,龙门造像已非权贵专享之事,普罗大众也广泛参与其中。

▲ 洛阳龙门石窟游人如织。摄影/黄政委
洛阳作为唐朝东都,商业繁荣,大量自由工匠在洛阳聚集,他们公开接受各类顾客的造像订单。此时,龙门石窟由私人定制的奢华商店,变为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信仰集市”。此时,开窟已蔚然成风,前朝佛事遗迹,成为“龙门集市”的最佳广告。
想象一下,在一个天朗气清的好日子,伊河波光潋滟,两岸绿柳成荫,僧人、信徒傍水前行,礼佛与游赏之余,仰望东西两山,千岩竞秀,万木争荣,漫山洞窟如蜂房蚁窝,令人一时恍惚,如入曼妙殊胜的佛国幻境。思绪万千之余,不禁心向往之:何不也为自己和家人造一佛龛祈福纳祥呢?或许,做造像营生的商人工匠,如今天景区随处可见的“摄影快充”商贩,正打着幌子在附近招揽买卖。
同时,频繁出没龙门的社会名流,又增强了宣传力度,大诗人白居易曾与僧人佛光同乘一叶扁舟,从洛阳城的建春门溯伊水悠悠而上,赴龙门香山寺游玩,二人一路低吟长啸,把酒论诗,引得岸上人们纷纷驻足,传为一段佳话。实地展销结合名人代言,对信徒们的吸引力自然不在话下。

▲ 惠简洞。摄影/石耀臣
据造像题记显示,唐代龙门石窟的功德主身份十分多样,如商业行会出资修建的北市丝行像龛、北市彩帛行净土堂、北市香行社;街坊邻里合伙修造的思顺坊老幼造像龛;僧尼营造的如西京法海寺寺主惠简造惠简洞、内道场沙门智运造万佛洞;外国人开凿的新罗人像龛、吐火罗僧宝隆像龛;奴婢修建的奉先寺家人造像龛等等。
各类下层百姓的营造不可胜数,如《总章元年王合为妻患得差》,是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开凿的小佛龛题记,讲述了唐代百姓王合之妻久病不愈,丈夫四处求医无果,于是希望通过造像积功德,祈求佛祖保佑其妻痊愈。
另如《仪凤三年齐州山荏县刘宝楂妻范为身娠》,刻于唐高宗仪凤三年(公元678年),记录了齐州山荏县百姓刘宝楂之妻*,刘宝楂对妻恩爱有加,希望母子平安,便出资开龛造像,为妻、子祈福。
因财力不足,普通百姓所雇工匠修养和技艺大多不高,他们的造像普遍雕凿粗糙,形制矮小,造像旁所刻发愿文或题记,多修辞简短粗率。不过,这些看来马虎、粗劣的字迹,对于窟主和工匠,也都是尽心竭力之作,饱含了他们的智慧与虔诚。
当然,唐代石窟中,雕造品质最精良,规模最庞大的,仍是皇家石窟。其中最知名的杰作,是卢舍那大像龛(奉先寺),其主尊卢舍那佛,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高1.9米,是龙门石窟中最高大的造像(龙门最小的佛龛高1.9厘米,龛内坐佛高1.3厘米,位于古阳洞南壁下层)。
唐代《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记载,大像龛是唐高宗下令建造,当年皇后身份的武则天捐两万贯脂粉钱资助,有人计算,盛唐一文(枚)铜钱的购买力相当于人民币0.5元,一贯钱是1000文,两万贯的购买力约等于今日1000万元人民币,堪称一笔巨款,而这只是工费中的一笔而已。
因卢舍那大佛法相慈祥典雅,面貌丰满圆润,民间传说其是依据武则天面容雕凿的。皇室成员所开石窟还有魏王李泰造宾阳南洞正壁大像,纪国太妃韦氏造敬善寺石像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