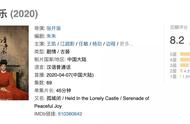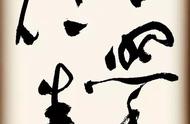作者:张九龙
不久前,在浙江衢州市实验学校菱湖校区门口,孩子们背着书包,拎着饭盒,开心地等待着进入校园。为了配合疫情防控,几名戴着造型奇异“一米帽”的孩子尤其亮眼,让人瞬间联想到热播电视剧《清平乐》里的宋代官帽。
《清平乐》等宋代主题影视剧的热播,引发了人们对宋式美学的极大兴趣。人们称宋式美学为“极简之美”,认为宋人是极简主义的先驱。其实,从宋朝官帽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宋人审美观念里,也有夸张的追求,并不能用“极简”二字来简单概括。
“一米帽”早有原型,君臣平民都可戴
在历朝历代的官帽中,大概没有比宋代更博人眼球的。电视剧《清平乐》里,官员上朝时所佩戴的官帽,左右两边长长的翅子足有一米长。

《宋仁宗坐像轴》
关于其来历,有种绘声绘色的说法。宋太祖赵匡胤是武将出身,手下有一帮出生入死的兄弟。等到赵匡胤黄袍加身当了皇帝,兄弟们也个个加官晋爵。不过,这些平时随便惯了的兄弟,没从过去的角色中迅速转换过来,上朝时没规矩,经常交头接耳。
赵匡胤很不爽,却又碍于情面,不好发作。于是,他设计出一种新型官帽,在帽子侧边加了一对又硬又平的长翅,每边都伸出去半米。大臣们戴上它,别说交头接耳,就是想挨近点,都有被啪啪打脸的风险。从此,朝堂上再也没有不守规矩的现象。
实际上,这只是后人杜撰出来的故事。宋朝官帽的学名叫“展脚幞头”。如果看看唐太宗李世民留存于世的画像,大家就会发现这种“幞头”早有原型。隋唐时期的幞头是略微下垂,到了宋代,只不过把它给进一步拉直加长了。
幞头最初是一块黑色的方形织物,“裁幅巾出四脚以幞头”,两脚在后面打结下垂,两脚反折到头顶上打结固定,所以也叫“折上巾”。
展脚幞头是古代一种常见的帽子。宋代时,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凡男子皆戴。从古代壁画中可以看到,唐、五代、辽、宋、金时期,不少门卫、乐伎甚至干活的仆人都头戴展脚幞头。
为了行动方便,宋朝身份低的公差、仆役,多戴无脚幞头。由于当时官吏戴的幞头所用罗纱通常为青黑色,也称“乌纱”,后世便有了“乌纱帽”的说法。
展脚幞头在宋代壁画和雕塑里屡见不鲜,但是留存下来的实物极少。1999年,江苏泰州市一职中工地发现了宋代蒋师益墓。蒋师益是名贡士,没有官职记载,但是墓里出土了一件展脚幞头。它高21厘米,通长达到了120厘米,是地地道道的“一米帽”。
至于宋人为什么把幞头的造型给夸张化,王得臣的《麈史》说得很清楚:“制度靡一,出于人之私好而已。”
我们还可以从流行史研究的角度来解读。历史上,很多具有实用功能的用品,会因为穿戴在外而被人们加以夸张化和装饰化。夸张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发不可收拾,逐渐达到极端,直至脱离了最初的结构和功能。
当发展得太夸张,以至于影响到正常使用后,这种夸张化的特征便会逐渐消失。展脚幞头的命运正是如此,元代以后便淡出了日常生活。
皇帝有钱有文化,奢华中追求雅致
宋代,尤其是南宋,基本处于收复国土无望、拘于一隅的偏安态势,这种内缩型、自守型的政治格局,直接影响到整个时代的文化风貌。宋代美学一改唐代美学顶天立地式的自我张扬与境界拓取,从自然、社会的外在形象的挖掘写照,转而进入一种生活理趣与生命情趣的内在体验品味。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壮阔意象,被庭院深深、飞红落英的清雅意趣取代。
当时商业繁荣、城市发展,人们对物质的追求比前代更甚,全社会形成了一种追求休闲、享受安逸的风气。这种风气,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皇帝的大力提倡与鼓励。
宋代皇帝多喜欢享乐。从宋太祖“歌儿舞女,以享天年”,到宋真宗大兴赏花钓鱼赋诗宴之风,从宋徽宗纵情于书画艺术,到南宋诸帝偏安杭州、“西湖歌舞几时休”,都足以说明问题。
稍微幸运的是,宋代的皇帝本身都是些“文化达人”,因此审美情趣超过了“土豪金”。宋代崇文抑武,皇帝一直以身作则。宋太宗既懂音乐,又爱好书法,其他如宋仁宗、宋徽宗、宋钦宗等皆是能书能画的皇帝。宋代皇帝也热爱读书,并雅好诗词创作。
有钱有文化,所以宋代皇帝在审美上追求雅致,一般的金银珠宝已经难入他们的法眼。只不过,看似“极简”的背后,其实是另一种“极奢”。
宋代宫廷生活非常丰富。有皇家园林可以赏玩游憩,有规模宏大的宫廷乐舞,有舞文弄墨的闲情逸趣,还有君臣相欢的赏花钓鱼、御宴活动等。到了宋真宗时期,皇帝甚至直接鼓励臣下享受太平,与臣下“以声妓自娱”相互劝勉,并为宰相王文正置办歌妓等,以尽情享乐。
营造园林可以看作是宋代追求“奢”与“雅”的缩影。在宋之前,中国园林的主流是皇家园林,讲究规模宏大,设在郊区,远离都市。而且中唐之前的园林,多带有实用性的功能,如生产、祭祀等。到了宋代,园林已成为单纯怡情养性或游宴娱乐活动的场所。
宋徽宗建的“艮岳”,有“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的赞誉,占地七百余亩,是当时园林的巅峰之作。为了营造雅致的氛围,宋徽宗向全国征集各种奇珍异石、花草树木。运送这类东西的队伍,被叫作“花石纲”。劳民伤财的行径直接引发了农民起义,《水浒传》的故事便源于此。
“休闲”指数显身份,宋式美学美在精神

宋徽宗《文会图》局部:点茶与分茶
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宋式美学觉得美呢?因为影视剧呈现出来的宋代文人居住环境,表现出一种“居室的园林化”。
宋人在居住环境设计中,体现出强烈的园林化倾向。如陆游故居“三山别业”,由居室、园林、园圃构成,居室与园林融为一体,共用一门,而园圃环绕四周。王十朋的茅庐、小室、小园,“晨起焚香,读书于其间,兴至赋诗,客来饮酒嚷茶,或弈棋为戏”。这些都反映出,宋代士人重视日常起居休闲游憩的重要性。
在室内的陈设上,他们也追求清远闲逸的园林风趣。现在中国人喜欢在室内挂些装饰画,这种源头就是宋代。
宋人特别喜欢将当时流行的山水画作张贴悬挂于自家墙壁上,寄托一种山水恬淡的闲情,即所谓的“不下堂筵,坐穷泉壑”。就连青楼、商铺、酒店等消费场所,也流行将山水画张贴于室内,以招徕顾客。
在日用器皿上,他们也崇尚古拙清逸、平淡简易的审美风格。居室中所常见的如香炉、花瓶、茶具、屏风、瓷器等,都体现出主人的闲情逸致。
至今,宋瓷仍是古代瓷器史上难以逾越的顶峰。宋瓷的代表为汝窑、官窑、哥窑,所产瓷器大部分流入宫廷,民间也有出售。其审美自然朴素,却透露着典雅的庙堂之气,淡泊之中又有温润如玉之美。宋瓷器型、线条、釉色晶莹柔和,厚重内敛,是宋代审美人文精神的凝固与浓缩。
今天来看,宋人是特别懂得享受生活的。如果要概括宋式美学,“休闲”显然要比“极简”更准确。在宋人那里,休闲意味着自由生活,可以回归自然,体验自我。
相比建功立业来说,这种“小确幸”似乎微不足道,但正是这微不足道的闲情逸致,被宋人赋予了极大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休闲”指数直接反映出宋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
吴自牧《梦粱录》中记载,宋代文人有“四雅”:焚香、点茶、挂画、插花。“琴棋书画诗酒茶”,便是宋人追求的诗意人生,也是宋式美学的外在表现。而且,宋人一再强调焚香、点茶、挂画、插花这个过程一定得自己享受或自己掌握,不能让外行的仆役动手。
“四般闲事”如果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遇到,那么,就成了文人之间的一个聚会——雅集。雅集是宋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他们抚琴、调香、赏花、观画、弈棋、烹茶、听风、饮酒、观瀑、采菊、写诗和绘画,躬身实践种种生活情趣。
现代人生活忙碌、节奏飞快,自然会羡慕和向往这种生活。不过,追求形似更要神似。
宋式美学的本质,是减少过多向外索求的*,而回到内在真实的自我生命上来,宋诗开山祖师梅尧臣管这种境界叫“乐亦由人”。
看看“背诵天团”就会发现,唐代的韩愈、柳宗元等,会因悲剧的境遇而自我哀悯、愤懑,而宋代的贬谪文人,大多能休闲放旷、内心平和,这与他们善于自我调适有很大关系。
不如意事常八九,人生忙碌是常态。没有一种自我满足、知足常乐的心态,就算置身宋式美学空间,仍难以从容体验山水林泉之乐。这对终日奔波的现代人来说,更值得反思。(张九龙)
原标题:《清平乐》背后的宋人生活情趣 宋式美学:奢中求简易,忙里偷闲难
,